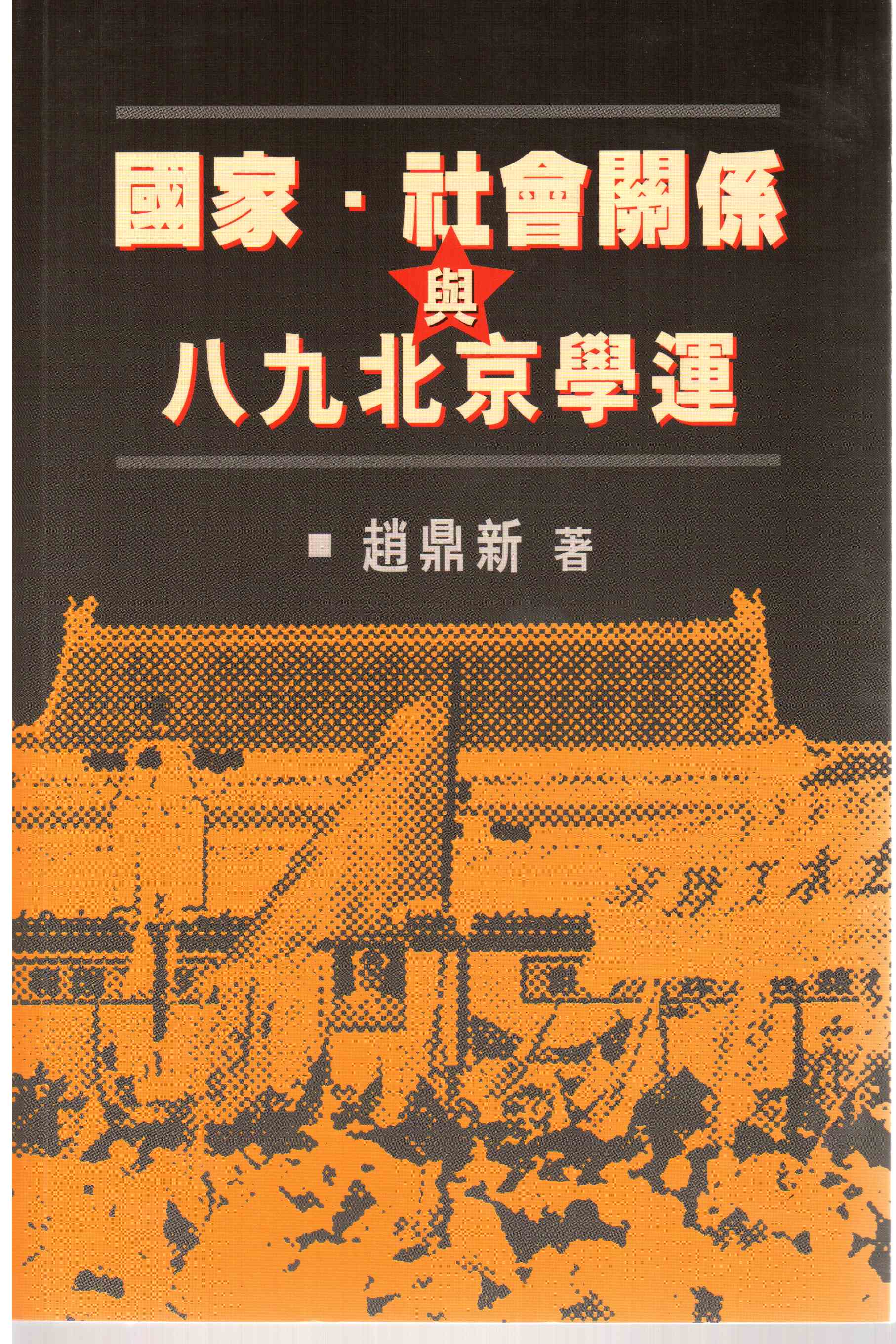——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共产体制除了限制身体与经济之外,还要求我们的灵魂也完全地屈服,要求我们不断地、积极地去参与普遍的、有意识的谎言。
索尔仁尼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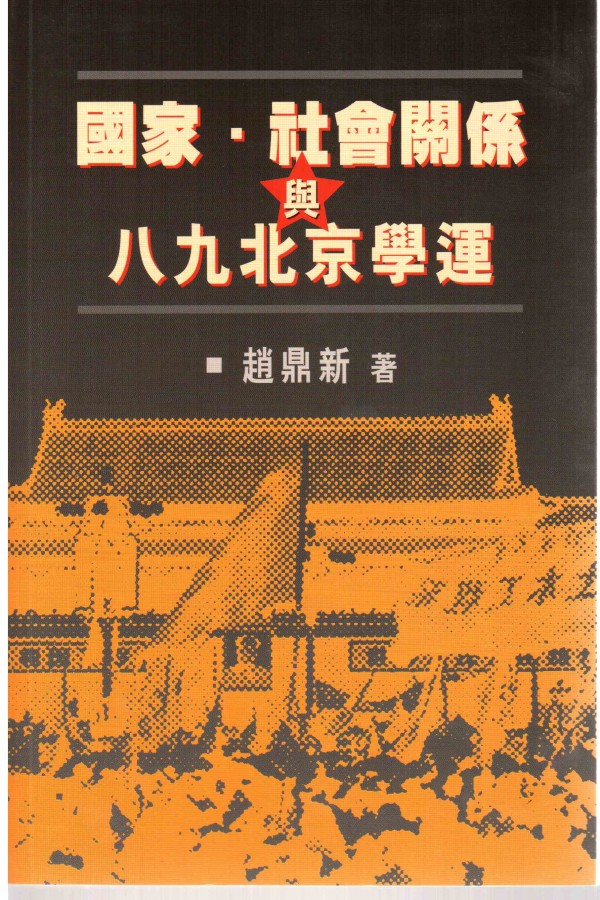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轨道。数以千计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遭到中共军队的屠杀,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全部被清洗出局,中国??从此掉头进入一个宛如“一九八四”中“老大哥”时刻盯着你的“美丽新世界”。八零年代短暂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给许多过于善良的中国人造成了“老虎从此不再咬人”、“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昨天的共产党”的美好错觉。然而,坦克和机枪一下子就暴露出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此后四分之一世纪,一种被命名为“中国模式”的极权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杂交的怪胎,在这块土地上蓬勃生长。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不仅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噩梦,而且日渐膨胀为全世界的噩梦。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轨道。数以千计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遭到中共军队的屠杀,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派阵营全部被清洗出局,中国??从此掉头进入一个宛如“一九八四”中“老大哥”时刻盯着你的“美丽新世界”。八零年代短暂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给许多过于善良的中国人造成了“老虎从此不再咬人”、“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昨天的共产党”的美好错觉。然而,坦克和机枪一下子就暴露出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此后四分之一世纪,一种被命名为“中国模式”的极权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杂交的怪胎,在这块土地上蓬勃生长。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不仅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噩梦,而且日渐膨胀为全世界的噩梦。
毫无疑问,没有八九,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基本面貌;所以,了解和研究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真相,乃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对八九学运最深入的研究著作,是社会学家赵鼎新写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这不是一本“冷”的书,而是一本“热”的书,正如作者所说:“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了解’六四’,就是因为产生大规模反体制运动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依然存在;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了解’六四’,是因为只有温故才能知新,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为避免把’六四’悲剧的重演作出努力。”作者采访了七十位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又考究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实证与理论环环相扣,因而本书两度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杰出书籍奖”。
我们仍然生活在产生“八九六四”的专制阴影之下
过去很多研究者讨论六四,都把目光瞄准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无论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一谈起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好像观看狗血电视连续剧一样沉湎其中、欲罢不能。看一看近期的周永康案,外媒有多少绘声绘色的长篇报道、立场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兴奋不已的评论,就能心领神会。这种心态是畸形和扭曲的,是中共统治方式的畸形和扭曲,导致了观察者和研究者思考方式的畸形和扭曲。而要洞悉中国的真相,必须抛弃此类隔靴搔痒的陈词滥调。赵鼎新指出:“高层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确是存在的,但导致运动中政策变动的关键因素却是各种国家控制手段的失效。”换言之,虽然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歧横贯整个八零年代,但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时代派系斗争“你死我活”的地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两派力量仍然可以达成某种妥协,这一点从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然而,为什么两派力量在八九学运期间一步步走向了决裂?
对此,赵鼎新指出:“在八零年代的中国,国家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中层组织发育得很差,而国家合法性基础则建立在道德和经济绩效之上。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加上国家主导的经济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的不安定感和各种社会冲突,终于导致八九学运的爆发,并塑造了它的发展。”也就是说,当时民间与官方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理解有了巨大裂痕:共产党仍然认为原有的那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绝对正确,受万民拥戴;但是,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民众,早已不相信官方意识形态,更多瞩目于在经济改革中获得多大利益,以及政府能否充当“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角色。用赵鼎新的话来说就是:“大部分学生和北京居民并不真正关心政府的组成方式,他们更关心的是政府行为的道义基础,以及政府是否能够稳定秩序和繁荣经济。集中在官僚腐败和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标语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正是它们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政府的期望。”一九八九年经济改革受挫,以及官僚阶层贪污腐败的泛滥,成为八九学运爆发的两大诱因,而中共当局无力在这两个问题上重新赢得民众信任,官方和民间这才渐行渐远。在此情形下,改革派偏向顺应民意,保守派企图压制民意,两者最终南辕北辙。
虽然八九学运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但正如赵鼎新所言,发生八九学运的背景,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首先,尽管经济的发展部分满足了民众的欲望,但党的腐败比起八零年代来变本加厉,几乎是“无官不贪”。其次,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掌控,中间社会的发育不良,公共空间的蹇迫,知识精英责任感和影响力的进一步衰减,使得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缺乏缓解和消化的渠道。赵鼎新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停滞,一旦国家财政收入不能以每隔几年就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胃口早已被吊大的中国老百姓的情绪就会向同一个方向集聚。到那时,如果主流知识阶层也不再能拿到今天这样的物质好处,中国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八九之前那样的反体制性思想整合。有了统一的反体制思潮和广泛的社会不满,一场与八九学运类似的反体制革命性运动离我们还会远吗?”
八九学运中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
本书最具创见的部分,是将八九学运与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相比较,认为“八九学运的组织化程度远低于前两次学生运动,参与者也习惯拿道德标凖来评价政府”,“八九学运比起前两次学运来显得更为传统”。就此而言,八九学运是一场“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运动。运动的领导者,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对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从未有过深刻的认识和研究,更是缺乏运作反对派组织的经验与能力。
作者指出,传统的修辞和活动形式充斥于八九学运的首要原因是,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经过中共四十年的极权统治,中间社会被破坏殆尽,“八九运动中出现的所有社会运动组织,都是在运动开始之后才成立的,这些组织成立仓促,其领导人也未通过具备一定人数和合理的程序而产生,领导人本身也没有什么组织运动的经验”。所以,广场上虽然一度有百万人潮,却是一群缺乏组织的乌合之众。
其次,在运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前提下,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同情者和旁观者的心理状态对运动发展所起的作用相当大。“运动参与者更容易为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活动所打动,特别是当学生以道德说辞为核心向政府发起攻击,而政府当反应不恰当的时候,人们马上变得非常情绪化。”在八九学运过程中,情绪的推动力始终大于理性,以至于激进派始终占道德高地,温和派被斥责为“叛徒”,学运错失了好几次和平退场的契机。
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也在学潮中暴露无遗。以秦始皇自居的毛泽东是中国专制传统的产物,但共产党却长期对年轻人推行反传统的教育和宣传。表面上看,跟五四和一二九的大学生相比,八九这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甚少受传统文化的左右。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传统的因素立即借尸还魂。赵鼎新指出:“八十年代的学生起用了许多被他们的五四前辈猛烈地抨击过、并早已淡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言辞。”比如,八九学运的导火线是胡耀邦的去世,最初的抗议活动围绕被视为贤相和青天的胡耀邦的葬礼展开。这一点,当时只有宣称彻底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刘晓波有所体认和反省,他对民间神话胡耀邦、迷信青天大老爷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他的看法并未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
紧接着,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上学生的下跪,成为一种重要的运动手段。三名学生下跪和绝食,打动了成千上万富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从而决定了运动的态势。但是,下跪显然不是现代公民面对政府时应有的举动,更像是帝制时代子民像皇帝需求救济的最后手段——告御状。在《绝食宣言》等重要文告中,撰稿者也更多诉诸于传统的忠孝理念,而不是来自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
不过,在这个层面,作者对“传统因素”的定义稍显狭窄。其实,不仅是被贴上“封建”标签的、帝制时代的文化特征属于“传统因素”,中共统治以来形成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也形成了另一种植入中国人血液里的、更强大的“传统因素”,如果不付出刮骨疗伤的痛苦,人们不可能与之一刀两断。在八九学运中,“党文化”的“新传统”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比如,当学生与士兵对峙时,双方高唱的居然是一模一样的歌曲——《国际歌》、《血染的风采》、《龙的传人》、《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歌曲或者是共产党长期推广的左翼革命歌曲,或者是八十年代宣扬新兴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爱国歌曲。由此可见,那一代人虽然经过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洗礼,思想和文化背景依然是贫乏之极。
在形而上层面,没有全面而系统的民主、人权、宪政理念的研讨及普及;在形而下层面,没有公民社会的自觉和高度组织化的反对运动,八九学运即便不被武力镇压,也很难像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苏联东欧发生的反对运动那样结出民主转型的硕果。
屠杀能够带来稳定和富足吗?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个弱项是,对八九以后至今中共统治术的评价过于正面。作者指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不再具有理想主义特质,而是具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观,而且对经济问题有更好的理解。“这一代领导人具有较为高超的执政能力”,“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举措促进了政权的稳定”。
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把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与赵紫阳相比,尽管他们学历显赫、教育背景更为完整,但他们真实的学养、对知识对渴求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远远比不上赵紫阳。即使单单以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和对自由经济的理解而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与赵紫阳和江泽民都有过深入交谈,他的感受是:“我从来认为,对经济学的感受是人生来俱有的而不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许多高智慧并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只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没有受过什么经济学训练的人却可能对经济学有某种直觉。赵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类人。他对经济形势和市场如何运作显示出富于经验的理解。同样重要的是,赵认识到需要重大的变革,而且认为改革要有公开性。……赵显示出他真的理解让市场获得自由是什么意思;而江泽民不懂。”可见,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领导人既没有道德感召力,也缺乏基本的智慧和能力。
所以,对领导人历史地位的评价,绝对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赵紫阳受到元老的制约和时代环境的限制,未能实现其理想,但这并不表明他治理经济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弱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反之,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六四屠杀之后以发展经济取代政治改革,最终“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但这算不上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功。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让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失去了八零年代残存的那一点道德权威,这种“跛足”态势只能以“暴力维稳”来平衡。今天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百分比而付出的环境破坏和人心败坏的代价,未来需要付出十倍的数字来救赎。所以,今天受到官媒歌功颂德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们,未来真实的历史评价将有可能跌为负数。
在此意义上,中国的稳定性远不如印度:印度已经解决了民主化问题,不再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空悬的困境;而中国只能靠经济发展来麻痹民心,国家未来的方向暧昧不明,且发生根本性崩溃的可能越来越大。中国财富调研公司胡润报告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百分之六十四的百万富豪已经移居外国,或打算在未来几年内移居。他们把最受青睐的目的地列为美国,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虽然受访者将更好的教育、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移居外国的主要原因,但据中国富豪家庭的顾问表示,对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担忧,使富豪们将更多财富转移到海外以确保安全。据估计,二零一三年,中国居民在海外拥有六千五百九十亿美元财产。可见,中国的富豪阶层宛如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老鼠,提前觉察到了大难降至,于是就夺命狂奔。
中国这艘千疮百孔的巨轮将驶向何方?屠杀不能赋予一个政权以统治的合法性和长久的稳定,一九八九之后只能是一九八四的幽暗结局。赵鼎新在书中承认,“没有迹象表明中共高层领导当中有人想利用八九学运来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没有一个高层国家领导人愿意发动一场首先针对他们自己的政治改革,所以,时机非常重要。……世界上许多改革都引发了革命或其他动乱,原因就在于那些改革来的太少、太晚。”因此,我也深信,六四获得正名,不可能在作为刽子手的中共手上完成,而只有等待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