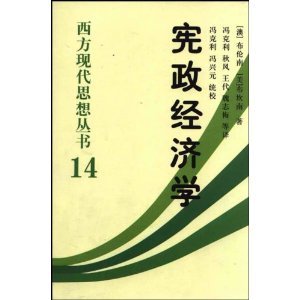
“无规矩不以成方圆”,这是人类千百年生活的精辟总结,似乎已成“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在现实生活中,不遵守规则甚至有意无意破坏规则却几乎时时处处可见,这又说明“规则”的重要性未必得到人们应有的认识。要让人遵守规则,首先要让人重视规则;而要让人真正重视规则;首先又要从学理上认真细致地论证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如何制定。著名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杰佛瑞·布伦南和詹姆斯·布坎南合著的《征税权》和《规则的理由》两书就是从经济学角度、或者说从经济学出发对人类社会的规则、制度作了深入的学理探讨。由于两书内容紧密相关,讨论的都是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宪政问题,而且后书实际是前书的进一步阐释,所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两书“合二为一”名为《宪政经济学》(2004年2月版)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
宪政的逻辑
在所有的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是宪法,宪政。可以说,宪政是制度的制度规则的规则,是生成制度的制度生成规则的规则,是“元规则”、“元制度”,对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不可能不谈宪法、宪政。对如此宏大的题目,作者不是宏观泛论,而是“小题大做”或曰“大题小做”,从“税收”入手,一点点深入,对宪政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发人深省的探讨。
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经济学:一种是告诉政府怎样才能高效征税,提高政府的收入,即向政府决策人提建议,也就是传统的“宫廷理财学”,关注的核心是任务是“提高国家财力”而不是任何约束政府“财政”的办法。另一种经济学关注的对象是纳税人或公民,也就是所有那些承受纳税负担的人,亦即那些政府财政制取权力的潜在对象的人如何参与制定限制政府的规则。作者承认:“本书所关注的是财政宪法,是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和支出权的手段。”无疑是“第二种经济学”。依此标准,中国1993年那篇引起广泛注意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则无疑是“宫廷经济学”。
历史表明,税务与宪政关系极其密切,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的直接导火索都是由税收引起的。基于此,作者阐述的税收观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其“宪法”取向,“始终把‘宪法’视为一套规则,或一套社会制度,个人在其中从事活动和交往。把这些规则比作一种博弈规则可能是有用的。”(《征税权》第3页)立宪选择是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进行的,即所有人对选择的后果都“一无所知”,这样才可能公平、公正。从霍布斯的契约论观点出发,如果没有政府或类似的权威机构,人类将陷入可怕的无政府、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为了结束这种情况,全体公民只有出让自己的权力组成政府。作者由此引出一系列问题:“全体公民有可能同意服从的政府的性质是什么。特别是,公民会自愿同意允许政府完全无保留地行使权力吗?他们是不是更愿意对政府的行为施加约束——即限制政府采取一些它本来有可能采取的行动的能力?”因为“无知之幕”使人无法预料到政府的行为,所以“宪法限制的逻辑包含在如下隐含的预见之中:授予政府的任何权力,都有可能在某些范围内和某些场合下,以不同于公民在‘无知之幕’中所规定的可欲的用途得到行使。”(《征税权》第5页)显然,作者深受洛克以降的英美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认为“政府”也与“经济人”一样,会追求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因而对“政府”深抱戒心。
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
那么,如何对政府作出必要的限制或曰宪法约束的手段是什么呢?通常认为民主选举是最好的限制方法,但作者认为这固然不错,但远远不够、依然有许多漏洞所以对政府的限制非常脆弱。因此,他们提出并论证了对政府进行财政约束的重要性,认为财政约束补充了选举约束的缺漏。这样,“税收”就从“财经”层面上升到了“宪政”层面,因为立宪层面问题的本质即是如何约束政府的自然倾向。
作者认为,政府用税收提供公民/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品是纳税的理由,但这并不是对这种征税权力本身的理解,这二者必须作严格的区分。“征税权本身并不包含着使用这些以任何特定方式征集的收入的义务。征税权在逻辑上并不隐含着支出的性质。”从此角度而言,“征税”的权力不过是一种“索取”(take)的权力。“若要坚持索取和征税两者之间的差别,税收方案必须包含一些在直接占有情况下不存在的附加要求。”(《征税权》第9页)这种“附加要求”即力图约束政府的自然倾向,使其行为的后果符合公民/纳税人的预期。因此立法过程应是社会成员、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其中的讨价还价过程。
税收解决的是控制政府的“收入问题”,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如何控制、管理政府的“支出问题”。也就是说,仅仅限制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并不够,“纳税人――受益人如何同时保证那些征到的税款被用于他所要求的物品和服务呢?一旦授予利维坦征税权,用什么办法来防止它把税额用于自己的特殊目的呢?”而且,衡量、控制政府公平地“支出”比衡量、控制政府公平地“征税”更加困难。所以,在政府的“支出”方面,必须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把信息公诸于众。做到这些,必须有一套公开的、事前定好的程序。“支出”一旦经过法定程序确定就应严格执行,并要以追问绩效和可问责性作为公平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些,政府“支出”的公平性更难保证。
这样,作者进一步“用研究市场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过程”,其中最重要之处是把政治过程视为有着互动关系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系统,由此产生出各种均衡的结果。与在合理清晰界定的规则下运行的市场过程一样,政治性选择也是从一定规则之下的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由于规则、立法必须具有普适性,所以规则的制定、立法过程必须具有“公共性”。在这种博弈中,“他们在可以利用的范围内做出选择,以便使他们的回报最大化(在这里如果在其他背景下一样,回报既包括经济方面的也包括道德方面的目标)。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对分立的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起支配作用的一套制度,是否最有利于引导个人去增进其他人的利益,或至少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规则的理由》第17页)健康的政治规则与健康的市场规则一样,互不相认的人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益在这套规则的规范下通过分工合作,在自己获利的同时也使他人获益,最终结果是增进全社会的福祉。
公正与规则
一个社会之所以要建立种种规则,除了需要秩序外还需要公正。换句话说,只有公正的规则或规则的公正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规则的秩序。不过,公正与规则的关系探究起来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作者提出,讨论公正也就是讨论相应的规则,不提规则而奢谈公正毫无意义。具体而言,公正又可分为“公正行为”和“公正规则”两个概念。所谓“公正行为”是指“规则内的公正”,即个人或机构在已经存在的规则下严格“遵守规则”的行为,不违犯参与者事先已表示同意之规则的行为,如遵守游戏规则的运动员和严格执法的裁判就可以说是“公正的”。“公正行为”的含义就是信守向其他参与者做出遵守规则的承诺,当然重要的一点是预期其他参与者也会遵守规则。
而“规则公正”即“规则应当是什么”,无疑是将公正视为评价不同规则体系的标准,不过这样说却有些过于宽泛抽象。因此,“关于规则应当是什么的决策,只能根据适用于从不同规则间作出的选择的更抽象的规则做出。这种更抽象层面的规则,我们称之为元规则。”“只要筛选过程符合公认的元规则,那么,从中筛选出的规则就是公正的。”(《规则的理由》第120页)也就是说,只要规则制定的程序是正当的,规则就可说是公正的。同样,对规则的修改只要循此原则就可以说是公正的,如同过正当程序对宪法的修订。作者的论证表明:“在这一抽象层面,众多主体将会乐于维护自愿达成之协定”,“正是这种确立道德义务的自愿达成协定的能力,推动着整个‘宪政事业’。人人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宪政秩序,使自己能置身某种恰当的环境中,以追求自己(设想中的)未来的生活计划。”(《规则的理由》第121页)
总之,作者认为对公正的考察既是价值考察也是事实考察,对“公正”的性质做出详细阐释,得出了“公正”是宪政契约论立场的自然产物这一结论。对此结论可能有人不同意,而本书的其他许多观点可能会引起各种争论和批评,但作者成功地论证了应当从宪政角度讨论税制改革,此点确难反驳。而一旦税制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就能打通值得严肃考虑的真正的税制改革的道路”。而税制的变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公民思考并参与税制改革,也是制定最基本的规则——宪政的重要方面。
虽然国情不同,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若能借鉴“他山之石”、引入相关学理,将大大减少我们的“学费”,降低我们发展过程的“成本”。
来源:思想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