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第一乐章的叙述,确切的说是第一乐章中著名的侵略插部与《红字》的叙述迎合到了一起,仿佛是两面互相凝视中的镜子,使一部音乐作品和一部文学作品都在对方的叙述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让那个插部进展到了十分钟以上的长度,同时让里面没有音乐,或者说由没有音乐的管弦乐成分组成,一个单一曲调在鼓声里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如同霍桑《红字》中单一的情绪主题的不断变奏。就像肖斯塔科维奇有时候会在叙述中放弃音乐一样,纳撒尼尔·霍桑同样也会放弃长篇小说中必要的故事的起伏,在这部似乎是一个短篇小说结构的长篇小说里,霍桑甚至放弃了叙述中惯用的对比,肖斯塔科维奇也在这个侵略插部中放弃了对比。接下来他们只能赤裸裸地去迎接一切叙述作品中最为有力的挑战,用渐强的方式将叙述进行下去。这两个人都做到了,他们从容不迫和举重若轻地使叙述在弱软中越来越强大。毫无疑问,这种渐强的方式是最为天真的方式,就像孩子的眼睛那样单纯,同时它又是最为有力的叙述,它所显示的不只是叙述者的技巧是否炉火纯青,当最后的高潮在叙述的渐强里逐步接近并且终于来到时,它就会显示出人生的重量和命运的空旷。

这样的方式使叙述之弦随时都会断裂似的绷紧了,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仿佛又在推开高潮,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培育着将要来到的高潮,使其越来越庞大和越来越沉重,因此当它最终来到时,就会像是末日的来临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了。
肖斯塔科维奇给予了我们这样的经历,在那个几乎使人窒息的侵略插部里,他让鼓声反复敲响了175次,让主题在十一次的变奏里艰难前行。没有音乐的管弦乐和小鼓重复着来到和离去,并且让来到和离去的间隔越来越短暂,逐渐成为了瞬间的转换,最终肖斯塔科维奇取消了离去,使每一次的离去同时成为了来到。巨大的令人不安的音响犹如天空那样笼罩着我们,而且这样的声音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到,天空似乎以压迫的方式正在迅速地缩小。高潮的来临常常意味着叙述的穷途末路,如何在高潮之上结束它,并且使它的叙述更高地扬起,而不是垂落下来,这样的考验显然是叙述作品的关键。
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是让主部主题突然出现,这是一个尖锐的抒情段落,在那巨大可怕的音响之上生长起来。倾刻之间奇迹来到了,人们看到“轻”比“沉重”更加有力,仿佛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一道纤细的阳光瓦解了灾难那样。当那段抒情的弦乐尖锐地升起,轻轻地飘向空旷之中时,人们也就获得了高潮之上的高潮。肖斯塔科维奇证明了小段的抒情有能力覆盖任何巨大的旋律和任何激昂的节奏。下面要讨论的是霍桑的证明,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什么,纳撒尼尔·霍桑证明了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
几乎没有人不认为纳撒尼尔·霍桑在《红字》里创造了一段罗曼史,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红字》的出版,使纳撒尼尔摇身一变成为了浪漫主义作家,也让他找到了与爱伦·坡分道扬镳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两个人都在阴暗的屋子里编写着灵魂崩溃的故事。当然,《红字》不是一部甜蜜的和充满了幻想的罗曼史,而是忍受和忠诚的历史。用D·H·劳伦斯的话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故事,却内含着地狱般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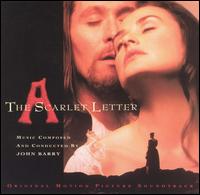
海丝特·白兰和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他们的故事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勾引和上勾之后,或者说是在瞬间的相爱之后,就有了人类起源的神话同时也有了罪恶的神话。出于同样的理由,《红字》的故事里有了珠儿,一个精灵般的女孩,她成为了两个人短暂的幸福和长时期痛苦的根源。故事开始时已经是木已成舟,在清教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海丝特·白兰没有丈夫存在的怀孕,使她进入了监狱,她在狱中生下了珠儿。这一天早晨──霍桑的叙述开始了──监狱外的市场上挤满了人,等待着海丝特·白兰──这个教区的败类和荡妇如何从监狱里走出来,人们议论纷纷,海丝特·白兰从此将在胸口戴上一个红色的A字,这是英文里“通奸”的第一个字母,她将在耻辱和罪恶中度过一生。然后,“身材修长,容恣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的海丝特,怀抱着只有三个月的珠儿光彩照人地走出了监狱,全然不是“会在灾难的云雾里黯然失色的人”,而胸口的红字是“精美的红布制成的,四周有金线织成的细工剌绣和奇巧花样”。手握警棍的狱吏将海丝特带到了市场西侧的绞刑台,他要海丝特站在上面展览她的红字,直到午后一点钟为止。人们辱骂她,逼她说出谁是孩子的父亲,甚至让孩子真正的父亲──受人爱戴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上前劝说她说出真话来,她仍然回答:“我不愿意说。”然后她面色变成死灰,因为她看着自己深爱的人,她说:“我的孩子必要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
这只是忍受的开始,在此后两百多页叙述的岁月里,海丝特经历着越来越残忍的自我折磨,而海丝特耻辱的同谋丁梅斯代尔,这位深怀宗教热情又极善辞令的年轻牧师也同样如此。在两个人的中间,纳撒尼尔·霍桑将罗格·齐灵窝斯插了进去,这位精通炼金术和医术的老人是海丝特真正的丈夫,他在失踪之后又突然回来了。霍桑的叙述使罗格·齐灵窝斯精通的似乎是心术,而不是炼金术。罗格·齐灵窝斯十分轻松地制服了海丝特,让海丝特发誓绝不泄露出他的真实身份。然后罗格·齐灵窝斯不断地去剌探丁梅斯代尔越来越脆弱的内心,折磨他,使他奄奄一息。从海丝特怀抱珠儿第一次走上绞刑台以后,霍桑的叙述开始了奇妙的内心历程,他让海丝特忍受的折磨和丁梅斯代尔忍受的折磨逐渐接近,最后重叠到了一起。霍桑的叙述和肖斯塔科维奇那个侵略插部的叙述,或者和拉威尔的《波莱罗》不谋而合,它们都是一个很长的,没有对比的,逐步增强的叙述。这是纳撒尼尔才华横溢的美好时光,他的叙述就像沉思中的形象,宁静和温柔,然而在这形象内部的动脉里,鲜血正在不断地冲击着心脏。如同肖斯塔科维奇的侵略插部和拉威尔的《波莱罗》都只有一个高潮,霍桑长达二百多页的《红字》也只有一个高潮,这似乎是所有渐强方式完成的叙述作品的命运,逐步增强的叙述就像是向上的山坡,一寸一寸的连接使它抵达顶峰。
《红字》的顶峰是在第二十三章,这一章的标题是“红字的显露”。事实上,叙述的高潮在第二十一章“新英格兰的节日”就开始了。在这里,纳撒尼尔·霍桑开始显示他驾驭大场面时从容不迫的才能。这一天,新来的州长将要上任,盛大的仪式成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节日,霍桑让海丝特带着珠儿来到了市场,然后他的笔开始了不断的延伸,将市场上欢乐的气氛和杂乱的人群交叉起来,人们的服装显示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使市场的欢乐显得色彩斑驳。在此背景下,霍桑让海丝特的内心洋溢着隐秘的欢乐,她看到了自己胸前的红字,她的神情里流露出了高傲,她在心里对所有的人说:“你们最后再看一次这个红字和佩戴红字的人吧!”因为她悄悄地在明天起航的船上预订了铺位,给自己和珠儿,也给年轻的牧师丁梅斯代尔。这位内心纯洁的人已经被阴暗的罗格·齐灵窝斯折磨得“又憔悴又孱弱”,海丝特感到他的生命似乎所剩无几了,于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告诉他和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老医生是什么人。然后,害怕和绝望的牧师在海丝特爱的力量感召下,终于有了逃离这个殖民地和彻底摆脱罗格·齐灵窝斯的勇气,他们想到了“海上广大的途径”,他们就是这样而来,明天他们也将这样离去,回到他们的故乡英格兰,或者去法国和德国,还有“令人愉快的意大利”,去开始他们真正的生活。
在市场上人群盲目的欢乐里,海丝特的欢乐才是真正的欢乐,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其脱颖而出,犹如一个胜利的钢琴主题凌驾于众多的协奏之上。可是一个不谐和的音符出现了,海丝特看到那位衣服上佩戴着各色丝带的船长正和罗格·齐灵窝斯亲密地交谈,交谈结束之后船长走到了海丝特面前,告诉她罗格·齐灵窝斯也在船上预订了铺位。“海丝特虽然心里非常惊慌,却露出一种镇静的态度”,随后她看到她的丈夫站在远处向她微笑,这位阴险的医生“越过了那广大嘈杂的广场,透过人群的谈笑、各种思想、心情和兴致──把一种秘密的、可怕的用意传送过来。”
这时候,霍桑的叙述进入了第二十二章──“游行”。协奏曲轰然奏响,淹没了属于海丝特的钢琴主题。市场上欢声四起,在邻近的街道上,走来了军乐队和知事们与市民们的队伍,丁梅斯代尔牧师走在护卫队的后面,走在最为显赫的人中间,这一天他神采飞扬,“从来没有见过他步伐态度像现在随着队伍行进时那么有精神”,他们走向会议厅,年轻的牧师将要宣读一篇选举说教。海丝特看着他从自己前面走过。
霍桑的叙述出现了不安,不安的主题缠绕着海丝特,另一个阴暗的人物西宾斯夫人,这个丑陋的老妇人开始了对海丝特精神的压迫,她虽然不是罗格·齐灵窝斯的同谋,可是她一样给予了海丝特惊慌的折磨。在西宾斯夫人尖锐的大笑里,不安的叙述消散了。
欢乐又开始了,显赫的人已经走进了教堂,市民们也挤满了大堂,神圣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演讲的声音响了起来,“一种不可抵抗的情感”使海丝特靠近过去,可是到处站满了人,她只能在绞刑台旁得到自己的位置。牧师的声音“像音乐一般,传达出热情和激动,传达出激昂或温柔的情绪”,海丝特“那么热烈地倾听着”,“她捉到了那低低的音调,宛若向下沉落准备静息的风声一样;接着,当那声调逐渐增加甜蜜和力量上升起来的时候,她也随着上升,一直到那音量用一种严肃宏伟的氛围将她全身包裹住。”
霍桑将叙述的欢乐变成了叙述的神圣,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只有丁梅斯代尔的声音雄辩地回响着,使所有的倾听者都感到“灵魂像浮在汹涌的海浪上一般升腾着”。这位遭受了七年的内心折磨,正在奄奄一息的年轻牧师,此刻仿佛将毕生的精力凝聚了起来,他开始经历起回光返照的短暂时光。而在他对面不远处的绞刑台旁,在这寂静的时刻,在牧师神圣的说教笼罩下的市场上,海丝特再次听到那个不谐和的音符,使叙述的神圣被迫中断。那位一无所知的船长,再一次成为罗格·齐灵窝斯阴谋的传达者,而且他是通过另一位无知者珠儿完成了传达。海丝特“心里发生一种可怕的苦恼”,七年的痛苦、折磨和煎熬所换来的唯一希望,那个属于明天“海上广大的途径”的希望,正在可怕地消失,罗格·齐灵窝斯的罪恶将会永久占有他们。此刻沉浸在自己神圣声音中的丁梅斯代尔,对此一无所知。
然后,叙述中高潮的章节“红字的显露”来到了。丁梅斯代尔的声音终于停止了,叙述恢复了欢乐的协奏,“街道和市场上,四面八方都有人在赞美牧师。他的听众,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认为强过于旁人的见解尽情吐露之后,才得安静。他们一致保证,从来没有过一个演讲的人像他今天这样,有过如此明智,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精神。”接下去,在音乐的呜响和护卫队整齐的步伐里,丁梅斯代尔和州长,知事,还有一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从教堂里走了出来,走向市政厅盛大的晚宴。霍桑此刻的叙述成为了华彩的段落,他似乎忘记了叙述中原有的节拍,开始了尽情的渲染,让“狂风的呼啸,霹雳的雷呜,海洋的怒吼”这些奢侈的比喻接踵而来,随后又让“新英格兰的土地上”这样的句式排比着出现,于是欢乐的气氛在市场上茁壮成长和生生不息。
随即一个不安的乐句轻轻出现了,人们看到牧师的脸上有“一种死灰颜色,几乎不像是一个活人的面孔”,牧师踉跄地走着,随时都会倒地似的。尽管如此,这位“智力和情感退潮后”的牧师,仍然颤抖着断然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搀扶,他脸上流露出的神色使新任的州长深感不安,使他不敢上前去扶持。这个“肉体衰弱”的不安乐句缓慢地前行着,来到了绞刑台前,海丝特和珠儿的出现使它立刻激昂了起来。丁梅斯代尔向她们伸出了双臂,轻声叫出她们的名字,他的脸上出现了“温柔和奇异的胜利表情”,他刚才推开老牧师威尔逊的颤抖的手,此刻向海丝特发出了救援的呼叫。海丝特“像被不可避免的的命运推动着”走向了年轻的牧师,“伸出胳膊来搀扶他,走近刑台,踏上阶梯”。
就在这高高的刑台上,霍桑的叙述走到了高潮。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属于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尖锐地剌向了空中。他说:“感谢领我到此地来的上帝!”然后他悄悄对海丝特说:“这不是更好吗。”纳撒尼尔·霍桑的叙述让丁梅斯代尔作出了勇敢的选择,不是通过“海上广大的途径”逃走,而是站到了七年前海丝特怀抱珠儿最初忍受耻辱的刑台之上,七年来他在自己的内心里遭受着同样的耻辱,现在他要释放它们,于是火山爆发了。他让市场上目瞪口呆的人们明白,七年前他们在这里逼迫海丝特说出的那个人就是他。此刻,丁梅斯代尔的乐句已经没有了不安,它变得异常地强大和尖锐,将属于市场上人群的协奏彻底驱赶,以王者的恣态孤独地回旋着。丁梅斯代尔用他生命里最后的声音告诉人们:海丝特胸前的红字只是他自己胸口红字的一个影子。接着,“他痉挛地用着力,扯开了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让人们看清楚了,在他胸口的皮肉上烙着一个红色的A字。随后他倒了下去。叙述的高潮来到了顶峰,一切事物都被推到了极端,一切情感也都开始走头无路。
这时候,纳撒尼尔·霍桑显示出了和肖斯塔科维奇同样的体验,如同“侵略插部”中小段的抒情覆盖了巨大的旋律,建立了高潮之上的高潮那样,霍桑在此后的叙述突然显得极其安详。他让海丝特俯下面孔,靠近丁梅斯代尔的脸,在年轻的牧师告别人世之际,完成了他们最后的语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最后的对话是如此感人,里面没有痛苦、没有悲伤、也没有怨恨,只有短暂的琴声如诉般的安详。因为就在刚才的高潮段落叙述里,《红字》中所有的痛苦、悲伤和怨恨都得到了凝聚,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压迫,压迫着霍桑全部的叙述。可是纳撒尼尔让叙述继续前进,因为还有着难以言传的温柔没有表达,这样的温柔紧接着刚才的激昂,同时也覆盖了刚才的激昂。在这安详和温柔的小小段落里,霍桑让前面二百多页逐渐聚集起来的情感,那些使叙述已经不堪重负的巨大情感,在瞬间获得了释放。这就是纳撒尼尔·霍桑,也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用一个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高潮段落,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拯救,需要在越来越沉重或者越来越激烈的叙述里得到解脱。同时,这高潮之上的高潮,也是对整个叙述的酬谢,就像死对生的酬谢。
来源:西方音乐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