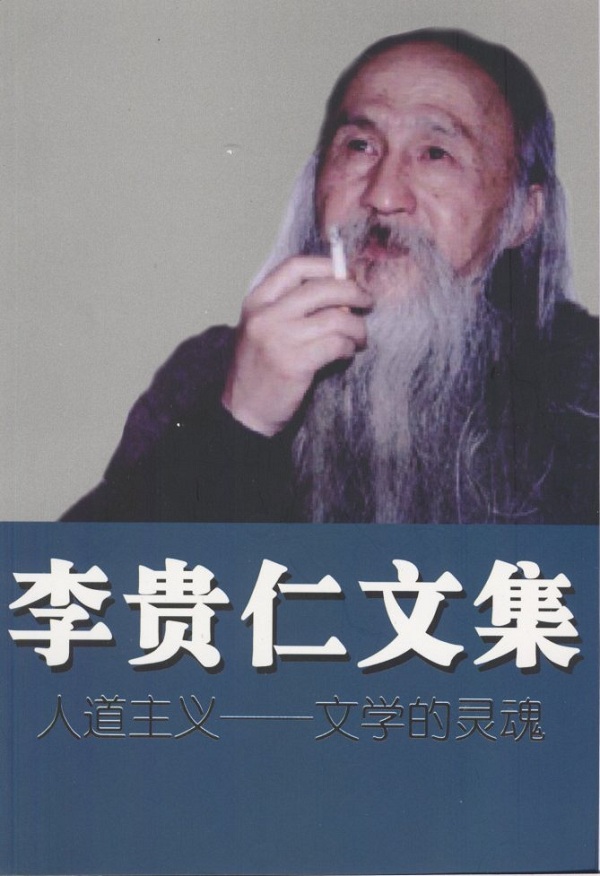“写真实”和“写本质”,作为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本来都是对的,它们二者也完全可以达到一致;但在我们的文艺批评中,它们却常常被搞得互相对立,而主要倾向则是鼓吹一种特定的“写本质”论,用以否定和反对“写真实”的正确主张。症结何在呢?计永佑同志一语道破了实质:“归根到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写光明与写阴暗面的问题。”那么,“写本质”论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同样被计永佑同志一语道破了:“要真实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侧重写光明。……因为阴暗面并不规定中国社会的本质。”(《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
作为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参加争鸣的权利。然而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种以只许写光明为特定内容的“写本质”论,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实实在在只是一根棍子!它被奉为法典挟制作家,用作法宝戕杀作品,滥施淫威,煞是可怕。而尤为可怕的是,此风相沿成习,于今不衰,其积弊之深,绝非旦夕可除。不是么,二十多年前,一批敢于揭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作品,正是在这个“写本质”论的圣殿阶下被宣判死刑的;如今,好不容易翻了此案,使它们成为“重放的鲜花”,就马上又有一批敢于揭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也被推到这个“写本质”论的圣殿阶下,要宣判死刑了。《时代的报告》评论员和漠雁否定《在社会的档案里》,燕翰和田均、梁康否定《飞天》,等等,就是一个又一个明证。这些“革命性”强得惊人的批评家,就因为这批作品不合他们那个“写本质”论的规范,便断然判定这批作品“宣扬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其目的“是为了动摇新制度的基础”云云;有人甚至公然喝道:不许以揭露阴暗面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呵,问题竟被搞得如此严重,我们不是分明看到和听到“写本质”论作为一根足以致人死命的棍子,还在舞得飕飕响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铁一样的事实,无视它是可笑的,回避它是愚蠢的,否认它则是荒唐的,而听任和放纵它去发展,就更是危害无穷的了。
(全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