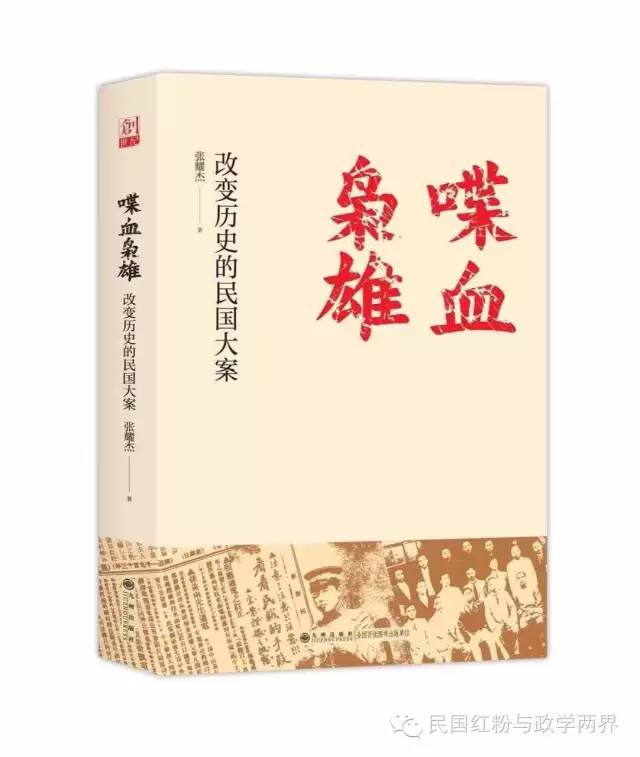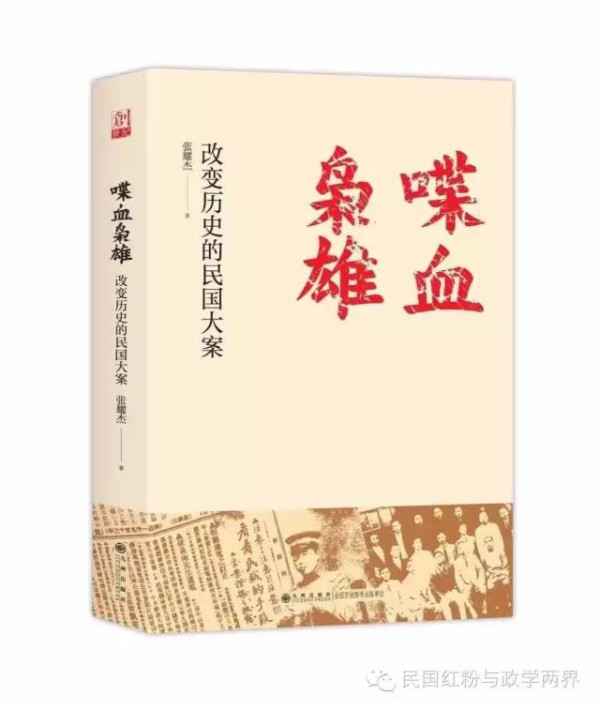 辛亥革命对中国国运与民生产生的巨大影响世所共睹。有人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而顶礼歌颂,有人为辛亥革命中断立宪扼腕叹息;有人认为革命带来了新天新地,有人批评革命造成了失范、失衡。
辛亥革命对中国国运与民生产生的巨大影响世所共睹。有人为辛亥革命建立共和而顶礼歌颂,有人为辛亥革命中断立宪扼腕叹息;有人认为革命带来了新天新地,有人批评革命造成了失范、失衡。
近年以来,随着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著作不再对这场革命进行流于表面的价值评价,而是力求进行客观而全面地深描,展现这一重大事件的复杂面相。张耀杰先生近期出版的《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便是这种努力的代表。
张耀杰先生批评“家国一体、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及皇权专制的传统文化”,因它造成二元对立、单边片面及惯于区分贤吝、忠直、正邪的脸谱化史观。因此,他在《喋血枭雄》一书中抛弃简单立场,通过挖掘和整理史料,对辛亥前后发生的与革命党有关的一系列重大命案细节加以钩沉,以求为读者认识辛亥革命与辛亥人物提供新的视角。
枭雄陈其美以权欺法
此书名为“喋血枭雄”。窃以为,“枭雄”者,首先系指陈其美也。因为此书的论述围绕陈其美这一革命巨头、地方军阀、帮派强人的故事展开。此书探讨了陶骏保、陶成章、周实、阮式、宋教仁等一系列命案。在这些命案中,陈其美或为幕后主谋(如陶骏保、陶成章案),或是左右案件审理的重要力量(如周实、阮式一案),或被指为疑犯(如宋教仁),甚至最后自己还成为命案中的死者。因此,将此书视为陈其美这一民初枭雄的评传亦无不可。
而另一方面,本书似又不止于展现陈其美的传奇人生,而是对陈其美和牵涉诸案的多方力量、各色人物均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北洋中枢、清廷旧臣、革命党团、地方督抚、军阀警督、黑帮刺客以及租界中的各种力量在命案中的举动莫不梳理,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程德全、张宗昌、王金发、应夔臣等人在各案中的角色莫不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所呈现的是革命前后暴力冲突中的枭雄群像。
在如此繁多的人物和事件背后,《喋血枭雄》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即辛亥革命中力与法的冲突。作者在论述各个命案的前因后果以及时代背景时,一再涉及的现象便是革命党人(以陈其美为代表)通过帮派与军警,或黑或白、或明或暗地使用强力,以违背法治的方式追求其自身的目的。这种力量,在暗则为操纵帮派的暴力(包括革命党人亲身组建的暗杀团体),在明则为统摄军政的权力。
在暴力与法的冲突方面,《喋血枭雄》还原了上海光复后陈其美通过“敢死队”武力胁迫当地绅商强行出任沪军都督的经过。这支“敢死队”以帮派份子刘福彪为司令。刘氏不仅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目为罪犯,而且在革命军中不改江湖习气,以割耳、插箭等酷刑管理士卒。在上海绅商代表集会选举沪军都督时,刘福彪等人携带枪支、炸弹力挺陈其美,二者的关系可见一斑。
争夺沪军都督时陈其美还只是发出死亡威胁,并未采取实质行动,但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他竟连续痛下杀手,枪决江苏都督府参谋次长陶骏保,暗杀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等人。对于这些命案的影响,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和同盟会据此巩固了强势地位、扩张了势力范围、威吓了其他势力,然而,也造成暴力恐怖、相互残杀的局面,败坏了法治,也损害了同盟会自身的名誉。
在权力与法的冲突方面,《喋血枭雄》中周实、阮式一案则为明证。周实、阮式均为南社成员,在鼓动山阳县光复之后,为前清旧臣姚荣泽所杀。后来姚荣泽被执,孙中山亲令司法总长伍廷芳组织审判。伍廷芳以“民国方新”,意图“展示民国司法气象”,力主“文明审判”。而陈其美则为报同志之仇,亟欲对其严惩,在组织审判期间与伍廷芳笔战数次。
在此案中,陈其美以权欺法的行为不一而足。本来,根据地域关系,姚荣泽一案应由江苏都督程德全管辖,然而陈其美和柳亚子等南社成员则一再敦请,终使孙中山以总统身份下令将姚押解至沪。在组织审判时,陈其美首先便绕开伍廷芳单方面委任军法司总长蔡寅担任审判庭长,遭伍拒绝,则又借口已经登报欲造成既成事实。后在伍廷芳的坚持之下,定由陈贻范、蔡寅和丁榕三人出任法官。
此后,陈、伍二人还围绕是否允许外国律师出庭辩护一事发生激烈争论。伍廷芳为此撰写长信,对自己的主张详加解释,而陈其美则揶揄伍廷芳“斤斤计较”“以博虚誉”。最后伍廷芳忍无可忍,明确批评陈其美对姚案早有定见,立场不公,又指陈对于司法事务横加干涉,有违三权分立,表示以后“不必再辩”。
此案之后,陈其美与伍廷芳的冲突愈演愈烈。伍廷芳严厉指责陈其美擅用军警滥捕政敌是“藐视司法,侵越权限”、“迹近蹂躏民权”的“强盗之行为”。而陈其美和其他革命党人也对伍廷芳坚持法治的做法嗤之以鼻。不久,伍廷芳自觉“心力交瘁”,黯然辞职,为革命政府的司法建设留下一个尴尬的注脚。
法驯服力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根据张耀杰先生的论述,抛开革命党人所欲追求的目的为何不论,他们以力犯法、抗法甚至乱法的事实是存在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力、法之争呢?
强世功教授曾在《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一文中指出,革命意味着暴力,而法治则驯服暴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革命与法治之间天然存在张力。笔者认为,暴力只是革命的一面,革命与暴乱不同,革命的目的不是毁灭秩序,而是要建立新的秩序。辛亥革命的目的在于摧毁专制的法制,进而建立民主的法治。这是一破一立的过程。
然而,破不易,立亦不易。因旧秩序不易撼动,革命党不得不采用暗杀、起义等暴力方式加以冲撞。旧秩序既倒,“秦失其鹿,豪杰竞逐”,包括革命党人在内,莫不想大权独揽,于是彼此杀伐、刀光剑影。
况且,强力(包括体制内的权力与体制外的暴力)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本能,而新的法治秩序则是要限制强力,将其关入牢笼。已经手握强力的枭雄岂会轻易束手就擒?因此,在革命之后,法驯服力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毫无插曲。
力与法的冲突不独辛亥革命有之,放眼其他国家的革命,类似情形亦不在少。要实现法治的秩序,除了需要主观上树立对法治、宪政等观念的信仰之外,客观上还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均衡与妥协,最后服膺于一个共同接受的盟约,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障宪政和法治。西谚所谓“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正是此意。
在《喋血枭雄》一书中,最令人惋惜的一案乃是宋教仁案。当时南北已经议和,《临时约法》早已通过,《天坛宪草》亦正起草。正在首届国会选举成功之际,宋教仁却横遭暗杀。而宋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又无视已经启动的司法程序,拒绝通过法律解决此事,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辛亥革命后建立的短暂秩序再次崩坏。
有人会问,为何《临时约法》也无法制止这次悲剧的发生呢?难道政治盟约也无效吗?其实问题恰恰出在《临时约法》上,因为它难以发挥政治盟约的作用。如上所述,所谓政治盟约,当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与妥协的结果,它反映各方的实力与利益,也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然而《临时约法》却不是。该法由南京政权所立,全无北洋方面的参与,其目的仅在为国民党抓权,对袁世凯限权。试问这种约法以及它所建立的秩序怎会让袁世凯诚心接受?
所以,《临时约法》徒有宪法之表,其里则是党争的工具而已。意图通过这一约法来建立宪政、实现法治、驯服强力,只能是一厢情愿。辛亥革命以后依靠《临时约法》所建立的秩序并不牢固,即使没有宋教仁遇刺,即使孙中山不因此发起“二次革命”,孙、袁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在日后以其他形式爆发。只是,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带来的伟大成果遭到这样一场血案和革命的打击,终是使人遗憾。
辛亥革命有其不足,《喋血枭雄》为我们展示了它的一个侧面。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绵延千年的帝制,打开了中国走向共和、民主与法治的大门。这个过程势必漫长而艰难,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言的“历史三峡”一般。我们必须坚韧、弘毅地走完这段路程,将强力关进法治的牢笼,使革命的成果为每个国民所公平地分享。这是革命者及其后继者的任务。
(作者系旅美法律学者)
来源:《法制日报@法制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