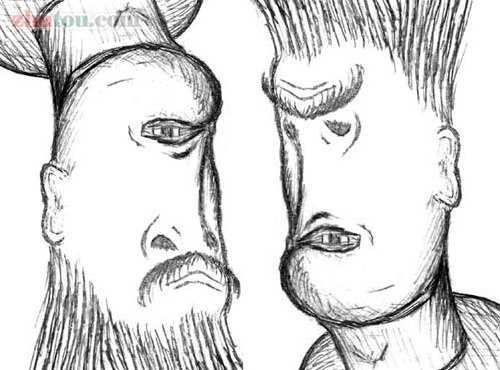
网络图片
我在韦伯论官僚制的著作中读到,无政府主义其实是文明历史以来亘古就存在。有秩序就有反秩序的,反秩序的,往往就是渴望加入秩序而不得被抛弃出来的结果。
Baechler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起源》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源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雅法指出美国政治的基础就在于无政府主义。从人作为人的条件来看,其政治经济都源于无政府主义。现代性正是把自己奠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地基上,不断反对不断否定是其路径。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与组织的关系,始终没法像作为例外的美国宪政这样做出比较终局性的安排。
每一个基督徒都认为自己在上帝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应该是例外的。失序的民众与沉沦的小资产阶级,其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反对现存秩序,然而其进入行动层次,就要遭遇组织问题。
二十世纪模仿美国精神的极权主义组织都有着美国之心,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把美国政治神学占为己有,在超越美国渴望中体现为更极端更急躁,就像该隐之于亚伯。美国以宪法来终结革命,并且以继续革命,极权主义组织以组织来内化革命,并继续革命,也就是政治救赎和革命之弥撒亚都在秩序内运行。美国政治除了军事外交外,都世俗化成了治安,而极权主义如中共除了与外敌交集的军事外交外,凡是内政都纳入组织,成了组织体系内组织性事务。即使是民众运动也仅仅成了党内运动,党外无政治救赎,党外无政治。
极权主义政教合一党组织攫取了所有的行动,变为纪律服从与执行,也就是行政吸纳了政治。即使无政府主义加入极权主义组织,他的行动消失了,只能退化到立场,以立场代替行动,同时补偿以组织体系内的升迁,来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那么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渴望,被阉割后,党组织提供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外,想行动的,要么被消灭,要么只能投射,以文化和心理作用的方式投射于党组织身上,有什么的革命理想,有多美的旗帜,如自由民主,就像上个三十年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玫瑰色的梦幻马上破灭。毛泽东在延安反对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投射,是永远不会或极难变为政治现实的,而且往往南辕北辙,就像一个怀着伟大爱情理想的妓女,越投入距离理想越远。
现代性秩序建立于,根基于反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力量之上,一切人间坚固的,都会或即将烟消云散,故只有在当下预支于未来秩序,建立的秩序,才是暂时稳固的,能用一段子时间的。圣经中基督授予彼得的权柄,是预备于将来神国才有的。而且暂时稳固下来的秩序,也会带来反对它的后果,都会是生产掘墓人的,正如资本主义就生产了它的掘墓人。
那么要克服暂时稳固下来秩序的不利后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腐败既得利益化,就要在当下就有反对党机制,来随时提出另外的可能,随时替换掉。这样暂时稳固下来的秩序,就吸纳反对的力量,而越加普遍有容乃大起来。人心向往自由,再美好的秩序,都是一种约束,都会有反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产生,要么排斥镇压,要么以反对党的方式吸纳。
民国的反对党
抗争总要胜利目标来支持。对胜利和目标,持悬而不决的态度,似乎不是进入政治的姿态。无政府主义与民国张力,还是要决断的,宁可有所牺牲其他可能性,做出替补性安排。以反对党同时在场或民国之民族国家帝国性来预备替补性安排。
民国历史包括49年前的,和现在的但即将过去的民国历史,它是为了打开未来民国宪政之完满路而对我们重要,如果不能打开或者被认为不能打开,当然要以反对党精神攻击,甚至抹黑之,例如孙中山的独裁倾向。
新教徒抵抗罗马天主教时,总是个人主义的或者个体的,但总是以新教会或者教会联盟的名义。被专制所原子化的个体,起来反抗总是无政府主义者,当他要获得普遍性时,总会带各种各种各样,传统的或者现代的群体性帽子,如知识分子道统身份。但是我认为忠实于政府主义而且最靠近普遍性的,就是永远的反对党。
太阳花运动及其社运政党化的第三势力,在民进党还是反对党的时候,构成对反对党的监督或者发对。这是台湾社会内部的边缘反对主流,社运反对政党。这是宪政里面的创新。这种创新遏制了民进党执政后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同效应,避免民进党变为新的国民党。例如当时本来民进党就开华山会议要冻结台独党章,结果就停住了。拖住后退,不让变质或者向对方倾斜。
当大陆党内民主派和自由派已经三十余年,作为中共的反对派存在,积累沉淀,同时僵化,同样需要第三方异质力量来做内部的反对。内部的反对比内部的支持更加能壮大力量,因为不管内部如何矛盾,中共都知道总体上是反对中共的,而内部反对比同一种声音更能吸引有差异的人参与,从而数人头更多社会基础更大。
反对派让对手调定格。就像散居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活在自己的法律宗教社区中,回避所在国的政治,其不追求但散发造成的不自觉影响,呈迷糊状态,而只有反犹主义的残酷指责和阴谋论妖魔化才能帮助其真正显现出来。
基督教在民国的巨大政治性作用,只有基督教会的反对者非基运动以及其继承人中共在49后的残酷镇压,才能反面折射清晰出来。民运在改革时期怀着宪政目标被迫适应中共改革路径,去政治化把宪政隐藏起来,好像光讲路径的主义不讲目标,然而其批判者新老左派通过批判,就把他们的政治意图给暴露定格了。
在执政党与反对党对立的格局里,模糊混淆的中间地带容易造成执政党的扩大,反对党主体性的瓦解,所以一定要在迷糊混淆的灰色地带制造分裂,拉开距离,放弃一些对方拉力大亲缘性强的,例如中共和改革,拉回一些对方排斥的,界定为准敌人的,例如改革的受害者,放弃与拉拢,资产重组,以明晰自己的反对党身份地位。反对党所拉拢的,执政党就会进一步放弃,反对党所放弃的,执政党就会进一步拉拢,互相调整以界定自己的不同主体性。
民国以来的内部政治矛盾,简单化约地说,是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统治与人民主权的矛盾,也是代表权带来的矛盾。也就是王朝政治,国民党蓝朝,共党红朝在现代性中的延续带来的现代性危机。民国以来民众与知识分子政党的关系,需要理顺,到底谁是主人,谁是附属。组织不了知识分子政党成为主人统治者,就要让知识分子集团内部,老年人和年轻人,主流与边缘之间狗咬狗,也就是需要反对党制度。民初有这种常识和尝试,拐弯在孙中山1913年的革命党出现,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间,国共之间即使内战,同时隐含着革命党放下武器转化为反对党的隐隐倾向。
于是当下时钟又拨回1911到1913年的民初,和平统一与内战又在分叉路口,在大中华框架国共合作的和平转型,与国民党共党互为反对党的框架是一致,然而又存在对共党发动的内战的必要,只是这种内战有可能是宪政化的。
政府主义反秩序力量,叫做毕利蒂希,秩序叫做利维坦。这是两个《约伯记》中的怪兽。当然如果不是像美国那样植根于,建立于无政府主义之上的政体,没法容纳反对党。现代性秩序,以及作为反方案的反现代性秩序,受基督精神的支配,都是在预备主的路铺直主的路,以靠近基督的方式或者反基督的方式。前于耶稣新纪元的秩序力量,要想成为现代性中反方案,以镇压无政府主义反秩序精神,就必须模仿基督,成为敌基督,敌基督为基督做工。反方案,如民国后的士大夫及其共党教育专政继承人,它会是暂时维稳的秩序,它是滔滔不绝奔流河流上堵塞形成的堰塞湖,自己炸开,拓出更宽河道。
这是一种利用过去历史和现实惯性力量,镇压并不吸纳无政府主义反秩序,敌基督者往往是被迫的,屈服于必然性的,如康有为为了对付民国初年的国体危机,就要利用儒家搞成儒教。但是必须看到,这一些被利用起来的传统惯性力量,正好是革命所要干掉的,他们是阻挡者,是现代性目标的敌人。一时急迫利用它,为了最后还是要战胜摆脱它。如毛泽东没有办法,把自己关在屋里里面一个星期,学习苏联搞起国内殖民工农业剪刀差。
既然是不得不的,被迫的,那么就要同时有个可撤销它的力量,来替补,来修补其恶性后果。这还是反方案,现代性秩序本身即使容纳反对党,其看不见的后果在于何处,也是要预防的,所以也要让反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反秩序力量,以反对党方式在场。也许后果就在民族国家之外,也许就在政治终结消解的时刻里,所以马克思之国家死亡政治死亡,也可以以反对党的方式在场。
无政府主义也是有建构的,不过就是藏在黑暗中。毁灭与建构,本来就是命运双生子,为了建构什么,才有毁灭。从现代到后现代,我不认为后现代是单纯毁灭,而是回归到原始的。
美国电影《2012》洪水灭世中有个一直批评人类,穿的破破烂烂的先知般人物查理,我觉得就是人类秩序终结政治死亡时的反对党形象。正如这个反对党所竭力避免的,如果在场,也许就能延迟秩序终结的后果降临。
查理说,诸位真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眼前的景象。真希望你们此刻和我在一起,快来吧,千万要记住,是查理,最先告诉你们的。
太美了,我要留下来/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最后一天/明天全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我正看着地球在眼前土崩瓦解/超级火山扬起的火上会首先笼罩拉斯维加斯/然后是圣刘易斯,然后芝加哥/最后华盛顿特区的灯光将会熄灭/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诸位真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眼前的景象
尼采论述了现代性中的怨恨。这无政府主义,就是怨恨,既然有怨恨,那么就有爱。查理即使灭世态度,那么也是让这个世界更完全。也许这个更完全就是彻底的虚无彻底的死亡,死亡也是更大的超越,“无”是“万有”。我看《剑仙奇侠传》中的拜月教主,看见不得这个大地的有限性,就想毁了重建。无
专制的无政府主义基础
国内的新左政治意识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体制内右派的也一样。毛统治下的政治意识都是,即使强调服从组织,国家的,底色或者生命意识都是无政府主义。不管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只要剥开其内核,去考虑他们为什么那么说的时候,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
毛式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基因,来自他们皆是以美国——民国为命运,反抗这命运的暴民。民国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是共党的底色,其组织性背后的生命意识,也是这样的。在意识形态下面的生命意识,揭开迷雾,就看的清楚。与俄国一样,毛在延安时反对自由主义。
有个理解的钥匙,如与列宁争论的那一些人,如卢森堡,就在于无政府主义精神与组织的关系。毛从无政府主义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组织手段。
无政府主义者其意识形态和理论是不重要的,而其后面的为什么,是重要的,也可以说放在存在主义中,才得以理解。丁玲他们去延安的,就是民国秩序中的失范者,被秩序抛弃的暴民,以左翼道德文人的面目出现,“娜拉”一旦出走,就成了组织胯下的“性奴”。这一批“性奴”,如“周扬”到了八十年代就开始切割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就是无意中在恢复无政府主义及其组织问题之间的冲突:组织是异化,是坏的。
植根于无政府主义之上的反对党,在我看来,是反秩序的抗争同时在场,不被延迟或者隐藏在黑暗中,而在阳光下显示出来,并列供挑选。反对党就会替代道德化,因为道德化总是弱能力,以至于动用大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暴力,来镇压反对,并把服从病态地提升为绝对律令。反对党就意味着,政治秩序是建立在可以推翻的前提下,人民在场,奠基于革命权之上。人民主权就是意味着否定。这时候,决断的标准,就回归于原初的“好”与“坏”,而不是道德化之后的善与恶。在“好”与“坏”的决断标准中,就容易揭开意识形态的谎言,直面生命意识本身。
无政府主义者是永远的反对党,是永远的批判者,如果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时候,就是以批判为工具重塑人际关系,寻求身份平等的承认,贬低他人或者把他人从高位拉下来,把自己抬上去。批判了别人远离目标,就会产生真理在我感,自己与真理二位一体,虽然实际上更远更背离,但因为是投射移情心理的巫术活动,足以虚幻地维持。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同时在场的,并不是局外人,例如公知批判时局久了,就会给自己虚构一个政治局中的身份:在野常委。
无政府主义是永远的弱者,因为即使在人际关系中地位身份再高,为王,为“独一人”,他就必须面对命运,必须与天斗,在命运面前,在更高者至高者面前,他永远是弱者,是可怜的人。在弱者面前装强者,这是自我保护。49后毛找斯大林抱怨,是自己说话没人听,很边缘,斯大林安慰他,毕竟是胜利者。
到了红二代之后,相对于民国,他们有征服感,有战利品的感觉,可是红一代就不一样了。1966年毛发动文革时,还恶狠狠的说,要与国民党斗争,也许民国自己都觉得自己沦陷了败了,毛泽东还觉得自己还是被压迫者,民国以及沦陷在大陆的民国要素是很强大的,他们的命运是可悲的。坐井观天的人和设置陷阱的人,是两码事。后者会永远活在他们一生所抗争的对象的阴影里面,其命运以美国-民国为象征的民国底层无政府主义者,注定要与命运搏斗,与天搏斗,与人搏斗,要阶级斗争。没有了敌人,也要制造一个稻草人来当。
统治专政于已经被征服的,与继续与不可征服的搏斗或就屈服,是无政府主义弱者的特性,继续与不可征服的命运搏斗,为了搏斗的需要或者为了转嫁恐惧,都会紧紧抓住已经被征服的。同样如果屈服于不可征服的,那么也需要从已经被征服的哪里暴虐获得补偿,这就是在外面混不好就回家打老婆孩子的道理。共党的人,在反美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想与美国并驾齐驱,并列而不得的又爱又恨。在命运面前的,所反对的秩序就是命运,只要给予同时在场,就很容易纳入反对党框架。如果大英帝国国会给美洲大陆几个议员资格,独立战争就不会爆发,这是麦迪逊说的。如果法国三级会议,给第三等级几个议员,同样法国革命也不会爆发。
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纪律,等级,对他来说,一切形式的理智至上主义都对生活充满敌意。这是一个天真的狂暴武士。自然与组织性有着根本的冲突。可是当他一旦进入政治,就极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列宁,正是其天真狂暴会摧毁会对现实约束性条件的审视能力,如果缺乏自我反思避免进入政治,止于工团,而避免有组织强迫和等级出现的政党,那么就会滑向另外一个极端,正是其天真狂暴,被毒太阳灼伤,而在光下黑,在战争和敌人逼近的例外状态,不管多么等级森严组织残酷,都能被忍受,因为跳出等级和组织就意味着死亡,为了生存可以忍受不自由,为了胜利,可以忍受残酷牺牲。俄共是一个敌基督教政党,它同样共享弥撒亚主义,有着命运作为随时吞噬掉他们的敌人,为了胜利,无政府主义者会赞成纪律,并且不断内化为自由。丁玲说过,必然性就是自由。一个无政府主义关在监狱久了,会认为监狱就是自由,外在世界的可怕和残酷,会迫使他把内心自由,安全秩序和身体欲望的满足,当作自由,神秘主义的理解。
十二月党人政变失败后就是在沙皇身上投射“无限自由”。有着强大的敌人,随时吞噬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之间就必须抱团,“我们性”,是我们的组织,虽然极权,只要是我们的,也能忍受,革命党吃掉儿女,我的理解是只要不吃掉,折磨折磨还是不会背叛的,还是爱党的。只要是我自己的,我们的,就很容易免于自我批判,提灯自照。孟德斯鸠说这是禁忌的自我豁免。无政府主义者让自己免于自我批判,同样也是无政府主义精神,同样是对理性批判对他构成压力的摆脱,自我批判的理性一样是一种理性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反对“自由主义”,就是要用组织模式格式化无政府主义。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八九后引进市场经济,一样是格式化无政府主义。可以有,但是要党的不同时期的安排而有,自己生命长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是野草,要割得整齐,为组织所用,组织不同时期要什么样的,就要长成什么样的,超出部分割除整齐。
49后右翼的无政府主义好说,也好观察,他们有着主奴辩证法的巫术,不断阐述党组织的右翼原教旨主义,从而把自己们当作党组织的主人,胡耀邦赵紫阳作为总书记的出现,给此“盖棺定论”,因此他们反毛不反党组织,毛不是自己人的,而党组织可以是,这里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党组织控制下面的人,而是抱成一团,可以控制党组织的人,而组织体制的问题得以淡化,需要批判和揪问的是,自己们或者可以构成自己们的党内人士的立场伦理问题,他们的立场伦理,构成党内良知,对组织和体制之间保持无政府主义批判,这是现代性秩序建立于,植根于无政府主义的特殊状态,换成通用的俗语,就是威权是通过不断瓦解专制总体性而得以维持。
对左翼的理解,可用前面巴枯宁和列宁之间张力的论述,他们是被组织完全吸纳身体的人,正如铁道部长刘志军说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党的。右翼与党组织之间有一定张力,他可以想象自己是超越的,有良知而有历史归属,而左翼被完全吸纳,同样也需要心理补偿,这就是党内资源的等级分配,也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同样需要内心渴望的平息(内心自由),安全秩序感和物质欲望的满足为补偿。无政府主义变为党组织控制下,有等级的,附加社会荣誉的消费主义。
是否有一个不根据偶然和暴力,而根据人民意愿和理性可更换的政府,足以奠立和颠覆宪政体制。汉密尔顿自豪于美国政府可根据人民意愿和理性更迭,说先进于世界五百年。只有政府可更替,才能有反对党制度。只有政府可更替,民众不满而激烈社会动荡时,可以通过更换领导人和解散政府,来化解群众运动的不理性和巨大冲击力。政府不可更替,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制度化条件,宪政秩序就很容易发生内战。
德国历史上的反民主主义潮流反秩序者很强大,最大抵达现代性危机之顶峰法西斯主义,是为宪政秩序因为完善的需要而极端行动,走向宪政的反面,是宪政秩序之极大张力中的内战,纳粹也正是以魏玛共和的法权之下走向反面。若不是一战后的国债压力和经济危机,我相信反对党机制和不断更替的政府,可以维持宪政秩序。正是国债和经济危机中,不断政府更替加剧了危机。而此时的政府更替是为前共和的专制政府不可更替买单。
宪政秩序之下捍卫者与反秩序者,其实已经在一个屋檐下,同一轭中,他们是在同一共同体和同一法律体系下的“内战”,对话语权和统治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可以撕裂,也可以成就,只要有共同体目标高于话语权,主权高于统治权,前二者不为后二者所吞噬,而变得“教会之外无救恩,组织之外无政治”,那么就可以成就,吞噬往往就是以“立场”替代行动,从而窒息行动造成的,此时就没有了反秩序的反对行动,反秩序的激情能量被转化为在现秩序内获取身份承认,重塑主奴关系,最后取缔了反秩序的维度。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1/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