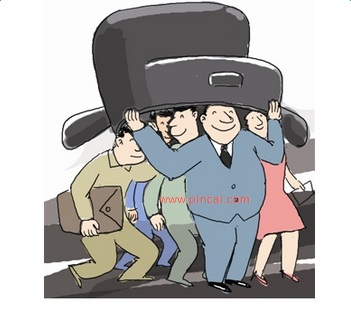
派系斗争(网络图片)
七
江泽民的破格升迁打破了1949年以来的“接班人”遴选惯例和1981年以来的总书记任职惯例(此前,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在获得接班地位或总书记职位时均已担任政治局常委,华国锋成为“第一副主席”时虽不是常委,但已是国务院代总理且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验,而江泽民在天降恩宠之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未曾有过一天中央工作履历)。在中共党史上,大概只有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名义党魁)被杀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由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担纲“临时中央”可与之相比拟。如果没有“八九风波”,这样的高层异动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此亦可见1989年的红色恐怖对党内派系政治的扭曲有多么严重,对胡赵时期所形成的中共高层政治生态的破坏多么具有摧毁性。
1989年5月16日是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政治同盟破裂的日子。那一天,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披露了“十三大后重大问题仍然由邓小平掌舵,重要决策仍需向邓小平报告和请教”的党内“秘密”(其实这一事实举世皆知,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邓对赵的公然“出卖”感到惊愕并怒不可遏。邓及其家人认为,赵紫阳此举意在煽动民主抗议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知识分子将矛头转向邓小平,是“引火烧邓”、“保赵倒邓”。邓榕当晚就打电话气势汹汹地质问了赵紫阳,赵百口莫辩,从此邓赵关系不可挽回。此前,邓小平虽对赵紫阳在学潮中的宽容姿态不太满意,但基于多年来对赵的信任与支持,仍然同意给予赵“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案留出足够的实施时间和施展空间。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的大秘书王瑞林曾要求赵在“五四讲话”中加入邓小平一贯关心爱护青年的内容,说明“四·二六社论”作出“动乱”定性之后邓仍在犹豫、观望,并未下定大开杀戒的决心。但5月16日赵戈会“泄密”之后,赵立即被邓所抛弃,赵的和平解决方案亦被同时抛弃。5月19日北京戒严,20日赵紫阳被软禁(一直被软禁至死),22日江泽民被秘密确定为赵的继任人选,十二天后“六四”惨案发生。
人们没有想到,没有一天中央工作经验、也没有政治野心、早就做好了两年之后在上海退休养老准备的普通政治局委员江泽民,成了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屠杀事件的最大受益人。据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做出用江泽民(而不是现任常委李鹏、姚依林或乔石)顶替赵紫阳的决定用了五个小时时间。然后,邓小平对被召集到他家里开会的八个元老说:“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于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其他人有什么看法?”结果当然是全票通过。五月底,邓召见李鹏、姚依林,此二人在学潮、民运期间立场坚定,始终站在强硬镇压路线一边,且利用学潮倒赵成功,本来是满心指望顺位接掌总书记、总理职务的,不料白忙一场,替他人作了嫁衣裳。邓告诫二人“不要搞小派、小圈子”,不要对平白无故夺走大位的江泽民不服气,“要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此即所谓“核心”概念的最初版本。
邓小平之所以接受了陈云、李先念推荐的江泽民,一是街头运动事态危急,高层换马事出突然,邓来不及仔细考察、从容选择其他的人选,二是与毛泽东相中华国锋的理由一样,江泽民与当时因学潮、民运而愈益复杂、微妙的高层权斗没有关联,与邓陈两派持续多年的派系之争亦无瓜葛:江既不亲近赵紫阳,也不亲近李鹏;既不属于邓的“改革派”,也不属于陈云、李先念的“保守派”,在中央高层江泽民不仅是个新人,而且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几个月后,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恐怕这才是江泽民侥幸入选中南海的首要原因。
问题是,如果江泽民真如邓小平所期待的那样,不搞小圈子,不参与任何派系,他能够在中共高层站稳脚跟并巩固权力吗?在李鹏、姚依林对江泽民心怀嫉恨,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根本就不把江放在眼里,党内外、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江的前景——都把江泽民视为华国锋那样的过渡性人物——的情况下,不搞帮派、没有足够强劲的派系支持力量,仅靠邓小平戴在他头上的那顶“核心”冠冕,江泽民真的能够坐稳他的头把交椅吗?
八
严格说来,身在中共高层而不搞派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搞派系的领导人,成不了真正的中共领袖,不搞派系政治的中共体制,也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正常运转。须知,派系政治是中共专制政体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中共高层政治的结构性特征之一,中共高层人物建立派系、参与派系并非异常现象或偶然现象,而是正常现象、必然现象。所以,邓小平指望江泽民、李鹏、杨尚昆都不搞派系活动,完全是异想天开。
显然,邓小平严重低估了江泽民拉帮结派的能力。即使是在邓小平仍然健在的时候,江泽民就已经开始利用邓的支持打击敌对派系,培植并经营自己的小圈子。最初,江泽民站错了队,在言论、政策方面倾向于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体现出反改革开放的苗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公开表露出对江泽民的不满,隔空传话“谁不改革谁下台”。杨尚昆追随、陪同邓南巡,杨白冰先于江泽民表态“军队愿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随之“改革派”群起反击,江泽民遇到了他成为“第三代核心”以来最大的政治难关。江泽民立即转向、及时归队,以对邓理论的高调吹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提法重新获得了邓小平的信任。经此惊吓之后,江泽民迅速还击,离间邓杨关系,在邓小平的帮助下赶走了“杨家将”。此举对江泽民稳固权位至关重要(若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杨尚昆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的杨白冰兄弟不在邓死之前下台,江泽民将不仅永远与军权无缘,邓死之后难免还要面临赵紫阳复出的威胁)。1995年,江泽民又在曾庆红的策划下将李鹏亲信陈希同绳之以法。从此杨尚昆的军中派系完全瓦解,李鹏一派也不得不退缩隐忍,而江派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权力斗争中步步为营,逐渐做大做强。随着1992至1998年间李先念、邓颖超、王震、姚依林、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相继过世,此后中共“八老”仅剩对江有恩的薄一波一人在世(邓九二南巡后薄一波则曾助江脱险),江派遂成中共高层最大的派系。事实证明,江泽民不仅是拉帮结派的行家里手(大多数政治观察家将此归为江氏亲信曾庆红的功劳,但江对曾识人善用,笼络得住、驾驭得住曾庆红这样的派系游戏高手,足以说明江的权术段位并不在曾庆红之下),也是中共高层派系政治新形态、新格局、新时代的开创者。
江泽民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江熟悉中共官场运作,但只知做官而不识从政;小聪明很多,但大智慧欠缺;上下级关系维持得非常好,对每位中共元老都毕恭毕敬(江因对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殷勤备至而一直在社会上被谣传为李先念的女婿),但从来没有什么系统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没有任何成熟的政见与主张。江在政治上可左亦可右,在经济政策上可改革亦可保守,其一切行动均以维护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为最高准则,是一个经济上的事务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江泽民身上的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后邓时代中共官场的普遍特色。
从江泽民时代起,中共高层的派系构成与派系之争与毛、邓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派系之间意识形态分歧淡化、政治色彩趋同,而各派系作为特权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则凸显放大。中共高层的派系,从江派开始,几乎就再也没有什么政治路线、经济政策、政见主张方面的对抗性分歧,各派系的形成与壮大也几乎与成员在政治路线上的一致性无关,而完全蜕变为山头老大与众喽啰、政治靠山与其附庸、职位提供者与官场追随者之间的利益结盟关系。简言之,江泽民时代以降的中共派系之争,主要是利益集团之间的权位与利益之争,而非政治上的左与右、经济上的改革与保守之争。江派如此,团派、习家军亦复如此。
当然,在中共高层,总是会有人左一点,有人右一点,有人比较开明,有人比较僵化,有人比较正派,有人比较邪恶,这些区别仍然存在,但是,这些区别并不重要,不是他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基本依据所在。倒是谁提拔了谁,谁是谁的门生故吏,谁和谁有旧交新谊,谁和谁来自于同一个山头,谁和谁有血缘或裙带关系,这些东西,才是九十年代江泽民掌权以来中共高层派系之生成和发展的真正粘结剂。江派、团派、习家军,全都是这种性质的高层派系。至于所谓上海帮、清华帮、“太子党”、石油帮、电力系、秘书帮、西山会、江苏帮、吉林帮、山东帮、之江新军、军工系、陕北系这些附属于江派、团派、习家军的内部支系,也全都是这种性质的党内派系。
谈论这些中共派系,一般谈不上哪派改革、哪派保守,更谈不上哪派进步、哪派落后,因为这些派系的组织机制及其存在价值,无非是为了争夺政治资源、势力范围与经济利益而安插亲信、布置党羽,上下攀援、权位分赃,主公施恩、僚属报恩,抱团取暖、党同伐异,资源共享、利益均沾,投桃报李、结伙贪腐。这种性质的派系,不论它在中共政坛上、官场上的政绩大小、功过多少、是成是败,某种程度上讲,它们都是一丘之貉。
九
江、胡、习时代的中共高层派系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山头主义。如江派以上海帮为基础,曾庆红、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陈至立这些江派骨干力量均为江泽民主政上海时的亲信旧部,上海就是江派的主要山头。有些人曾夸大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政见分歧并因此认为朱镕基不属于江派,但江派本来就不以政见相同而划分,朱升任总理虽由邓小平提拔,亦离不开江的大力推荐,且江朱搭档期间正是上海官员吃香获得广泛重用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团派以团中央为主要山头,习派以“之江新军”(即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省委班子)为主要山头。一般来说,从同一个山头下来的人更容易被原来的山头老大所信任、所提拔,也更容易结起伙来排挤、暗算其他山头的势力。
二是家长制与人身依附关系。中共高级官员加入某个派系,既不用发公文,也不必走程序,而是对号入座、心照不宣,只要在派系内部固有的主从、尊卑关系中承认对方的角色、接受自己的角色,自觉执行各自的角色义务即可。派系的形成并不是完全没有政见、路线方面的共同立场,但最重要的则是以人事关系为基础,是派系领袖与派系成员之间恩惠与忠诚、利益与感情关系的存在,是派系成员对派系领袖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一朝天子一朝臣”,“树倒猢狲散”,派系头领是否具有提供职位、庇护臣僚的能力,是利益交换关系、派系凝聚力、派系存续的关键所在。
三是派外有派、派里有系,每当旧派衰落,必有新派崛起。江派、团派、习家军是以三任总书记为“核心”的主流大派,每派里均有若干支系——比如新近成型的习家军里有之江新军、闽系、沪系、陕系等支系。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治局常委或中央要员都有聚焦在自己名下的比主流大派较小的派系,比如江派曾庆红麾下有“太子党”、周永康旗下有石油帮、政法帮,团派李源潮麾下有江苏帮、令计划旗下有山西帮。习近平厌恶派系政治——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强人”全都厌恶派系政治——希望消灭一切“团团伙伙”,只留下习家军一派掌权,这样做当然不可能成功。最后的结果将是:当众派凋零、一派独大之时,即是其内部分化、自我裂解之际。昔日毛派独步一时、随即分崩离析,便是历史例证。
四是权力互保、利益交换。后邓时代的高层派系几乎不再有“凡是派”与“实践派”那样的思想理论或路线政策基础,而主要是恩惠—忠诚、庇护—报效的利益结盟关系定义了江派、团派、习派这些派系的使命。而若严格按照党纪国法,派系内部的恩惠—忠诚、庇护—报效关系均不具有正当性,一旦遭到敌对派系清算,任何派系活动,不论其是否被包装为符合组织程序和官方话语体系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具有拉帮结派、团团伙伙性质的活动,都将成为敌对派系指控其腐败的证据。习近平、王岐山通过反腐败而清洗异己派系,正是抓住了派系活动的腐败特征。
十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承认中共是一个政党——虽然它从未依法登记,但它有章程,有政纲,有组织纪律,有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有讨论、表决、执行、监督的组织程序。按理说,有了这些东西,就没有必要再有派系——毕竟,派系或多或少是一种前现代的、黑帮化的产物。凡是派系所能做到的政治行为,政党都能以更公开、更透明、更组织化、更程序化的方式做出。为什么中共这样的专制政党的高层权力精英总是热衷于派系政治,而且使得派系结构超越正式组织结构成为高层政治的基本形态呢?
其实,无论是宪政民主政体之下的普通执政党,还是专制政体之下的永久“执政党”,政党领袖大批量地任用自己的政治亲信出任重要官职,而这些官职者通过正式组织程序之外的某种形式组织起来,以维护他们的共同主张或共同利益,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川普,江泽民还是习近平,用自己人组阁,与政治亲信分享政权,这是他们都会做出的同样选择。但是,川普任命自己熟悉的、信任的、亲近的人士出任近五千个联邦高级职位,并没有人指责川普组建“川军”,更没有人担心美国高层政治陷入派系之争的泥沼,何以习近平任用数十个亲信故旧出任疆臣枢吏并试图在十九大上垄断高层重要职位,却被人们普遍指责为大搞习家军?
原因就在于,川普对于联邦政府高级职务的人事任免权来源于宪法,植根于美国政党政治的传统,是循章依制、公开透明的政治行动,当然不会造成美国政府或美国共和党内部不正当的私人朋党性质的派系政治。但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其一,中共的统治地位没有经过民选程序的确认,习近平本人的权力来源尚且名不正言不顺,若再任用私党、培植亲信,就更加没有合法性了;其二,中共的人事任命传统,无论是“五湖四海”的明规则,还是“七上八下”的潜规则,都不认可党的领袖拥有任用亲信、排斥异己的法定权力,中共的组织纪律、“政治规矩”也一向以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为禁忌,不曾赋予任何党内派别以政治上的合法性,这种事情只可做而不可说、只可悄悄做而不可公开做。在这种极其扭曲的政治氛围中,应该说,高层政治的派系化正是专制政党的宿命。
2017/1/7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5/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