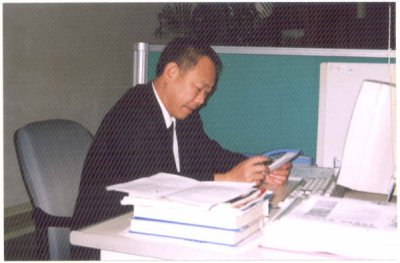网络能使人读到精彩的禁书。《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是秦耕先生对一段坐牢生活的回忆,乍一开卷,便令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废寝忘食,一气读完。读罢仍觉余香满口、余音绕梁——此番溢美是否言过其实,诸位可先行阅读,再作评判。
当然,监狱总不是什么好去处:狭小、阴暗、潮湿,囚禁秦耕先生的监狱,也大致如此。因为少了开阔、明净和干爽,自古人起,一旦与监狱扯上关系,便会有“牢狱之灾”的说法。这不是什么错误,对一个守法公民来说,身陷牢狱,自是莫大的灾难,但在秦耕的回忆中,却无灾难面前的恐慌、沮丧和焦虑,相反,正如该书书名所言,秦耕的监狱生活是“快乐”的。
尽管阴暗潮湿的环境使秦耕的腿部湿疹发炎、流血流脓、浮肿到无法行走,而食物缺乏更导致长期饥饿,以至于“我还记得在那次与父亲难得的会见中,我告诉他,希望以后不要给我送吃的东西,理由是:肚子每天都饿,你送来的东西只能管几个小时,管不了每天;吃完之后几个小时又饿了,而且饿得更强烈、更难受,如果因为吃了腥荤消化不良造成拉肚子,还得不偿失。”可在秦耕笔下,这些不够快乐的监狱生活构成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他不仅笑着入狱,笑着出狱,而且做到了将监禁生活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这种快乐的“感受”,即使对有过坐牢经历的人可能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秦耕先生的文笔美而精练,史料之外,兼具文学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我一度怀疑他的所谓“快乐”,只是一种“零度写作”的技巧。然而,作为纪实,所写又是亲身经历,作为具有痛感的人,饥饿和病痛面前,如何能够“零度”得起来?清代方苞的《狱中杂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该文展示的狱政弊端,至秦耕时代尚未结束,但作为文人书生,方苞身处监狱时的震惊感,在秦耕这里确确实实已不存在。1989年,秦耕先生的牢狱之灾是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经历,但秦耕先生在入狱前已有充分思想准备,所以,《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中的秦耕先生虽然面对的是无法预知刑期的“中国第一罪”,却无慌张,也无焦虑,仿佛他不是被囚禁在陕西的监狱,而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度假。
那么,秦耕先生的从容快乐是否是一种矫情?
从文中透露的秦耕先生的经历看,他曾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机关工作人员,但当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东风吹落他的头上,他拒绝了被提拔为局长的机会,局长属于官员序列中的低层级别,但在一个县城里,那可就属于中层干部、是手握实权的人物了,而且,当时的秦耕先生年仅23岁,前途不可限量。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思潮”影响下,秦耕想都不想便拒绝了做官的机会,此后,秦耕走的实际是一条民间学者的道路。拒绝体制的招纳、并且绝不以此作为博取“名士”声誉的策略,或许只在秦耕成长的时代才成为具有文化支撑的人生模式,此一模式的放大,便是民间社会自觉意识的生成。由于这样的人生选择,秦耕主动远离权力、贴近民间,这就使他与方苞的士大夫心态迥然不同,对他来说,入狱不过是从民间的一个角落走入另一个角落。
正是这种主动自觉的民间身份定位和追求,使秦耕先生既不以官为荣,也不以囚为耻。相反,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飞黄腾达,正是一个人的耻辱。在六四这样一个善恶分明的历史时刻,秦耕先生“甚至固执的认为,在中国,作为一个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抓进监狱就是必然的命运,否则就一定是在罪恶面前有意沉默、有意回避和暗中屈服;监狱,也只有监狱才能洗刷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面前表现出的懦弱、恐惧、麻木、选择性沉默或精明算计而蒙受的层层羞耻,才能与专制罪恶保持起码的距离。”
有了这样的意识,入狱便是心灵的自我救赎。当高墙挡住了外视的目光,人就很自然地转朝向内的自视,在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内视正是难得的契机,也就是说,监狱囚禁了人的身体,却未使之丧失心灵的自由,乃至于我们可以说,监禁成就了秦耕先生的自由。
当然,《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并非秦耕先生的心灵独白,也不是卢梭式的漫步遐思,佛家有云: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对乐观、积极地热爱生活的秦耕先生来说,监狱还是他接触特殊人群的独特视角。草根的秦耕与儒雅的杨建利不同,同是坐监的政治犯,杨建利先生从不打探身边囚犯的案情,只以人与人的平等姿态与之相处,由此赢得了囚犯的尊重与敬佩,秦耕的做法却是与囚犯“打成一片”,短暂的戒备之后,秦耕便与同室囚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了”,他不仅详细了解并记录同室囚犯的案情,还兴致盎然地参与各种囚室内游戏,直至恶作剧般地捉弄看守警察。《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普通刑事犯罪者的故事:飞檐走壁的关双喜、行窃乡里的张新良、“撮”瘾甚大的少年赵红兵••••••这不是法制类报纸居高临下的报道,也不是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而是对身边人的真实记录,为研究当代中国底层生活提供了真实的范本,这些故事自然穿插于书中,连同秦耕对监狱管理者的观察与记录一起,使《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成为一本可读性极强的社会记录。司法制度掌控者大概无法想象,将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混同关押的做法,一方面增加了政治犯对社会底层生活的了解,一方面也让政治犯的思想影响波及最底层的社会人群。
实际上,秦耕的快乐生活在我看来并不快乐,当同室囚犯为能拣到一个看守丢弃的烟屁而制定复杂周密的“香烟行动”时,我们能够想象监狱生活的单调、困乏和无助,但无论会见亲属时提出的“三不主义”,还是戏弄女警官卢某时的“不怀好意、不露声色”,都显示出秦耕先生“蛮不在乎”的性情,而这些都发生在六四刚过、第一罪的刑期长短尚在未定之天的时候。如果说解除收容审查时秦耕的“表演”比较容易理解(“我想了想,觉得也表演得差不多了,就说:‘把笔拿来!’于是我在解除收容审查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从抓捕到审讯以至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他却总能以这种幽默、快乐的心情坦然面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人”了。
“奇人”非指具有特意功能、而是那些行为处事超出一般想象的人。面对秦耕的如下文字,谁能不为之称奇称怪:“我在监狱反复争取、申诉、抗议,要求得到的选举权,其实就是准备再投一次庄严的弃权票。后来监狱正式投票时,有人鼓动大家抵制,郭铁汉表扬说秦耕还不错,还主动要求参与选举,我说:不,我是为了投弃权票才争取投票权的。”其实,类似的怪人并不少见,如果由一个人所处的交际圈子而判定其是否奇人,那是一种愚蠢到家的做法,可是,十多年间,在政治异议这个圈子里,着实可以见到许多既奇而怪的人士,由于这个缘故,初识任何一个形容衣着寒怆的前政治犯,我都不敢怀有轻慢之心,在他们的背后,往往有着曲折离奇的故事,有着一份干云之豪情,即使多年的底层生活已经打磨掉他们脸上的棱角••••••
由于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由于对良知与正义的自信,监狱的墙壁对秦耕这样的政治犯来说,实在是不够坚硬的,如果一个人铁了心要趟一趟监狱的“混水”,那么,空洞的四面墙又算什么?“我要认认真真、一本正经、心安理得的度过我的监狱时光,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作为这个监狱后来的囚犯之一,我在监狱期间,脑海中从未闪过越狱的念头,甚至我希望自己被关押得更长久一些,因为我坚信坐牢与中国人的自由直接相关,坐牢的人越多,中国人离自由的距离就越近;不再惧怕监狱的人越多,中国人得到自由的机会就越大;只有在监狱再也无法使人们感到恐惧、再也无法使人们屈服时,只有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慷慨赴狱,把监狱变为不是惩罚罪恶的场所而是反抗罪恶的场所时,只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确信中,把坐牢当作最高奖赏、最高享受和最高荣誉而不是一种拙劣的惩罚时,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光荣入狱、更多的清醒者就迫切等待自己也光荣入狱的时刻来临而不是莫名恐惧、竟相逃避甚至互相推委时,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希望!”
一个“认认真真、一本正经”选择监狱生活的人必是一个傻子,但秦耕这个清醒、自信而又快乐进出监狱的傻子,却会让很多聪明人怀疑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信念:监狱是否是世间最不可承受的痛苦?如果入狱是一种莫大的荣光,知识分子的莫名恐惧和竟相逃避是否不过是一种胆怯和无力把握生活的表现?也许,种种现实因素使我们无法象秦耕这样坦荡、快乐地走进监狱,但由于秦耕先生的快乐的监狱生活,“我们要战胜内心的恐惧”、“勇敢说”不就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境界和修为吗?人们未必敢于追随勇士所为,但当勇士将勇敢者的游戏玩到如此精彩,使人读来欲哭欲笑,苦笑不得后不由击节赞叹,人们难道不会萌生出寻求快乐与精彩的冲动?生活未必需要悲壮,毕竟却总不能少了快乐。
内心世界充盈的秦耕让我们明白了快乐的源泉在哪里,这与一个人身处的环境无关:监狱中同样会有快乐,脑满肠肥的优游同样可以使人失去生活的兴致。当然,舍身入狱未必关乎政治追求,我们知道秦耕是不喜做官的人,大到局长、小到牢头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知识分子,仅仅为了“不肯继续以猪狗的方式接受奴役”而借监狱洗除耻辱而已。这甚至算不上富有策略的政治抗争,在“自由本身就是罪恶”的地方,他的入狱仅仅是为真正做一个人。
入狱并非实现做人愿望的唯一方式,但对1989年的秦耕来说,他无悔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一般来说,异议者的第一次入狱多不能令自己满意,秦耕却能在离开监狱之际“看着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大声说:‘其实我最后想告诉你们的是,监狱对我没有任何改变!我进去时满面笑容,今天我依然笑着走出来。’”这是足可让他可以骄傲一生的经历。自由民主必胜的未来预期之下,无须以短暂的成败来论英雄,对秦耕来说,在1990年他就已经取得胜利,他战胜了监狱,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己,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战胜了卑琐和恐惧,同样重要的是,他还以一本书战胜了一个读者的懦弱:种种现实牵绊之下,我不敢说自己能够达到秦耕先生的人生境界,但是,如果有一天被迫再次面对高墙,我希望能象他那样活得平静一些,快乐一些。
谢谢秦耕先生和他的作品。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