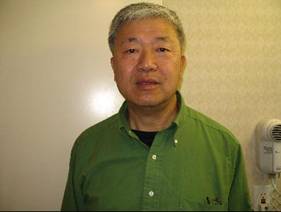我爱读同时代人的自传,如果作者是熟人,是朋友,那就更好。作为那个恐怖时代的过来人,我和章诒和一样,很想知道别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比较类似的人——到底“是怎样熬过来的”。不少朋友知道我有此癖好,所以老康这本自传一出,就有朋友向他建议:让胡平看看这本书,他一定有兴趣。
一
自传是个人的历史。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是一个大写的词,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是不能算做历史的。然而正如波普(Karl Popper)所言:如果有一部人类的具体历史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只是这种具体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的。我们必须有所省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写艺术史,或语言史,或饮食习惯史或伤寒病史,如此等等。一般人所说的历史,无非是政治权力史,即罪恶与谋杀史(其中也包括制止这类行为的某些企图)。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政治权力史呢?因为权力影响大,权力影响到每一个人;其次,人们易于崇拜权力;再者,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够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很多历史家就是在掌权者的监视下进行写作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个国家越是自由越是民主,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五光十色,越是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例如美国,政治权力一直受到约束,因此一部美国史便丰富多彩,其中,权力史或掌权者的故事只占很有限的部分,其他各种类型的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在当代美国,比尔。盖茨的历史地位就远远超过总统们和将军们。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是独立地发挥其伟大作用的,他不需要沾权力的光,他的成功不是某一掌权者英明政策的产物,端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反过来,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极权,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梁启超说: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族史耳(司马迁的《史记》要好一些吧)。“新中国”,尤其是毛时代的“新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一切,毛时代的中国史,如果你要按照老式的方法书写的话,那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要跟我说毛泽东有什么功劳贡献,单单是他把中国变成他一个人独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几亿人无从独立发展自我实现枉生一世白活一场,就罪无可赦罪该万死。
毛时代的中国没有思想史,那当然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人没有思想,那是因为在毛时代,一切不同于毛思想的思想都没有登台亮相的机会。就连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也都还是藉着毛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才得以出笼的。无怪乎章伯钧、罗隆基在被毛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而打成右派后反倒感谢毛,因为要不是毛搞这场阴谋或阳谋,他们便无从向公众公开表达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也无从以头号二号右派的身份“被历史记上一笔”。
按照老式的历史观,毛时代的中国史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标准,否定官方对毛的历史评价,但仅仅这样做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不管对毛是褒是贬,那总还是围绕着毛一个人打转。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独裁者一个人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毛核心或邓核心或江核心或胡核心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我们必须要有另外的历史。谢天谢地,尽管中国的所谓正史常常是政治权力史,但一般人并不是只从正史中瞭解历史,我们还通过各种野史,通过文学,甚至通过民间传说去瞭解历史(譬如通过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传说去瞭解秦始皇的暴政)。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重视当代中国人的自传的原因。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没做出过任何足以进入历史的事情,你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一部个人的历史。在这里,个人历史的写作是对否定个人独立价值的极权政治的反抗。写作是对人生的补偿,对命运的反抗。极权政治糟蹋了我们的人生,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写作来做一种纠正一种反抗。我们需要大量优秀的个人历史流传后世,非如此不足以与那个黑洞式的政治权力史即独裁者的个人历史相抗衡。所以有时我要想,也许,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就是自传了。
二
普希金说:“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生在俄罗斯是多么可怕呀!”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哪里比得上共产时代的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难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对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大饥荒夺取了四千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难道不是平平庸庸?不过,极权统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压抑个性摧残精神,因此,那些有着比较突出个性与才能的人便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在毛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有几个没挨过批挨过整?有报道说,文革后清理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当然“知识分子”和“有才能的人”并不全等),竟多达860 万件。注意:这还只是毛时代的数字,还只是官方后来承认的数字,还只是官方承认的冤假错案。两千万地主富农(他们中间该有多少有才能的人!)不在其内,章伯钧、罗隆基也不在其内,因为当局始终不承认那些是冤假错案。应该说,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要算是很“幸运”的了。至少,他们的个性与思想早已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下发展成熟,他们毕竟在人生舞台上有过正式的演出。当章伯钧得知1957 年反右运动被写进大英百科全书,他们的言论被评价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相比之下,像康正果这样的人就更不幸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们象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就遭到冰霜的摧毁。他们还没来得及使自己成熟,使自己发展,还不曾向社会发言,更谈不上影响社会,影响历史,就被卷进极权暴政的绞肉机。你因思想言论而受难,但社会并不知道你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再说了,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年龄上,你又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你的思想和言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而你的受难也就不可能具有多少历史的意义。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的前途都被糟蹋了,白白地糟蹋了。你的全部苦难顶多是在庞大的受难者数目中充当一个无名的零头,而且还是常常被忽略不计的零头。这该是多么可怕啊。这种可怕的程度,岂是普希金想像得到?
老康受迫害的故事很荒诞,但是在那个时代也很寻常。
从少年时代起,老康就热衷于读书与写作。1964 年,老康在陕西师大中文系念书,校领导号召同学“向党交心”,老康因为一向表现“落后”,再加上出身不好,成为重点教育对象,被逼着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还过不了关,系上又进一步要求老康交出他的日记以及和朋友的来往信件,老康拒绝交出,因为他知道那等于自投罗网,结果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不得不进入一个公安局办的建筑材料厂当了就业工人。文革中的1967 年,老康从报上读到苏联批判“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一时心血来潮,用俄文写了封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自己翻译,此信不消说被政府截获,据此给老康定下“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满后,城里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去西安郊区农村落户,认一个老贫农为养父,改名李春来,当了农民。
在老康的苦难经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被孤立、被监视、挨批判和写检讨,最可怕的是长期的繁重的强迫劳动和卑微忙碌的日常生活,其力量足以彻底摧毁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老康在建材厂当就业工人时就非常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127 页)然而坚毅如老康者,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腐蚀,后来他成了农民,成了个很蹩脚的农民,三十出头了,才娶了个山沟里的老婆,“从此淹没在劳碌的农家生活中”。“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娃,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我惊奇地发现,父母的制止,劳改队的改造,一切强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积习,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妇生活中日渐磨损,消蚀殆尽。真是岁月不饶人,激情易衰老呵!”(插一句,我觉得老康这段描述不够准确,“平庸的夫妇生活”只不过是压垮老康文学梦的最后一根草)老康担心,“再这样荒废下去,真有那么一天,学校要找我回去上学,我也许早已丧失学习的兴趣和能力。”(356-357 页)这种麻木和担心还是发生在毛死后,中国出现转机之时,倘若毛泽东象邓小平一样活到九十几岁,老康恐怕就给废掉了,“新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才俊之士,恐怕都给废掉了。
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文学热潮。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把多少人逼成了作家,举国上下都为文学而如癡如醉。自学成才的报告文学,反极左路线的先知先觉的报告文学,伤痕文学,劳改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还有种种爱情与婚姻的悲剧故事,以及被压抑的性苦闷性飢渴的文学描写,凡此种种,都盛极一时。不难看出,上述几种文学,几乎都具有我在前面说到的个人历史的性质。老康既有出色的文学才能,又有沉重的苦难经历,当然也少不了这样的写作冲动。现在一般人只知道老康是个学者,写过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其实老康原来一直最想写的是小说,是以自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
老康产生这个念头已经有二十几年了。1979 年是老康的春天,多年的“反动”罪名一风吹,一考两考,从农民一跃而成为研究生。那时候报刊上正流行报告文学,报道了不少平反后得到新生的人物,有朋友带记者找老康采访,打算把他写成一个受尽打击而自学成才的典型。老康一想起自己多年的学业荒废就是气,怎肯把自己还塞进那个“自学成才”的俗套里。老康说:“你们真想写,还是听我讲我被打成反动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写我到底怎么反动起来,后来又怎么不反动了。”双方话不投机,采访一事遂作罢。不过这倒激发起老康要写自传的念头。但是老康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觉得,“我要写的与那些报告文学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应该说,遭遇的事件都有类似之处,但他们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却让我觉得不太对头。”(2 页)
这就是老康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我最欣赏老康的地方。众所周知,当年那些报告文学和小说大多有一套流行的模式,譬如写到受迫害,那就一定要写主人公如何对党坚信不疑,越受迫害越是忠诚;譬如写到下放劳改,那就一定要写到劳动人民具有如何的优秀品质,如何保护了帮助了落难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局照例是一片光明,受迫害者照例对党的“拨乱反正”感恩戴德,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类作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最容易误导读者。老康终于没有加入“新时期”文学大合唱。直到今天,他才拿出这本打了二十几年腹稿的自传。时过境迁,老康这本书自然不可能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不过我敢说,老康这本书要比绝大部分当年轰动一时的同类作品更真实,更有价值。
老康虽然不是“生在新社会”,但却也是“长在红旗下”。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老康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新社会”的游离分子,他几乎从不曾进入官方的话语系统,他只希望能摆脱红色政治的干扰,并不指望得到官方的承认。这多半要归因于老康在十几岁的时候从祖父的书房里阅读到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著作。如余英时教授指出的那样,古典文化为少年的康正果“建构了一个强固的精神堡垒,因而决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IV页)
老康写到周围的许多人物,着墨不多,但依据我的经验判断是真实可信的。例如他那位养父、贫协组长李宝玉,要是落在张贤亮一类作家手中,那还不写成恩深义重的再生父母?处处闪耀着劳动人民的纯洁光辉。还有那些“社会渣滓”,如小偷、流氓,老康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因为他并不想印证什么概念或理论,既不想媚上也不想媚俗。他只是写下他的经历和感觉。
很多遭受迫害的人,在平反后对共产党,尤其是对邓小平感激涕零。老康则不然。当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向他灌输对共产党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时,老康不肯附和,“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要不是他们给我制造了‘反动’的罪名,我在大学都教了好多年的书了,哪会落户到农村?捆了人家多年才给松绑,又有何感谢可言!”(370 页)老康这段话讲得实实在在,然而在那时竟没有多少人讲得出来。一般人只知道嘲笑阿Q,挨了别人的打不敢还手,只好转过脸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可是,这比起我们那么多右派,挨了共产党的整,事后还要说是“母亲打儿子”,不是有骨气多了吗?
鲁迅尖刻有余,深刻不足,他想像不到有些受迫害者事后竟然还要向迫害者认同。老康的几个有类似遭遇的熟人,平反后都迫不及待地站在了党的一边,有的原来不是党员的还积极争取入了党。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一个人受到共产党那么残酷的迫害,到头来还要宣誓对它效忠,这不是十足道地的受虐狂么?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当一个人遭受党的残酷迫害时,他很容易产生两种感受,一是怨恨党的残酷,一是深感党的强大。前者驱使你反抗,后者驱使你依从。假如你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或没有力量反抗迫害者,那么你就会觉得,免除迫害的最稳妥办法就是赢得迫害者的接纳,使自己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所谓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那倒不一定意味着你自己也非要参与对其他人的迫害不可——很多原先的受害者在重新被党接纳后都拒绝或避免参与对他人的迫害,他们只是希望不再被党视为异己,只是希望被党视为“自己人”而已。
四
老康不肯像别人那样,“在平反后老实当我的教授,厚着挨过耳光的脸,喜孜孜接受党恩浩荡的抚摸,努力在纯学术上做出应有的贡献”。(370 页)所以他的故事就没有随着重归学院而以喜剧收场。此后老康的生活依然麻烦不断,先是在硕士学位论文中评析“艳情诗”触犯清规,差点毕不了业,继而又在八九期间参加游行而受到审查;最后,在老康已移居美国,执教耶鲁的2000 年,老康回国开会探亲,被安全部非法扣押,其罪名是向国内邮寄和携带《北京之春》等“反动刊物”。老康的这些遭遇固然证明了他秉性难移,但更加证明了的是江山未改。等平安回美后,老康赶快入了美国籍,从此安下心来定居在这片自由的土地。
就这样,老康的自传以一种既非悲剧也非喜剧的方式结了尾。它不能不令读者深思:究竟要到哪一天,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老康还是乐观的。他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462 页)。◆
2004年12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五辑 开卷有益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