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所说的虚无,主要是指文学精神世界里的虚无。最近看到些批评中国文学虚无观滥觞的文章,也常看到有人指斥鲁迅虚无,王小波虚无等等。在汉语里,“虚无”是个贬义词。虽然当今中国人普遍的虚无,但人们潜意识里都觉得“虚无”不是个好东西,于是一见批评“虚无”的论调,大家就都一窝蜂地上前喝彩。对此我实在无法苟同,文学精神世界里的虚无观并非都是毒瘤,有些文学作品所展现的虚无与荒谬恰恰能警醒世人于迷醉中。关键是看创作者对虚无的态度如何:是得过且过,认为这就是人世之常态,把人的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还是自始至终对虚无持坚决的否定态度,揭穿谎言制造者的丑恶嘴脸,揭下世人自欺欺人的虚假面具。
有人大言不惭地认为,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是最虚无的年代,鲁迅则是那个年代的“虚无党首”。论据还是老一套,鲁迅的心理与文章都太过阴暗、残酷,读来让人看不到希望云云。此种论调,鲁迅的一篇小文《希望》里所引述的一句话就足以驳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在这篇作于1925的小文里,已“大概老了”的鲁迅,“心分外的寂寞”。毫无疑问,此时的鲁迅,已毫无掩饰地表现出对冰冷世界的绝望之情。但是,“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绝望却也决绝,只能化作虚妄——虚妄之“妄”,正是融一丝希望在其中!由此我将文学精神世界里的虚无观分为“虚妄”与“虚幻”这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前者正是鲁迅所言的“绝望之为虚妄”,而后者则是实实在在的虚无与麻木,是真正要批判与摒弃的。
徐友渔为《哈维尔文集》所作的序言《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里,有一节论及作为荒诞派戏剧家的哈维尔对“荒谬感”的理解,读来让我颇为认同,忍不住搬来深入佐证一下:“哈维尔被人们认为是荒诞派戏剧家,当有人问到他的荒谬感和戏剧创作的关系时,他回答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意义与荒谬的互补性:荒谬即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的追求就会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所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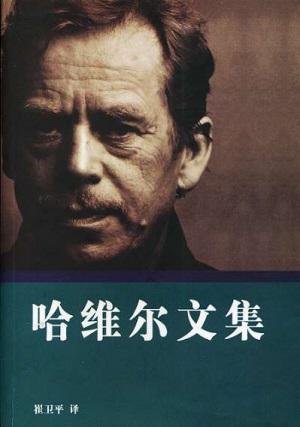 文章引用了哈维尔的原话:“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文章引用了哈维尔的原话:“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哈维尔这段话划分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虚无观:无意义的虚无与无信念的虚无。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对前者而言,这里的“无意义”并非指虚无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指我们的生存状态的畸形与变态——而绝非常态。体验无意义,正是因为对它的另一极“意义”的渴求。认清了世界的无意义,也就认知了意义的所在。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学,“无信念的虚无”已泛滥成灾,而且被众多人标榜与膜拜。举例言之,我们有余秋雨的所谓历史文化散文,二月河的帝王将相小说,琼瑶、汪国真的手纸文学,小资作家们笔下的堕落青春等等。放弃深层的精神价值,放弃批判与反思,放弃探寻与求索,以肤浅庸俗的“口红”和“麻药”(朱大可语词)的形态,向自甘庸碌的人们烘托出一片虚假繁荣的幻象——他们才是彻头彻尾的“虚无党”。这些在文学史上注定要丢进垃圾堆的作品也都是“应运而生”的,只能怪中国人越来越自甘虚无的麻痹精神状态。
接下来我要谈论一下王小波的虚无观。王小波在世时,也就是还默默无闻时,就已经有人批评他的小说太过虚无了。我记得王小波还写过一篇杂文驳斥此论调,但并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自己应该属于“无意义的虚无”一类。
我已经说过,王小波和他笔下的人物,由于所处的特殊时代,他们自身都有着无法摆脱政治束缚的宿命,内心却又崇尚自由,漠视体制,摆出一种活在别处、消极对抗的姿态。但由于叛逆者本身的弱小,这种故意摆出的流氓姿态的背后又饱含着一种悲天的英雄主义情结。正如哈维尔所言,“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王小波笔下的这种英雄主义情结,正是绝望之为虚妄,正是无意义的虚无。这一点,在王小波后期的一部中篇小说《2010》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已写过一篇分析《2010》的文章:《2010年的中国——解读王小波〈2010〉》。记得有一“王小波门下狗”评论说,王小波的作品也需要分析与解读吗?这种论调倒也与那一波波的“门下狗”们一脉相承,他们学会的只是王小波小说里的文字游戏,肆无忌惮的情爱描写、插科打诨,和小说人物表面上的顽劣与轻浮——这也是毫无信念的虚无。我之所以要“解读”王小波这篇尚未来得及定稿的小说,主要因为它明显表现出王小波开始尝试突破以往,小说的叙述开始抛下暧昧不清的态度,人物到最后公开明确地醒悟、反抗、表达真爱。
2010年的中国是个相对主义的暧昧国度。起初主人公王二同许多人一样忍受压迫,或者说习惯于被压迫,麻木不仁,得过且过,用存在即合理来解释现实的一切不合理。王二的妻子不得不与王二离婚,去做压迫者的“傍肩”。王二与前妻藕断丝连,但他们却无法或者说不敢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真情实感。后来被压迫者们聚到一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狂欢,以宣泄内心的压抑。事后作为发起人的王二被施以鞭刑,在行刑的过程中,王二终于幡然醒悟:
“后来人家用皮绳捆着我的手腕往架子上吊……此时在我视野里,只有一个血迹斑斑的X形架的上半部,还有楔形黄色的天空,万籁无声,还有背上冷嗖嗖的,时间停住了。你说这是在干嘛?我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此生体验到的一切荒诞,在此时达到了顶峰”。“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不是一般的不对头,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对头”。“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一点地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一个乌托邦”。“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以发人深省……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
幡然醒悟后的王二,在目睹自己的前妻正也正被施以鞭刑时,心脏病发作而死。接下来小说明确肯定了王二与前妻之间的这份真爱的价值:
小说最后一部分只有一段话,通过王二的前妻交待了王二死后的事情。这是一段让我感到意外的话,熟悉王小波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小说,故事人物最终都难免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虚无当中,一切都是虚假的,看不到任何希望。但仔细阅读《2010》的最后一段,会发现王小波分明是肯定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爱——它也是2010年的中国仅存的一丝希望。
王小波笔下似乎从未有过真实的东西,一切都罩着一层虚伪的面纱。他所描述的爱情,通常会被各种利害关系和大肆渲染的情爱描写所淡化,让你说不清这到底是不是真爱,《2010》也基本如此。在牵动各方利害的暧昧关系下,在身不由己的2010国度里,他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王二最终将自己对前妻的真爱记在了日记里,而王小波这次也终于在结尾借用看到日记的王二前妻之口,明确肯定了这份真爱的价值。
“对于爱上他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今后也不会爱上别的人了。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时,后者受鞭刑,鞭子就会打到前者心上。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唯一的区别是,我的心脏比他的好。现在我人活着,心已死。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平静地干我该干的事了”——这份爱已不仅仅是爱情,不仅仅局限于爱情。
——《2010年的中国——解读王小波〈2010〉》
今天,我们不应去苛求当年的鲁迅与王小波,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让麻木不仁的世人意识到这世界的荒诞与无意义,让人们明白世界本不应如此,我们应去找寻人生的真意所在。正所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当然,这只是启蒙与希望之门的微微开启。前人拓路来者承继,希望之途任重道远,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2007年7月14日
《吾诗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