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网按:徐泽荣博士是深具中西文化素养的社会学者。2000年入冤狱11年,狱中笔耕不缀,苦研马学,心得盈筪.自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州监狱遭遇了滑铁卢!”作者改称马克思主义为马学,而马学之核心乃是劳动价值学说,本书即力证其说之非。以此见证马学入中100年。系列共20章,本刊将予连载。】
早年照片.jpg)
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左二)早年照片。人称誉其“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他对之曰“执教着文中有我,吃饭穿衣外无他”。
世事难料,所启后人竟然有后于狱中将马学劳动价值学说证非的我。
【马学劳动价值学说逻辑证非系列之一:索品】
人类诞生之后通过劳动追求和通过市场交换的,并不只是产品,即人造效用,而且还有“索品”,即天设效用。产品源自生产劳动(Producing labour),索品出于“索要劳动”(Possessing abour)。人造效用无非是经过人力作用的天设效用的分解与合成,缩小与扩大、移动与固定、拆开与整装、曝露与隐藏等等。陆水空天,树草土石,禽兽鱼贝,以及社会关系、生物关系、天–人关系、事–物关系等等,一经对其有所需求的人类的占有,便可称作天设效用,或者称索要劳动的成果“索品”。一边被提供一边被消费的生产劳务和索要劳务,无法像产品、索品那样收凝劳动时数——于此场合,劳动时数不被收凝,只被流淌,而以劳动时数为效用序数计算单位。产品、索品、生产劳务、索要劳务四者之间的交换形式,乃有以下十种:
01. 生产劳务与生产劳务之间的交换;
02. 索要劳务与索要劳务之间的交换;
03. 生产劳务与索要劳务之间的交换;
04. 产品与产品之间的交换;
05. 产品与索品之间的交换;
06. 产品与生产劳务之间的交换;
07. 产品与索要劳务之间的交换;
08. 索品与索品之间的交换;
09. 索品与生产劳务之间的交换;
10. 索品与索要劳务之间的交换。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定义广义经济学为“关于各种不同制度形式下的所有交换活动的一门科学”;并称“交换给交换双方带来好处的根源”为何,乃是经济科学的核心问题。作者认为上述十点业已穷尽了“所有交换活动”的形式,尽管布氏如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并没谈到索品及索要劳务。有些索要劳动本身,如抢劫、战争等并不必然带给双方好处,但是,索品、索要劳务的交易——例如劫赃与虏获的交易,却像产品、生产劳务的交易一样,会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至于好处是否长久、对等,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由于许多对于索品和索要劳动的获取,牵涉到威权,牵涉到暴力,所以它们亦属政治科学的研究物件,或属“政治经济耦合科学”的研究物件。
就像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曾具振聋发聩作用一样,本书将具体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索要劳动,更具振聋发聩作用。对于马教教徒而言,后种分法还有可能使得他们闻后即现瞠目结舌,如果不是即感五雷轰顶的话。
“劳动”的经典定义,乃为“人类使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使之合适自己需要的有目的活动”。索要劳动的外延无疑符合这一内涵。宫殿、仪仗、锣鼓、饰物、标语、武器、工事、界碑、禁栅、城墙、文字、书刊、仪器、电脑等等,都是索要劳动使用的工具。你不能说它们不是工具而是别的什么器具——吴王宫女误将武器当作玩具,便被得到吴王允许训练她们的孙滨下令斩首。天设效用的“改变”可以包括:“生命的传续”、“财宝的易主”、“技能的提升”、“西学的东渐”、“权力的旁落”、“爵位的剥夺”、“道德的沦丧”、“感情的转移”等等。求知索解活动的鹄的乃是一种天设效用,即客观规律的形而上式道化肉身——“知识”。客观规律不能被人制造出来,所以不能将求知索解活动归入生产劳动;夺取政权活动的鹄的亦是天设效用,人类具有“施治–受治”基因,蚯蚓、蝤蛴、蝴蝶、瓢虫之类却没有,你亦不能将夺取政权活动归入生产劳动;体育竞赛的鹄的既有人造效用,如货币,亦有天设效用,如健康,不过体育训练和运动竞赛乃与生产劳动无涉。
索要劳动也像生产劳动一样,分为作业劳动和经营劳动,太平军的枞阳会议、共产党的庐山会议体现的就是索要经营劳动。亚当·斯密将生产经营劳动的提供者即司商家,视为“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时数“不能保藏起来,备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作者认为:其一,斯氏将生产经营劳动视为非属生产劳动乃属错误。今天看来,斯氏所说“非生产劳动者”应为“非生产作业劳动者”之误。其二,斯氏认为所有司商家无一例外地是“非劳动者”,因此如下公式“不劳动者不得食≠资本家是吸血鬼”,应是斯氏心中公理样式看法。作者马上就会谈到生产作业劳动和生产经营劳动的分别,以及两者与交换价值的关系。
马氏曾经说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类物种的自我生产、社会关系的“重新生产”(亦可称为“复制”——作者注)这四种生产形式,始终存在于历史之中,因而是人类生产的普遍形式。在此,马氏混淆了生产劳动和索要劳动:部分“精神生产劳动”应属精神索要劳动:“人类物种的自我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生产”,应属人类物种的自我索要和社会关系的重新索要:“物质生产”则应祛除“物质占有”。
显然,追求生存、安全、顺悦属于人类物种的自我索要;追求权力、地位、名望属于社会关系的重新索要;追求知识则既属于对于天–人关系之中客观规律的索要(自然科学),又属于对于社会关系之中客观规律的索要(社会科学),而且都是逐步升级的索要。“自我生产”中的“自我”,“重新生产”中的“重新”皆可暗示:马氏曾下意识觉察到,人类物种和社会关系都属于天设效用——“自我”意味着自在,“重新”涉及到母型,遗憾的是,唯生产力论即经济仲介决定论,阻碍了马氏从劳动一次划分论者变为劳动二次划分论者。
附带说明,由此观之,邓小平的“科技人员也是劳动者”的论断乃有实证根据,并非只是定心丹丸——这儿的“劳动者”,便是索要劳动者。
美国学者哈·拉斯韦尔将使用价值——又称效用——破天荒地分为八类,即:寿康、财富、技能、启蒙、权力、尊重、正直、情谊。这一分类对于作者此次成功证非马学的巨大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不过作者认为,“情谊”应当扩大内涵与外延,换成“顺悦”——顺觉、愉悦的合称,突破仅涉爱情、友谊之限。“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也是古代中国十万进士所追求的吗?不仅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吧?普通话、广州话以及各地方言,熟人相见,都有“近来怎样,顺还是不顺?”一问。
财富即是令人囊藏增值的实物收入和劳务收入。不过,天设财富和其他七种效用都是天设效用。从种类上说,天设效用与人造效用之比为7.5:0.5,即为100:007,十种效用当中只有零点七种效用属于人造效用。忽视或者无视涉及天设效用的交换的经济科学,显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但这不幸正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科学和中国官方经济学说的现状。
以下作者结合拉斯韦尔本意,针对七种纯粹天设效用再作一番本人有所发挥的解释:
寿康乃指生存和安全(包含健康)。技能可使任何实践——如艺术、手艺、贸易、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传媒等的活动——变为熟练。启蒙涉及资讯、见解、知识、发现等。权力本是政治科学的中心概念,即“A若能达到令B去做其原来B无意去做之事的地步,A便可称对于B拥有权力”——后面还会回到美国学者罗·达尔的这个操作性定义。领受尊重的载体,包含地位、荣誉、承认、威望、荣光、名望等。正直乃一伦理价值,应含美德、善心、忠直、信用等。
生存、安全先于意识、劳动甚至进化、语言出现,自是不必多说。技能可被掌握,知识可被发现,甚至假造,但亦非人力所能制造。权力、地位、名望、正直均属社会关系效用,都与“意欲支配别人”有关——亚里斯多德尝言“人类乃是天生政治动物”。诚哉其言!人类只能在戏剧之中仿生制造权力、地位、名望、正直。人类的顺悦,如快感——饱快感、性快感、成快感、知快感等等、爱感和美感,满意、随意和得意,可被人造效用唤起,亦非人力所能制造。若无回应基因,人类便会呆若木鸡。人类追求喜乐却不追求怒哀:荷兰科学家们的一项研究表明,人类天生就会笑,而哭是后天学会的。也许有人会说,顺悦、名望并不重要,可予删除。其实不然,英国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如果生命只剩两个小时,大多数被询者都会选择与心爱之人互诉衷肠,相拥相吻或者上床做爱,从事灵肉交流而非其他活动,包括为国捐躯之类。而亚当·斯密说得分明:“名誉的尊卑一端,对于一切体面职业,可以说是报酬的大部。”现今不是流行“人气=财气”的公式吗?
上述八种效用尽可进行类内交换,马氏就曾说过,人与人之间“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类际交换对于八种效用来说亦为全然适用。例如:
自杀爆炸:寿康与财富的交换;
高薪聘请:财富与技能的交换;
体脑相长:技能与启蒙的交换;
笔剑互卫:启蒙与权力的交换:
洋人朝廷:权力与尊重的交换;
贞节牌坊:尊重与正直的交换;
冰海沉船:正直与顺悦的交换;
英雄救美:顺悦与寿康的交换。
权钱交易:权力与财富的交换;
官包二奶:权力与顺悦的交换;
财色交易:财富与顺悦的交换;
纳粟拜爵:财富与尊重的交换;
开馆授徒:启蒙与财富的交换;
为帝王师:启蒙与尊重的交换;
好人平安:正直与寿康的交换;
以德服人:正直与尊重的交换。
不耻下问:尊重与启蒙的交换;
危地探险:启蒙与寿康的交换。
类内交换亦然可与类际交换交叉,并行不悖。例如,红军长征期间,刘伯承将军与小叶丹头人之间的枪支(财富与权力)与通道(生存与安全)的交换,同时也是信任与信任的交换——在此乃以歃血为盟公开表达。政治结拜在此代表安全,就像商业信用通常代表安全一样。而对于当代中国普遍百姓来说,权钱交易,财色交易乃是他们见惯不怪的交叉交换——受贿贪官与行贿刁民之间同时交换着信任;好色富商与绯闻女星之间同时交换著名望。
显而易见,索品交换——又可称“社会交换”——的历史、规模、频率、变化,必然远远超过产品交换——又可称“经济交换”,尽管总量未必。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的交叉简称“社经交换”,还原的话,简称“索产交换”。除了交换之外,人类还有赠予、遗传、遗失、分配等让渡形式。在此必须马上声明,在作者眼中,“分配”必然涉及威权:有被分者就有施分者,因此“按劳分配”之中的“分配”实为交换,“按需分配”之中的“分配”才属分配;下面将会谈到“按劳分配”应当改称“按效交换”或者“各取所值”。将“分配”与“交换”和“配置”区别开来,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往的混用已使人们吃尽苦头。交换的原则是平等,分配的原则是差等。显而易见,交换活动只有“交换双方”,但却既没有“施换者”也没有“被换者”,人们仅于语义学的角度,便可觉察得到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分野。马克思错误地将人类经济活动分解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种,乃是因为没有与时俱进或者抽象不够。封建主义社会“君赐”无所不在,“封”即是威权分配;资本主义社会“商取”占了上风,“资”乃为交换所得。
毫无疑问,产品及相关劳务,索品及相关劳务,均可成为商品,只要其被用于交换。
如果商品交换的依据,乃是最后以马氏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准的“劳动时数”的话,那么,一切产品及相关劳务,一切索品及相关劳务,其收凝的或者流淌的劳动时数,就必须是普遍地,恒常地可被间接测量(下文马上谈到何谓间接测量)通约的,即使此种时数乃为变动不居,亦须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某项商品的收凝劳动时数如不可被测量通约,则其交换价值便必不可被确定,如果世间的交换价值乃以劳动时数充当依据的话。读者稍作琢磨即知:在《证非二十义》中,已无必要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随机劳动时间”作出区别对待。
但是,显而易见,只有在相对其他三种劳动形式而言,场地和工具固定,人员和角色明晰,供产和流销重复,产品和劳务分明的生产作业劳动之中,劳动时数才是可被被普遍地,恒常地间接测量通约的;而在没有或者缺乏类似条件的生产经营劳动,索要经营劳动、索要作业劳动之中,劳动时数则是难以乃至无从被间接测量通约的。
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蒂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以下简称“配、布、坎、斯、李、马”)等人的劳动价值学说,不论是一元论的还是多元论的,以及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科学,当代中国官方经济学说,全部都没认真考虑这种“一明三盲”的现象,从而生成人类认知历史之上的最大的一个“黑洞”,人类实践历史之上最大一个错误——两者都是最大,不是最大之一!当然有人会说,没有测量并不等于劳动价值没有凝固其中,作者对此不持异议。作者想说的是,既然没有或者无从间接测量劳动时数,交换之时何能以劳动时数作根据?
作者若是没有学过公差测量、经济统计、概率初阶、高等数学,仅靠美国行为主义学派给予的训练背景,断难捕捉得到此一现象。
生产经营劳动和生产作业劳动乃是一对孪生兄弟,“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鹄的皆为人造效用。但是即使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那刻意与马学奠基“公理”保持一致的“社会主义统计学”,也不无遗憾地声明:不能将经营劳动的成本平摊到作业劳动的成本——即为直接费用亦即合格产品的成本之中去,因为这样做了,便会“歪曲产品成本”,令环比、同比失去信度。众所周知,生产企业时常都会发生经营时数(人均工作时数×人数)虽大幅增加,产品数量却大幅下降的事情,反之亦反是;或者时常发生产品数量虽有升降扬抑,经营成本却为岿然不动的事情;经营时数增加——例如冗员过多,生产企业反而破产的事情亦非少见。显而易见,“生产经营劳动”与“人造效用产出”仅呈因与果正相关,不呈量与量正相关。此谓:生产经营劳动“时不函价”。如前所述,亚当·斯密曾说,生产经营劳动时数“不能保藏起来,备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劳务或曰服务劳动何尝不是这样?
而在索要作业劳动(如中越界山保卫战)和索要经营劳动(如刘备孔明隆中对)之中,由于受到诸多想像得到的或软或硬的条件限制,由于植入人体计时晶片之事迄今尚未普遍发生,劳动时数则是更加难以乃至无从被普遍地,恒常地间接测量通约的。即使个别地、偶然地可被或者易被间接测量通约,一旦时间长度成为要素,人们就会发现:索要作业劳动时数,索要经营劳动时数的升降,与合格索品数量的升降,仅呈因与果正相关,不呈量与量正相关。索要劳动时数换取不到索要劳动成果的事情,更属常见,譬如,什么叫“你死我活”、“誓不两立”?另外,读者不妨掩卷思之:赵匡胤陈桥黄袍加身,历时多久?李自成出陕入主北京,耗年几何?结局异同?享祚长短?
由此可知,出于“条件并不许可”这条极为明显的理由,人类自古以来便从无起念测量通约索品,及相关劳务收凝或者流淌的劳动时数,以便开展与产品及相关劳务的交换,从来没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有人想过测量,似乎也不可能在个、共两相方面加以测量,这不是理论本身有何缺陷,而是索要劳动的不确定性就像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一样,必然会带出“测不准原理”。
由此不难推出:人类若选择劳动时数作交换依据,则商品交换的绝大部分个案,势将无法进行,原因不言自明:若间接测量通约不能行,则劳动工时资料不能全。从理论上说,前文所列十种商品交换,只有第一种、第四种、第六种这三种可以接受间接测量通约,其余七种皆不可以接受间接测量通约,由此可以推知,商品交换的依据绝无可能锁定劳动时数。
下举一则显例,继续说明上理:
以权力、地位交换粮食、货币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卖官鬻爵”制度,由秦及清,持续长达二千年之久。此一制度,辅之以“五均六筦”制度和“以德代道”文化,对于中国的官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官本主义社会,曾经盛行以官名冠平民这种举世罕见的风俗。例如,称读书人为“相公”,有钱人为“员外”,典当商为“朝奉”,医药士为“大夫”,工匠头为“待诏”,官子弟为“衙内”,行婚男为“新郎官”、茶侍应为“茶博士”……此种风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古代中国社会乃为“官入膏肓”。“以官为本”不仅仅反映在“以官为荣”、“十民九牧”、“官刁胜民”之上,而且反映在“权钱交易”、“权粮交易”、“权色交易”之上。一位亲中国菲律宾女议员曾因快人快语道破“中国创造了贪污文化”,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抗议。如果稍变说词,将上语改成“中国具有世上首屈一指的权钱交易、权粮交易、权色交易的传统”,倒是可谓一语中的。读者不难看出,卖官鬻爵的三个具体形式,即上述三种交易,其交换依据完全没有可能归于劳动时数:交易双方曾有何人何时何处间接测量、通约、表达、谈判过收凝于用以交换“国授权力”或者“国颁地位”之中的劳动时数?
商品交换的依据,迄今只有已为当代西方微观经济科学约略点出的“效用序数”一种可资候选。依照作者之见,单位基准效用序数只可能是“匀质效用序数”,不可能是庞巴维克曾作妄断的“边际效用”,本书第17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前述之权威的约·布莱克编之《牛津经济学词典》,关于“匀质效用价值说”并无专设词条,可见该说在西方学术当中还未引起注意,已被边际效用价值说挤兑得不成样子。
源于表现人类心理对于有所需求的索品及相关劳务,或者产品及相关劳务的社会属性或者理化属性的满足程度的“效用序数”,乃是时时处处都可成为商品交换的依据。中国先哲程颐曾经断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由此看来,上述“满足程度”便是可以“人同此心”,而非“异人异心”的。源于“抽象满足”而非“具体满足”——这里是在模仿马氏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效用序数,诉诸的是人脑之内的感知机制,而非人脑之外的测量尺具。此种感知机制乃属于全人类的“类本质”。脑在,则作为交换资料的效用序数必定可得,主观客观熔于一炉;尺在,则作为交换资料的劳动时数未必可得,主观客观从中断裂。以类型学角度观之,效用序数的可得性已然是百分之百,劳动时数的可得性则只是百分之七而已。人类完全没有可能放弃效度高达百分之百的依据,转取效度仅为百分之七的依据。当市场供求平衡之时,价格反映的是未受供求变动影响的“社会静适效用序数”,可称“出清价格”。与主由供方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同,“社会静适效用序数”主由需方决定。
诚然,序数远远不如基数精确。但是在卖方心理、买方心理、货币实值三者均在时时变动的情况下,货币反映价值的精确又有多少意义?久而久之,人类对于精确交换的要求势必趋于减弱,对于模糊交换的认受势必趋于增强,“大概齐”势必驱逐“算死草”,序数势必驱逐基数。世界首富之一巴菲特说得再好不过了:“我宁愿要模糊的正确,也不愿要精确的错误。”月票制、年票制、会员制、合作制等等,就是一类典型的虽然不喜欢锱铢必较,但却可致皆大欢喜的模糊的商品交换方式,换成精确的商品交换方式,反而会令交换双方感到不便。
由上多重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源于配、布、坎、斯、李五氏,峰于马氏的劳动价值学说,可谓万古糊涂之论,误尽世人之说。史达林、毛泽东时代的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带来生产供给恒萎,社会乱象频生一事,业已雄辩说明:锁定劳动时数为交换依据,既然有悖自然法则,必会招惹天谴。至此,共产国家亿兆人民方才明白,不应光是谴责斯毛二氏,还应追溯谴责配、布、坎、斯、李、马六氏——不是总说“行动从思想来”么?
必须指出,人类从事商品交换之时,绝无可能使用多于一种的交换依据。例如,混合使用“产品交换依据”、“索品交换依据”、“产索交换依据”之类,百花齐放;同时绝无可能在不同的交换依据之间来回切换,这就像人类无绝可能一族饮水,一族饮烷,一族饮汞一样。反过来说就是,经济交换必须使用与社会交换,经社交换完全一致的交换依据;各种交换内部,也必须使用与类际交换一致的交换依据。造化教会人类形式逻辑,岂容交换中的同一律横遭破坏?然而,正是马氏本人在他笃信劳动价值由浅入深之前,概念混乱地说过:“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马氏归根结柢竟是效用价值论者!且不说恩氏曾经说过“价值是生产成本对于效用的关系”了。试问:人类大脑灰质有没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的价值评定机制?人类雌雄个体有没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生儿育女机制?
作者相信大脑神经科学今后的发展,必定会为此处主张的命题提供更多更好的实证。在大脑灰质与效用价值之间许有“量子纠缠”。
简而言之,若视劳动时数为价值本数(LV = Labour Value)——价值末数乃为受到供求波动影响的市场价格(MP = Market Price),则此种价值本数只是一种谎量(谎花的谎)或曰岐量(AV = Ambiguous Value)而非信量。匀质效用序数(UUV = Uniform Utility Value)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假包换的,世间唯一的价值本数。就像植物花朵既有又开花又结果的,亦有只开花不结果的一样,劳动时数也既有测时可果的,亦有测时不果的,因此泛泛而谈劳动时数,不管是“社会必要劳动时数”还是“个别随机劳动时数”,只能落入谎量或曰岐量之列。只能如此,岂有它哉?
前人所说“绝对效用”乃指“商品满足人类需要具体属性”:“相对效用”乃指“商品适应市场需要程度”。据此,作者还做一种猜测:抽象效用序数可能就是相对效用序数,亦即商品可得难易程度,此种难易程度乃由四个向度混成:自然资源可得难易程度、四种资本筹集难易程度、制造过程劳动难易程度、产品研发技术难易程度。
出狱以后,作者方才看到国内学者:其一,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罗朝晖所作的一种自人类探讨如何计算价值以来异峰突起的,关于商品如何定价的天才猜测。他的的解释乃与作者香港经商所得经验并无二致。自然科学中亦常见使用这种“因为结果近似不妨以简法代烦法”:
那么,现实当中,生产者或消费者是怎样摆脱劳动价值论者和效用价值论者(因难以计算商品价值而引起的他们——作者注)的烦恼的呢?应该说办法并不复杂,就是利用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加上稍微精确的成本核算。一种新产品上市,它的定价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高于成本价,一种是等于成本价。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会有竞争厂家加入;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因为有超额利润,马上就有竞争厂家加入,知道商品卖价与成本价不相上下。消费者则是参照商品的价格、效用情况及自己的购买力来确定购买数量的,他们的购买数即是供给者的供给数,供给者如果是按照这一数量去生产,则市场上这种产品供求平衡,此时的价格即均衡价格,也即产品的价值。当然,这里面的竞争应该是完全竞争或接近于完全竞争。因而,只要排除了垄断,产品的价值事实上是无需使用价值理论来进行精确计算的。
其二,曹国奇曾以经济学家的嗅觉辨识出“按资分配”、“按效分配”、“权力分配”、“名誉分配”、“救济分配”、“教育分配”,以及“政治和外交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涉及分配标准,以决定各要素、各部门、各国家分得价值(或利益)多少”,其三,郑根权已经认识到了,由于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体,所以相应地剥削有着三种形式,即经济剥削、政治剥削或称权力剥削、文化剥削。政治剥削和文化剥削有着自身的运行方式和规律。读者可从曹郑二氏论述当中,看出本书引述的拉斯韦尔的八大效用分类、伊斯顿的政治定义的影子,说明国内学界大有思想开放兼且明敏之士。不过,可惜的是,曹氏没有想到:“过去无人测量权力、名誉劳动时数,权钱权色交易、人气财气转换也可实现”这一要害问题。郑氏未能从“剥削乃为源自持续的不平等交换”这一点,进一步悟出“人造效用与天设效用交换、天设效用与天设效用交换必不可能以劳动时数为根据”。
第一章的核心概念,可以浓缩成为六字:索品无法测钟。
如前所述,在广州话里面,“钟”指时间,此处和以下引申为“决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时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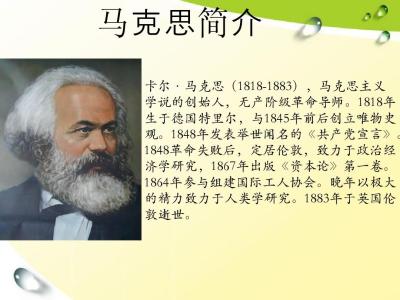


美国学者哈·拉斯韦尔

美国学者大卫·伊斯顿

中国学者郑克中颠覆马学元论巨著
开放2017-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