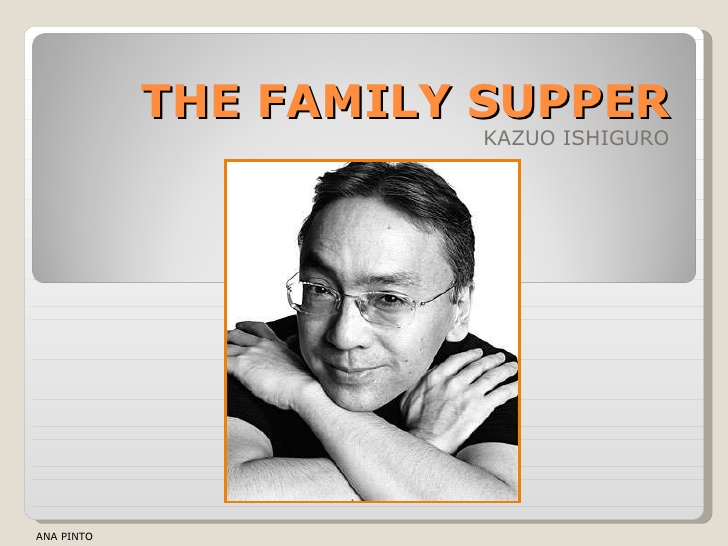河豚是日本太平洋沿岸所捕的一种鱼。自从我母亲因吃河豚身亡以来,这种鱼对我而言就有了特殊意义。毒素存于河豚的性腺,在两个易破的袋囊里。在收拾鱼时,这两个袋囊必须慎重清除,手笨就会导致毒素渗入河豚的血管。遗憾的是,不容易辨别进行这一手术成功与否,一向是吃了才有证据。
吃河豚中毒非常痛苦,几乎总是致命的。如果是在晚上吃鱼,那么中毒者通常在熟睡中被疼醒,辗转几个小时到早晨死去。这种鱼在日本战后曾极受欢迎,直到制定更严格的规定前,曾经非常时兴在自家厨房里进行这项危险的解剖手术,然后遍邀邻居和朋友们赴宴。
在我母亲去世时,我正住在加州。我与父母的关系在那段时间里变得有些紧张,结果我没听说她去世前后的情形,直到两年后才回到东京。似乎是,我母亲曾总是拒绝吃河豚,但在那个特殊场合破例了,受到一位她不愿冒犯的老校友邀请。在从机场开车去镰仓区的父亲房子时,正是他向我提供了细节。当我们终于到家时,已接近一个晴朗秋日的尽头。
“你在飞机上吃了吗?”我父亲问。我们坐在他茶室的榻榻米地板上。
“他们给了我一顿小吃。”
“你一定饿了,菊子一到,我们就吃。”
我父亲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人,坚石般大下巴,浓黑的怒眉。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很像周恩来,虽然他不会稀罕这种比较,而特别自豪家族的纯正武士血统。他的一般表现不是让人可轻松交谈的人,他每句说明都好像下结论的怪癖,更于事无补。其实,当我那天下午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一个儿时的记忆就回来了,记得当年因我“像一个老太婆那样喋喋不休”,他在我头上敲打过好几次。自我到机场以来,我们的交谈已经不可避免地有多次长时间停顿。
当我们两人有段时间无话后,我说:“听说了公司的事,我很难过。”他沉重地点点头。
他说:“其实,故事到此还没完。渡边在公司倒闭后自杀了,他不愿忍辱偷生。”
“我明白。”
“我们合作了十七年。一个有原则和荣誉感的人。我非常敬重他。”
“您会再做生意吗?”我问。
“我——退休了。现在我太老,没法投身新的冒险了。如今做生意大不同了。对付外国人,按他们的方式做事。我不明白我们怎么到了这个程度,渡边也不明白。”他叹了口气,“一个好人,一个有原则的人。”
茶室看出去是庭园。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古井,现在通过浓密的树叶隐约可见,我儿时认为那里有鬼魂出没。太阳已低沉了,大部分庭园已落入阴影。
父亲说:“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决定回来,我希望不止是一个短访。”
“我不确定我的计划会是什么。”
“我个人准备忘记过去。你母亲也曾总是准备欢迎你回来——像以往那样因你的行为烦恼。”
“我感谢您的宽容。正像我所说,我不确定我的计划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相信你心里没有恶意,”父亲继续说:“你受到某些——影响而动摇,像许多其他人那样。
“也许我们应该忘记它,像您建议的那样。”
“随你便。再来点茶?”
就在那时,一个姑娘的声音穿屋而来。
“终于来了!”父亲站起来,“菊子到了。”
尽管我和妹妹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一向很接近。再次见到我似乎令她非常兴奋,有一会儿,她不做什么只是神经兮兮地咯咯笑。不过,当父亲开始问她大阪和大学的事时,她总算平静下来。她以简短正式的回应答复他。她然后问了我几个问题,但她似乎受制于担心她的问题可能引到尴尬的话题。过了一会儿,谈话变得比菊子来前更稀少。然后,父亲站起来说:“我得去做晚饭了。请原谅,我要承担这些事务。 菊子会照料你。”
一旦他离开房间,妹妹明显放松了。几分钟里,她闲聊她的大阪朋友和大学课程,然后突然决定,我们应该去逛逛园子,并走上外廊。我们穿上放在外廊鞋架上草凉鞋,步入庭园。日光已几乎消失了。
“过去半个钟头,我想抽烟得要死。”她说着点了一只香烟。
“那你为什么不抽呢?” 她向屋子做了个鬼脸,然后调皮地笑了。
“哦,明白了!”我说。
“猜到了吗?我现在有个男朋友。”
“哦,是吗?”
“不过我正疑惑该怎么办。我还没有下决心。”
“很可以理解。”
“你看,他正在计划去美国。他希望我一完成学业就和他一起去。”
“明白了。你想去美国吗?”
“如果我们去,我们要搭便车。”菊子在我面前竖起拇指。 “人们说这很危险,但是我在大阪做过,没事。”
“明白。那么你不确定什么呢?”
我们正沿着一条穿过灌木丛到老井的狭径走。在我们散步时,菊子坚持不懈地把香烟不必要地抽得戏剧化的烟气腾腾。
“是这样,我现在大阪有很多朋友。我喜欢那里,我还不确定想完全离开他们。而修一,我喜欢他,但我不也确定想花那么多时间和他在一起。你理解吗?”
“哦,完全理解。”
她又笑起来,然后跳到我前面,直到那古井。
“你记得吗?”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说:“你过去是怎么说这口井闹鬼的?”
“是的,我记得。”
我俩都盯着旁边。
她说:“母亲总告诉我,你那天晚上看到的是菜店的老太太。但是,我从没有相信她,也从没有一个人来这里。”
“母亲过去也告诉我这个。她甚至告诉我,那老太太有次坦承自己是鬼。看来,她是从我们园子里走近路。我想象她翻过这些围墙有些麻烦。”
菊子咯咯一笑,然后她转身背向古井,扫视庭园。
“母亲从不责怪你,你知道。”她以新的声音说。我保持沉默。“她过去总是对我说,那时如何有错,她和父亲的错,因为没有好好带你。她过去告诉我,他们和我一起如何小心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好。”她抬起头,调皮的笑容回到了她脸上,说: “可怜的母亲。”
“是的,可怜的母亲。”
“你要回加利福尼亚吗?”
“我不知道。我还得看看。”
“怎么样了 ——她?薇奇?”
“那都完了。在加利福尼亚,现在对我没留多少了。” 我说。
“你认为我该去那里吗?”
“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你可能会喜欢它。”我向屋子瞥了一眼。“也许我们最好早点去。父亲做晚饭可能需要帮手。”
但是妹妹又一次盯入井下,说:“我看不到任何鬼魂。”有点回声。
“父亲对他的公司倒闭很苦恼吗?”
“不知道。你永远没法在跟父亲说话时辨别出来。”然后,突然她直起身来,转向我:“他告诉过你关于老渡边吗?他做了什么吗?”
“我听说他自杀了。”
“啊,那不是全部。他把全家都带走了,他太太和两个小姑娘。”
“哦,是吗?”
“那两个美丽的小姑娘。他在他们全部睡着时拧开了煤气,然后用切肉刀切腹了。”
“是的,父亲正是告诉我,渡边是个如何有原则的人。”
“有病。”妹妹转向井。
“小心点,你会掉进去。”
“我看不到任何鬼。你那时一直在骗我。” 她说。
“但是我从没说过它住在井下。”
“那么它在哪里呢?”
我俩环顾四周的树木和灌木丛。园里的光线已变得很暗淡。最后,我指向大约十码远的一处小空地。
“就在那里我看到它,就在那里。”
我们盯着那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
“我看不太清楚,当时天黑了。”
“但你肯定看到了某个东西。”
“那是个老太太。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
我们一直盯着那地方,好像被迷住了。
我说:“她穿着一件白色和服,有些头发已经脱落了。当时吹起一点风。”
菊子用手肘推我的胳膊,“哦,静静吧!你又在试图吓唬我。”
她踩熄了烟头,然后以困惑的表情站着看了它一会儿,踢了些松针在其上,然后再次露出笑容说:“让我们看看晚饭是否好了。”
我们在厨房里找到父亲。他扫了我们一眼,然后继续他在做的事。
“父亲成了个像样的厨师,自从他不得不自管自。”菊子笑着说。他转过头,冷冷地看着她。
“很难说是我自豪的技能。”他说:“菊子,来这里帮个忙。”
有一会儿,妹妹没动。然后她迈步向前,从一个抽屉里拿出围裙。
他对她说:“只是这些蔬菜现在需要料理,其余的只需要看着。”然后他抬起头,奇怪地看了我几秒钟,最后说:“我预料你想看一圈这屋子。”放下一直拿着的筷子,又说:“你很长时间已经没看过它了。”
当我们离开厨房时,我回头瞥了菊子一眼,但她背转身了。
“她是个好姑娘。”父亲平静地说。
我跟着父亲从一个个房间走。我已经忘了那屋子有多大。一扇拉门会滑开,另一间房会出现,但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在其中一间房里,灯没有亮起,我们盯着在窗外苍白光线下的僵死的墙壁和榻榻米。
父亲说:“这屋子对一个人孤身居住太大了,现在我没怎么用大部分房间。”
但是最终,父亲打开了一扇门,那是个充满书籍和纸张的房间。花瓶里有花,墙上有画。然后,我注意到在房间角落一张矮桌上的东西。我走近后,看到那是一个战舰的塑料模型,某种供儿童建构的玩具。它被放在一些报纸上,四周散落着各式各样的灰色塑料。
父亲大笑一声,他走向桌旁,拿起那模型。 “自从公司失败,我手头有了更多点时间。”他说完再次大笑起来,相当怪。一会儿,他面容看起来几乎温柔了,“多了一点时间”。
我说:“看来怪了,你曾经总是很忙。”
“也许太忙了,”他微笑着看着我,“也许我本应该是一个更尽心的父亲。”
我笑了。他过去注视他的战舰,然后抬起头说:“我本不想告诉你,但也许我最好还是说了。我相信你母亲的死不是偶然的。她有很多忧虑,还有一些失望。”
我们都盯着那塑料战舰。
我最后说:“当然,母亲没期待我永远住在这里。”
“显然,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对某些父母是怎样的。他们不仅必须失去孩子,而且必须把他们让给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 他用手指旋转那战舰。“这里的这些小炮艇本来可以更好地胶合,你不认为这样吗?”
“也许吧!我认为它看起来不错。”
“在战争期间,我在很像这样的船上度过一些时间。但我的雄心壮志一直是当空军。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的船被敌人击中,你所能做一切就是在水中挣扎,盼望有救生线。但是,在一架飞机上,嗯,总是有最后的武器。”他把那模型放回桌子上,“我不认为你相信战争。”
“不特别相信。”
他用一只眼睛环顾房间,说:“现在晚饭应该好了,你肯定饿了。”
晚饭在厨房旁的一个灯光昏暗房间里等着。唯一的光源是挂在桌子上方的一个大灯笼,将房间其余部分投入阴影。我们在开始吃饭前相互鞠躬。
几乎没有交谈。当我对食物做了点礼貌评论时,菊子咯咯一笑。她以前的紧张似乎已经回到她身上。父亲几分钟没有说话,最后他说:
“你一定觉得生疏了,回到日本。”
“是的,是有点生疏。”
“也许,你已经后悔离开美国。”
“有点,没那么多,我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只是些空房间。”
“明白。”
我瞥过桌子一眼,父亲的脸看来像石头,在半明半暗下森严壁垒。我们沉默地吃着。
然后,我的眼睛在房间后面抓住了某些东西。起初我继续吃,然后我的手不动了。其他人注意到并看着我。我盯入父亲肩后的黑暗。
“那是谁?那里的那张照片中?”
“哪张照片?”父亲稍稍转身,试图跟随我的目光。 “最低的那张。穿着白色和服的老太太。”
父亲放下他的筷子。他先看照片,然后看我。
“你母亲。”他的声音变得很生硬, “你不能认出自己的母亲吗?”
“我母亲。你看,黑黑的,我无法看得很清楚。”
几秒钟没人说话,然后菊子起身立脚,从墙上取下照片,回到桌旁,递给了我。
“她看起来老多了。”我说。
“那是去世前不久拍照的。”父亲说。
“黑黑的。我无法看得很清楚。” 我抬起头来,注意到父亲伸出一只手。我递给他照片,他专心地看它,然后把它递向菊子。妹妹乖乖地再次起身立脚,把照片送回墙上。
桌子中央有个没开盖的大锅。当菊子再次坐下时,父亲伸手揭起盖子。一团蒸汽升起,蜿蜒飘向灯笼。他把锅向我推了一下。
“你肯定饿了。”他说,一面脸已陷入阴影。
“谢您了!”我伸出筷子,蒸汽几乎烫人。“这是什么?”
“鱼。”
“闻起来很好。”
汤里面是些几乎卷曲成球的鱼条。我夹出一块放到我碗里。
“请自便,有很多。”
“谢您了!”我多取了一点,然后把锅推向我父亲。我看着他取了几块放到他碗里。然后,我们都看着菊子为自己料理。
父亲微微鞠躬,又说:“你肯定饿了。”他把鱼放到嘴里开始吃。然后,我也选了一块放进嘴里,感觉柔软,肉味令口舌生香。
“很好吃。”我问:“这是什么?”
“就只是鱼。”
“它很好吃。”
我们三人沉默地吃下去。几分钟过去了。
“多来点?”
“够吗?”
“有很多够我们大家的。”父亲揭起盖子,再次蒸汽升起。我们都向前伸手自便。
我对父亲说:“这里,您吃这最后一块。”
“谢谢!”
当我们吃完饭后,父亲伸展双臂,满足地打了个哈欠,说: “菊子,请准备一壶茶。”
妹妹看看他,然后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房间。父亲站了起来。
“让我们到另一个房间休息,这里面热了点。”
我站起来,跟着他进了茶室。大滑窗一直打开,从庭园里放入微风。有一会儿,我们默默坐着。
“父亲!”我终于说话了。
“什么事?”
“菊子告诉我,渡边先生带走了他全家。”
我父亲垂眼点点头。有一会儿,他似乎陷入沉思,最后说:“渡边非常专注于他的工作。公司的倒闭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怕这一定削弱他的判断力。”
“你以为他做了什么——那是个错误?” “为什么,当然。你有其它看法吗?”
“不,不,当然没有。”
“除了工作外还有些其它事情。”
“是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虫鸣声从庭园里传来。我向黑暗中望出去,那井已不复可见。
“你想现在要做什么吗?”父亲问:“你会在日本留一阵吗?”
“说实话,我以前还没有想过那么远。”
“如果你想留在这里,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屋子里,你会非常受欢迎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介意和一个老人住在一起的话。”
“谢谢您!我还得想想。”
我再次向外看入黑暗。
父亲说:“但当然,这屋子现在这么沉闷。你无疑会返回到美国。”
“也许吧!我还不知道。”
“毫无疑问,你会的。”
有段时间,父亲似乎在研究他两手背。然后,他抬头叹气。
“菊子在明年春天将完成学业。”他说: “也许那时她会想回家。她是个好姑娘。”
“也许她会。”
“那时事情会改善。”
“是的,我相信它们会。”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等着菊子拿茶来。
(张裕 译)
原文:A Family Supper,by Kazuo Ishigu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