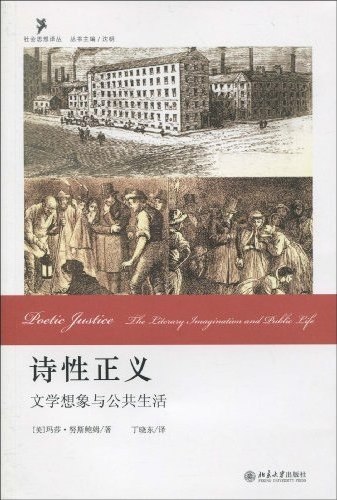 “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感召,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同情的姿态去关注那些弱者;而文学性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全面和更人性化的态度去对待人和人性。”
“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感召,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同情的姿态去关注那些弱者;而文学性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全面和更人性化的态度去对待人和人性。”
寻求一种恰当的正义标准,这一梦想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的孔子就曾经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 而在西方的《圣经》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2] 这些简约但却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正义准则,构成了一个政治社会中人们相互交往和判断事物的中立性标准。[3] 晚近以来,思想家们构想了一些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具有争议性的正义理论,例如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标准的功利主义,以财富最大化或效率最大化作为标准的经济学。这些正义规范和正义标准不仅在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正义(Justice)的同义词,在司法中寻求一种中立性标准同样贯穿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4] 无论是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司法的不偏不倚对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都非常重要。而且,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司法中的中立性往往更为具体、更为即时、更具对抗性和更为敏感,一旦裁判者有所偏颇,无论是法律问题还是案件事实问题,都会立即引起当事人和相关受影响群体的不满。因而,如果司法无法找到一种比较客观中立的司法标准,如果司法为摇摆不定的个人偏好所影响,或者为党派政治所操控,那么司法的中立性和正当性就将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法治这一理念也将面临合法性的拷问。[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正义与司法规范的渴求成了学术界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学术理论迫切需要探索恰当的正义和司法标准,并对它们做出正当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各种正义和司法标准之间也形成了相互竞争、批判和互补的复杂关系。
作为一名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学领域学养深厚的学者,努斯鲍姆显然对经济学提供的正义标准感到不满,对经济学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日益主导的话语权深为担忧。在《诗性正义》中,她以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为材料,对经济学及功利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诗性正义,一种建构在文学和情感基础上的正义和司法标准。
然而,这种诗性正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正义呢,它能够成为正义和司法标准的有力竞争者,特别是成为经济学功利主义和法律经济学的替代者吗?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所做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其中的批判有多少是出于真知灼见,有多少是因为疏漏和误解?诗性正义到底能够为正义理论和司法实践,甚至为更一般的公共领域提供什么?在进入本书之前,很多读者的脑海中或许都盘旋着这些问号。
一、经济学功利主义与诗性裁判
19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法学内部也涌动着“科学化”的内在冲动,法律人和法学学者试图将法律本身科学化,或者借助其他社会科学的工具将法律科学化,以寻求一种类似科学的中立性。在这些努力中,对当下学术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以成本-收益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方法,这种经济学功利主义试图通过对人类行为建模而建构一种单一和明确的正义规范和司法准则。
就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来说,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例如,它们都将个人看作“理性”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私自利的;它们认为,即使一些看似利他主义(altruism)的行为,也常常是出于为自己博取名声的考虑,以便在未来的博弈中获取好处。因此,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研究者大都相信,使得人们遵循法律或驱动人们行为的动机就在于个人对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同时,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都以追求效率最大化或者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将效率的最大化或财富的最大化作为规范性的目标,作为正义和司法的标准和指引。[6]
对于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批判、反思以及争论一直不绝于耳。有的学者质疑个人理性主义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人们的日常行为和遵守法律是否真的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7] 有的学者则批判效率最大化或财富最大化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上并不恰当。[8]
与这些对理性主义假设的方法论和财富最大化或效率最大化的质疑不同,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中提出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进路。努斯鲍姆认为,成本-收益分析的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首先会带来人的“物化”。功利主义并不将人作为一个个独特的“人”来看待,而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将人看作是效用的载体和容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个人甚至还比不上一只可以被清晰计算的昆虫那样具有独特性”。“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质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根本的界限,还是他们选择的自由,都将是可有可无的”。[9]在“物化”的指控和批判之外,努斯鲍姆还指出,由于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不能具体和同情地对待个人,这种思想和态度往往导致模式化的群体印象,导致同情和怜悯的缺失,并因而导致群体仇恨和群体压迫。
在对经济学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之后,努斯鲍姆提供和阐述了一种与文学和情感相关的诗性正义。这种诗性正义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位置,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fancy)”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性”。努斯鲍姆认为,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文学想象和情感能够在这种中立旁观者的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学,特别是小说这一媒介,能够让我们触摸到事物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能够引起我们对于普通事物的关心,能够让我们通过“移情(empathy)”和远处的人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一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无疑比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正义标准具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无疑能够为正义和司法提供更加可靠的中立性标准。至少,它能够为正义和司法的中立性标准提供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
从学术推进的角度来说,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的批判拓展了新的论证思路和论辩方式。从人的“物化”和群体仇恨等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和其他僵化的社会科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可以说,这种批判是对经济学功利主义和社会科学只注重“事实”的不满,对这些理论所导致的异化的不满。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努斯鲍姆所宣扬的诗性正义正是一种努力关注“人”的视角,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术姿态和人文关怀。
二、把人当作物看还是把物当作人看?
上文已经提到,在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的批判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经济学功利主义将人当作物来对待,从而用一种僵化的物化的视角来看待具有独特性的人和人性。经济学功利主义“只观察那些能够进入实用主义计算的东西……对可观察世界的质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对人们的独立性,对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希望、爱和恐惧视而不见;对人类生活是怎么样的和如何赋予人类生活以人类意义视而不见。”[10] 在这样的视角下,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被抛弃了,人的质性差别被抛弃了,人仅仅被当作一个统计数字来对待,或者被当作一种粗糙的简陋的物体来对待,就像阿玛蒂亚·森和伯纳德·威廉斯所描绘的:“人就像被当作分析全国汽油消费量的单个油槽车,而不是被当作独特的个体。”[11]
为了剥析这种经济学视角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和扭曲,努斯鲍姆借用了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对小说主人公葛擂硬的分析和批判,揭露了经济学的这种视角如何导致扭曲的现实。葛擂硬是一名宣传自己只相信“事实”的教育家,“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称一称、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分量和数量”[12]。葛擂硬以这种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教育自己的子女,并且身体力行地将功利主义应用在生活中。但吊诡的是,这种功利主义的向导却出现了种种扭曲、悲惨以及令人深思的后果:葛擂硬的女儿露意莎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嫁给了银行家庞得贝,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葛擂硬的儿子成了小偷……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力图以“数字和事实”来衡量人们的幸福,但结局却恰巧相反。忽略了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功利主义理论无法把握和追求人的真正幸福。
在《诗性正义》中,努斯鲍姆还特别提到了《艰难时世》中的一幕,以表现发展到极致的功利主义理论会产生多么荒谬的后果。葛擂硬太太深受葛擂硬式功利主义的影响,当她病倒在在床上,她的女儿询问她是否难受时,这位葛擂硬式功利主义的信徒这样回答:“我想这屋子里总有什么地方难受……但是我不能确定地说就是我难受。”[13]在葛擂硬式哲学的操控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人至此已经被彻底的物化了。葛擂硬太太不仅仅将他人当作物来看待,更已经将自身也当作物来看待了。
努斯鲍姆显然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这一视角持批判态度。在努斯鲍姆看来,经济学功利主义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这一视角是贫乏而僵化的,这一视角抹杀了人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无法真正捕捉人和人性的真实需求。努斯鲍姆主张,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应该建立在对人和人性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洞察之上,而不是简单和粗糙地将人当作物体来对待。[14]
事实上,努斯鲍姆不仅主张必须以人性的态度对待个人,以一种想象和同情的态度去观察个人,而且,努斯鲍姆还主张以人性和情感去观察自然世界,将“物”当作“人”来看待。在《诗性正义》中,努斯鲍姆描绘了她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课堂上的经历,描绘了一位学生听到童谣后的感受:童谣让他回想起那些闪烁的群星,那些灿烂的银河,童谣让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他的小猎犬,他开始变得“希望注视着这只狗的眼睛,想象这只狗在感受和思考什么,想象它是否会感受到伤感……”[15] 我们不难理解,努斯鲍姆之所以不仅仅主张将“人”当作“人”来对待,而且要将“物”也当作“人”来对待,根本的目的在于这种将物“人化”的努力最终将能够培养人们对于世界丰富性的理解,能够培养人们的同情和感受事物的能力。[16]
兼听则明,现在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学者是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的。波斯纳在论述物和人的“心智(mind)”的时候认为,我们对物和人的心智的专注恰巧说明了我们对世界了解的贫乏。例如我们对于猫的活动不了解,我们就会把猫说成是有心智的,“就像我们假定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并以此来预测和规制他人的行为一样”,通过把猫说成是有心智的,这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预测和掌握猫的行为。而“一旦人们更多了解世界时,被认定是精神的实体和状态的总量就会减少”。波斯纳提到,在古代,由于人们对一些不熟悉的物体,例如大海知之甚少,这就会使得人们把大海看作是有心智的,或者虚构一个脾气暴躁的海神来说明大海,然而,一旦人们对事物的信息了解更多,特别是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之后,那么人们就不再会将物“人格化”。[17]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波斯纳引用霍姆斯在《普通法》中的论断,提出了“不要把危险物品当作人来对待,而是要把危险的人当作物品来对待。”[18] 这一姿态和视角认为,随着我们掌握越来越多的信息,我们就会抛弃那些将物体看作人的视角,将事物神秘化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把人当作物来对待和控制。显然,根据信息来分析和看待人显然比根据心智或情感而做出的推理要更加准确,更加有效。
这里呈现的是两种非常有趣的对立立场。以努斯鲍姆为代表的一方主张看到个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甚至主张以移情的态度去看待事物。努斯鲍姆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地观察到世界的丰富性,才能理解人和感受人类生命的意义,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类真正的需求。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把人当作物来对待,以行为主义视角来分析和研究人,这是一种除魅式的历史进步,是人们更加了解世界和人的必然结果。在波斯纳看来,努斯鲍姆追求理解“人性”,甚至以“人性”看待物的追求反应了人类认识能力的贫乏,是人类无力认识世界所采取的“迷信”视角。
初看上去,这两种立场似乎也是高度对立、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二者的立场,却可以发现二者完全可以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努斯鲍姆主张以人性的视角去看待人和物,这是一种促进和提高人们道德能力的方式,也恰巧是一种拓展人们经验边界,获取更多信息的方式。而波斯纳主张的行为主义视角是一种分析世界的学术视角,其目标是通过不断的知识累进和试错来加深人们对世界和人的把握。即使这种“物化”的视角本身可能带来一些偏见和盲点,那也是技术上的错误,可以通过学术的批判和推进来进行修正,而并不能说明这种视角本身存在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的分歧其实主要是运用领域的分歧。努斯鲍姆更多关注的是生活领域的人的生活视角,唯恐“物化”的视角会导致葛擂硬式的僵化和扭曲,导致人们对人和人性的丰富性视而不见,导致人们爱和同情的道德能力的缺失。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则更多在学术领域践行着他们“冷酷”的行为主义视角,并不反对在生活领域采取努斯鲍姆的人性化视角。
因此,努斯鲍姆对行为主义视角的批判虽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却也仍然面临着错位的可能。一个法律经济学者在学术上将物当作人看,但在生活中,他却完全有可能以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人和物。同样,一个经济学功利主义在学术上或许相信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生活中,他却很有可能是一个道德水准超过一般人的利他主义者。虽然努斯鲍姆引用了两篇文献,希望证明学习了功利主义经济学模型的学生的确会变得更加自私,更加关注个人利益,[19] 但要证明学术领域的视角的确会较大程度地影响生活领域的视角和道德水准,显然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两者的相关性。在此之前,经济学功利主义和法律经济学的学者完全可以声称,他们的研究虽然把人当作物来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在生活中看到人类生命的意义和复杂性,不妨碍他们以非常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每一个人和每一种事物,就像惠特曼一样 “听见种种不同的颂歌”。[20]
三、群体区分与群体歧视?
除了行为主义的视角,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另一批判是,经济学功利主义常常不能具体地对待个体,常常以数字或群体来概括某一类人,这种做法很可能导致群体歧视和群体仇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恶毒偏见常常来源于把负面特征归于整个群体……通过把群体描绘为完全低于人类的,描绘为歹徒、卑鄙的人甚至是‘货物’,这样一种倾向排斥关于群体成员中的一人或多人的个人性认知。” [21] 相反,努斯鲍姆认为,文学想象和情感则能够赋予人们畅想的力量,去想象和理解那些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个人的生活,文学和想象能够使得我们融入那些被排斥的个体生活中,使得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对世界进行反思,而不仅仅为那些僵化的数字和模式化的群体印象所蒙蔽。
是的,我们身边充斥了太多的歧视和压迫,充斥了太多对个人熟视无睹的群体仇恨:从地域的歧视到种族的歧视,甚至到纳粹的种族灭绝,这些是否都在一定程度上和缺乏理解个人与同情个人相关?是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的思维习惯有关?
毋庸置疑,这二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太容易因为某个人的举止或某些原因就歧视和排斥某些人,就把某一类人划分为一个群体,把他们看成恶棍甚至是低人一等的动物。相反,如果我们拥有更强大和更具同情心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喜怒哀乐,想象每一个个体也和我们自身一样拥有丰富的人性,拥有值得我们尊重的一面,那么也许我们就会以一种更加同情和认同的姿态去看待他们,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区分和贬低为某一类人。
这样一种正确和同情对待个人,避免群体区分和群体歧视的做法自然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然而在生活中,这一理想的目标却面临着种种制约条件。
首先,一个复杂的社会需要正常运转,就必须要提供足够的信息量,而这就必然要求进行群体区分。在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由于社会的规模很小,每个人对他人的信息掌握往往比较全面,也因此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对于比较讲信用的人,可以不用订立合同,只要口头承诺就可以了;对于油滑奸诈之徒,则必须谨慎地采取多种措施加以防范,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对于蛮横粗暴和有攻击倾向的人,则要告诫自己和家人尽量避开他,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对于患传染病的人,则要防止不必要的接触,以免受到感染。在这样一个理想型的小型社会中,所有的信息都是个人化的,并不存在群体区分的必要。然而,在一个复杂的陌生人社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由于社会规模的庞大,个人掌握信息的有限,信息也随之变得异常缺乏。我们不知道谁是有才能的人,谁是讲信用的人,谁是奸诈之徒,谁有暴力倾向,谁又带有传染病。而现代社会的紧迫感又不允许我们用大量的时间去慢慢甄别每一个人,掌握每一个人的信息,很多决定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群体区分就成了信息甄别和信息传递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式。通过多重的群体区分,社会给个人贴上了种种的标签,把个人归类于各种不同的群体中。通过学历,证书,外形,谈吐甚至是衣着的区分,社会传递着包括能力,健康,暴力倾向等各种信息。在求职场上,名牌大学的学历就是其能力的一种证明,尽管就某个个人来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未必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更优秀。同理,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绅士风度将传递一个信息,即这一类人总体是比较安全的,相反,而衣衫不整和粗野的举止意味着这类人群的危险倾向要大的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群体的划分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也完全无法避免。即使在努斯鲍姆自身的叙述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她用纳粹和种族主义者来形容某类人群。
其次,如果群体区分和群体评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群体区分和群体评价的时候避免群体歧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提醒的是,并非所有所谓的“歧视”都是群体歧视,一些歧视其实只是正当的负面评价。对于那些滥杀无辜的孟买恐怖分子,大概没有人会把对他们的谴责和愤怒看作是群体仇恨,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大概也没有人会认为辱骂他们是群体歧视。只有当群体评价扭曲了现实,转化为不正当地评价时,群体歧视才能称作真正的歧视。
而在现实生活中,正当的负面评价与不正当的负面评价或歧视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难以区分。由于上文提到的社会信息贫乏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群体区分必然会使得信息无法正确地评价群体中的个人。而这将使得群体区分面临模糊化的问题,使群体评价同时具有正确评价的功能和带有偏见的部分。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由于某个群体中的部分成员或大部分成员的恶劣行为,社会就将这一群体划分为“坏人”,从而冤枉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好人”。例如,由于传销在中国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后果,传销人员在大众眼中俨然已经成为了犯罪分子,尽管其中的确有一些正规和正牌的传销人员。
由此可见,信息传递和群体区分所导致的连带责任将使得群体歧视无法根除。我们当然希望既实现社会舆论对于群体的正确评价,又不在这一过程中冤枉一个好人。然而,这毕竟是理想状态。只要整个社会存在对信息的巨大需求,而社会又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量,那么群体区分和群体连带就将不可避免,信息扭曲和个人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将不可避免。[22]
努斯鲍姆对群体区分和群体歧视的担忧是其引入文学和情感的一个重要理由。然而,这里的分析显示,群体区分似乎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信息传递手段,群体评价也是一个社会实现信息功能的重要方式。只要存在复杂的陌生人社会,这一点就无法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也许只是尽量以更准确地方式去评价某个群体,同时警惕以族群的划分来评价某类群体,警惕僵化的模式化印象操控我们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努斯鲍姆所提倡的文学和情感想象正可以构成群体区分的一个补充,而不是颠覆。通过对他人生活经验的同情性想象,文学和情感能够让我们能以最大同情的态度去拓展我们的生活边界和经验边界,能够帮助我们去除那些未经反思的歧视和仇恨,尽量做出真正负责任的群体评价,防止那些基于偏见的群体仇恨和群体歧视。
四、诗性正义的可能和限度
通过分析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倾听来自被批判者的声音,我们可以发现,努斯鲍姆的有些批判至少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这些批判只是表明了经济学在技术上存在问题,而不能表明经济学存在根本性的方向错误。因此,正如努斯鲍姆自己提到的,她所提出的基于文学和情感的诗性正义也许更多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并不能成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正义标准,一种替代法律经济学的司法规范。
但是,即使我们降低期望,把诗性正义作为经济学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我们也不禁还是要是问,基于文学与情感的诗性正义凭什么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正义标准?文学与情感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一种无偏私的中立性标准,真的能够给予那些被忽视的盲点以关切,“不让任何一个人受怠慢或被遗漏”?[23]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努斯鲍姆提出的诗性正义到底有何特殊之处,诗性正义和其他正义规范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发现,就学术渊源来说,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继承了休谟和亚当·斯密曾经提出的旁观者的正义。这一正义标准依赖于明智的旁观者(judicious spectator)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对事物做出中立和审慎的裁判。旁观者的身份保证了明智的旁观者自身不会和当前的事物有利害关系,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做出偏私的裁判。同时,明智和审慎保证了旁观者对事物进行全面和足够的了解,保证了判断不是敷衍和轻率的。
努斯鲍姆的贡献在于,她将文学和情感注入到了这个明智旁观者的身上,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旁观者身份的构建。文学和情感能够带来畅想,能够带来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文学对于普通大众的兴趣,情感对于那些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的关注,能够使得读者和旁观者尽量深入和全面地掌握事物的每个方面。在文学和情感的关注之下,旁观者的视角将变得更为公正和明智。正如努斯鲍姆所写的,这样一种文学裁判将“是亲密的和公正的,她的爱没有偏见;她以一种顾全大局的方式去思考,而不是像某些特殊群体或派系拥甭那样去思考;她在‘畅想’中了解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24]
然而,在将文学和情感引入明智旁观者身份的同时,也显然会引起新的疑虑和问题。首先,尽管努斯鲍姆将文学描绘为关注普通人和弱势群体的典范,描绘为同情地认识被排斥群体和个人的有力途径。但是,文学并不总是具有道德教益的,很多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道德教益,甚至“充满了作者显然支持的道德暴行”:例如蔑视穷人、体弱者、老人、残疾人,以及鼓吹暴力,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25] 波斯纳不无讽刺地写道:“甚至狄更斯也不是安全的;《艰难时世》表达了他对工会的极端憎恶,《雾都孤儿》表达了他的反犹主义;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有性别歧视。”[26] 可以想象,在这些道德不正确的文学作品的感染下,读者和旁观者被引起的情感可能就不会是努斯鲍姆希望的同情、怜悯以及仁慈。相反,文学有可能蒙蔽了读者的视线,引起读者内心野蛮和仇恨的情感。
其次,即使是同情、怜悯和仁慈的情感,也同样可能引起其他问题。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批判是,经济学功利主义往往忽视那些弱者的需求,往往为僵化的数字思维所束缚,而同情的情感则有助于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关注这些被遗忘者的生活。但是,同情的情感在道德层面上虽然总是值得追求的,但在不少时候,同情也会带来负面的效果,特别是在制度层面和公共政策层面起到负面作用。对于这一现象,最著名的讽刺莫过于《西游记》中的唐僧,“很傻很天真”的唐僧总是非常容易施舍同情,而往往看到不到真实世界其实“很黄很暴力”。在现实社会中,这一现象也并不少见,人们常常因为某一现象而责怪某种制度,企图改变某种制度,但却因此而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或者,人们因为同情某些人而设立某种制度,但结果却很可能是因此损害了其他,甚至是更弱势群体的利益。[27]从高尚的同情到妇人之仁的同情,有时候仅仅是一步之遥。
努斯鲍姆显然没有回避这些质疑和批判,事实上,在《诗性正义》中,努斯鲍姆就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部分回答。就部分文学的道德污点以及由此引起的野蛮情感来说,努斯鲍姆显然并不否认,她注意到,许多畅销作品正是“借助粗野的情绪,以及通过唤起可能包含对他人非人化的(dehumanization)幻想来吸引读者”。[28] 但是,努斯鲍姆同时认为,读者的阅读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种在阅读中反思,在自身伦理立场和小说视野不断交叉验证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筛选我们关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直觉”,“极大地改变我们作为读者能够拥有的情感经验”。[29]
对于后一种批判,认为情感有可能引起廉价的同情,而不是全局性的、制度性地看待问题,努斯鲍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种可能:“在有些情形中,如果我们被这样一种价值无限的模糊观念所操纵……‘冷酷’的经济学工具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准确的指引。” 但是,努斯鲍姆同时补充道,这并不是说“计算本身比情感本身更值得信赖”,而是“和当下某种程度的分离——对有些人来说,计算可能有助于形成这种分离——有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筛选我们的信念和直觉,从而使我们得到一种更精确的感受,感受我们情感到底是什么以及在情感中到底什么最值得信赖。” [30] 努斯鲍姆似乎认为,通过更加审慎和明智的情感,剔除那些情绪化的冲动莽撞的情感,情感本身仍然可以比经济学更加值得信赖,仍然更加具有中立裁判者的资质。相比之下,努斯鲍姆对于经济学贫乏的想象力和僵化的数字思维颇为忧虑,认为它们会遮蔽了人们真正的需求和对人们丰富性的关注,尤其会忽略对那些弱者同情的关注。
努斯鲍姆的论辩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自己诗性正义的正当性和可行性,然而,这些论辩在捍卫论点的同时也同样留下了理论上的疑点。既然文学和情感也并不一定是安全的,那么如何区别正确的文学和情感呢?如果说我们还可以通过政治正确和伦理道德来筛选文学,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真正的同情和幼稚的妇人之仁呢?这些问题都等待着进一步的回答,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足够充分的回答,也许诗性正义才能真正显示她的力量,才能真正证明她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正义,一种全面而非短视和偏颇的正义。
五、结语
行文至此,本文的结论或许会让人有些失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和论辩,通过倾听抗辩双方的观点和论述,我们发现,努斯鲍姆对经济学功利主义的批判也许略显单薄。她提出的两个批判论,经济学的行为主义视角导致了“物化”,以及非个性化地对待个人将导致群体分化和群体歧视,也许存在较大错位的可能。因此,要使得诗性正义成为正义和司法规范的有力竞争者,还仍然需要对这种正义标准做出更多的理论上的建构和完善。
这种建构和完善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通过分析已经看到,尽管诗性正义存在种种问题,但她已然显现了她的力量:基于情感的诗性正义能够给我们带来道德上的感召,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同情的姿态去关注那些弱者;而文学性的视角则拓展了我们的经验边界,使得我们能够以更全面和更人性化的态度去对待人和人性。在道德和信息的层面,诗性正义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视角和帮助,促使我们去寻求一种更加值得追求的、更加容易适用的正义标准。[31]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或许可以《诗性正义》中找到更多的启发和灵感,挖掘文学和情感更多的功能,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种建构正义标准的工具。近年以来,如何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促进公共领域的沟通,避免个人私利和派系政治妨碍公共利益的实现,成为了许多学术领域关注的焦点。[32] 然而,除了规范性的论证之外,很多经验性的研究却表明,原本设计用来促进商议民主和派系沟通的方案不仅没有实现方案设计的初衷,反而现实中陷入更为分裂的境地。[33] 这不禁提示我们,努斯鲍姆对文学和情感的分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对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沟通,文学和情感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文学与情感能够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和认同他人的生活,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开放自身。这样一种有力的公共生活的媒介,是否有可能成为真正促进商议民主,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宽容的有力工具呢?
问题的答案仍然需要人们去思考、去回答。然而,问题和思路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方向、一种探索和一种诗性正义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在一个冰冷和思维定势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可以拥有畅想,可以挑战贫乏的想象力,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
* 原文刊载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9年第1期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6页。
[2]《马太福音》第7章12节。
[3] 我在这里强调了“政治社会”这一前提条件,因为只有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中,只有存在共同利益的时候,正义才有实现的可能和意义。换句话说,正义并不存在于自然社会,正义是人为的美德。参见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7-524页。霍布斯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在自然状态下,“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都不存在”,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
[4] 例如,Herbert Wechsler, “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Harvard Law Review 73(1959).
[5] 司法受到个人偏好的影响恰巧是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而司法的背后受到政治的操控则是批判法学的观点,分别参见Joseph C.Hutheson, Jr., “The Judgement Intuitive: The Functional of the ‘Hunch’ in Judicial Decision,”14 Cornell Law Quarterly 174(1929); David Kairys, “Introduction”, in The Politics of Law: a Progressive Critique,3rd ed., David Kairys, New York: Basic Books,1998,pp.1-22
[6] 追求效率最大化是古典功利主义以及一部分法律经济学学者追求的目标,例如哈佛大学的Shavell教授, 参见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而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则强调以财富作为衡量标准,他们认为,效率比财富更难衡量,同时,“财富最大化是一种注重产出和强调社会合作的伦理”,而功利主义“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不注重社会生活的伦理”,理查德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489页。
[7] 例如,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尔斯教授(Tracy Meares)认为,个人理性主义的假设扭曲地假设了个人遵循法律是由于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因此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对个人惩罚的威胁越高时,将越能有效地阻碍社会犯罪。参见Tracey L. Meares, Norms, “Legitimacy and Law Enforcement”, 79 Or. L. Rev. 391 (2000),p.398. 社会心理学家泰勒认为,个人对法律自愿遵循是因为个人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权力机构有权利去执行法律。泰勒将前者看做是基于道德(morality-based)遵循法律,将后者看做是基于合法性(legitimacy-based)遵循法律。并且通过实验进一步表明,基于道德遵循法律比基于权威遵循法律会更有力量。参见Tom R.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pp.57-64。
[8] 例如,德沃金认为,“断言社会财富是社会价值的组成部分是极其荒谬的……由于社会财富自身的原因而赋予法官最大化社会财富的动力是荒谬的”,Ronald R. Dworkin, A Matter of Princi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64.
[9]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21.
[10]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p.26-27
[11]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reface.
[12] 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3] 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4] 早在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商品经济的批判中,就已经对这种物化或理性化表达了深深的忧虑。马克思认为,“生产不仅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15]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39.
[16] 通过“人化”来提高和促进人们的道德能力,这的确是一部分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中国古代许多的诗词就正是通过咏物来抒发情怀和感染读者的,例如梅兰竹菊的经典意象就寄托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高尚气节,也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17] 对于心智的讨论,参见理查德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09页,引文见209页。
[18] 理查德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19] 这两篇文献分别是Robert Frank, Thomas Gilovich, and Dennis Regan,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pring 1993), 以及“How do you Mean, Fair?” Economics Focus column in the Economist, May29, 1993.
[20] 惠特曼:《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1]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92.
[22]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群体区分可能会促进群体内部的反思和改善,因为这种群体区分的舆论必然会使得群体内部有些“好人”被冤枉了,从而促成他改善群体和群体形象。当然,另一种可能是导致群体和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和冲突对立。
[23] 惠特曼:《草叶集》,李野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24]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120.
[25] 理查德德·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414页。
[26] 理查德德·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页,注55。
[27] 例如,2008年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在保护了劳动者利益的同时,也同时对众多寻找工作的失业者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但篇幅主题所限,这里并不从整体上评价新劳动合同法的利弊。
[28]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10.
[29]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76.
[30] Martha C.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p.69.
[31] 例如,近几年来,努斯鲍姆发展起了一种以能力为核心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显然与诗性正义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参见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32] 最典型的例子包括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议民主的理论,分别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John Elster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参见Cass R. Sunstein, “Deliberative Trouble? Why Groups Go to Extremes”, 110 Yale L.J. 71,2000.
来源: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译者代译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