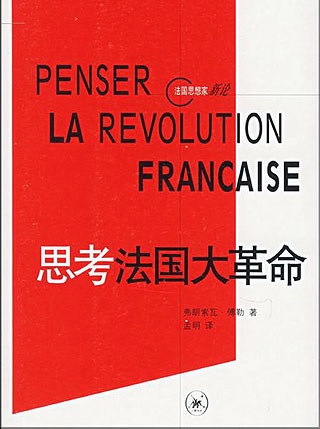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不计其数,被冠以“大革命”之名的唯有两百多年前法兰西大地上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要理解现代性,理解世界为何是现在的样子,法国大革命就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存在。基于自由与平等以及血与火交相辉映的复杂性,不同阵线和派别的论者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意识形态浪潮,将法国大革命原本丰润立体的脸庞冲刷得日趋平面化。有鉴于此,弗朗索瓦•傅勒向法国史学界发出挑战,尝试用一种阐释性的概念史方法取代“关于起源的叙事”的描述性通史。为此,傅勒发掘出被史学界遗忘的奥古斯丁•古参。古参对革命史作的是一种社会学研究,傅勒的概念史与其一拍即合。古参对革命动力的研究,托克维尔对君主制行政集权与民主意识形态亲缘关系的考察,成为傅勒概念史阐释的坐标。
虽然傅勒早年出身文学专业,行文流畅,文笔优美,但阅读《思考法国大革命》并不轻松省力。阐释性的概念史方法轻描述重揭示,摆脱了平庸的实证主义,以至于作为历史学家的傅勒,在某种意义上,更像一位哲学家。与其相类者,大概唯有被称为“莫扎特式”历史学家的列文森。而且傅勒如同一位敬业且技艺超群的刺绣者,经手过的布料上针脚细密,若想探究其艺,观者须细察每一处针脚,不可有所疏漏。
法国事件的方式相对其内容是次要的,革命并非其遗产,民主在行动才是革命史阐释需要面对的,而民主价值本身也无法为革命的正当性提供背书。革命的斯芬克斯之谜终要被猜破,如古参所言,革命的谜底并非雅各宾的心理学,而是民主现象的社会学。如果说出于对革命暴力的厌恶而否定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浅薄的看法,那么以高扬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保留革命手段的动力也是一厢情愿,因为二者共享一个错误的前提。
“革命只是规范了,调整了一桩大事业的效果并使之合法化,并非革命就是这一事业本身。”托克维尔的话使大革命事件摆脱了“革命”这一关键词,真正的“大事业”乃现代民主现象。因此,对革命的肯定或否定并不能为理解大革命事件提供什么帮助,重要的是解释,唯有在解释中,关键词“民主”方才凸显出来。傅勒宣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以此远离“纪念式史学”的意识形态之争,构建自己的概念史论述,进入到真正的问题当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傅勒告别了革命话语,拯救出大革命的遗产。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为我们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枷锁的有无,而在于枷锁的合法与不合法。卢梭不是社会观察家,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他关注的是原则问题,而非事实,一种新的合法性才处于他视野的中心。这种新的合法性即民主的合法性,也就是公民社会被赋予法的地位。然而,新的合法性必须在宪政框架内经由代议制确立起来,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法国大革命诉诸直接民主,藉此无限压缩了法与事实的距离,将权力社会化,权力属于每个人,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透明的。为了保持这种透明,合法性话语成为权力的唯一保障。民主合法性取代神权合法性,从而唯有象征人民的寡头们经由话语实践才具备合法性。“大革命是不讲平等的,它只讲合法性。它整个地立足于一种既多样又独一的民主合法性话语。”故大革命最纯粹的形式终结于热月九日,之后的一切均围绕利益展开,法与事实拉开了距离,政治合法性不再是革命的中心。
托克维尔视大革命为社会文化的整合过程,绝对君主制在加强行政集权,使等级制度徒具形式后寻找不到合法性原则而陷入困境,最终只能经由大革命的剧痛重组政治合法性。绝对君主制与大革命中的民主现象不过是两根磁针,它们都指向同一方向: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随着拿破仑接过路易十四留下的接力棒,新的政治合法性得以建立,大革命便结束了。
据说,路易十六在引颈就戮前曾重复了痛苦之神的话:我尝尽艰辛。革命的血与火同样使法兰西尝尽艰辛,但如今它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一个三色旗飘扬的共和国。然而,有些国家在经历百年的风云激荡,尝尽艰辛之后依旧沉溺于“一个幻想的往事”当中,在历史三峡的漩涡里打转,悲夫!
大革命结束了,革命却是不死的幽灵,静静守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思考法国大革命》,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三联书店2005年1月)
(四季书评2018-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