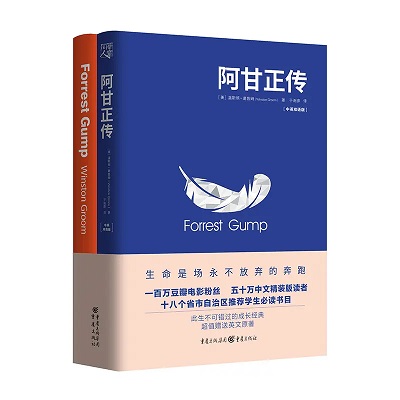第十九章
蒙夕的比赛预定结果是这样的:我要被屎蛋痛宰。
这是麦克在赴蒙夕途中告诉我的。原因好像是屎蛋是我的前辈,所以应该赢,而由于这是我的第一场出赛,所以我必须输。麦克说他只是想把话说在前头,免得伤感情。
荒唐,珍妮说,居然有人自称-屎蛋。
他大概就是个屎蛋。丹恩说,想逗她开心。
你只要记住,阿甘,麦克说,这码事根本是表演。你可不能发火。任何人不可受伤-屎蛋-一定要赢。
唔,我们终于到了蒙夕,摔交比赛是在当地一座大体育馆举行。当时已经在进行一场比赛——蔬菜跟一个自称野兽的家伙较量。
野兽浑身是毛,就像只猿猴,眼睛戴着黑眼罩,他一出场就夺下蔬菜戴的挖空西瓜,踢到后排看台上。接着,他抓住蔬菜的头,把他撞到擂台柱子上。然后他咬蔬菜的手。我正替蔬菜难过,但是,他也有几招绝活——也就是,他把手伸进他穿的绿叶吊带内,掏出一把什么鬼东西,揉在野兽的眼睛上。
野兽闷吼,满场踉跪,一面揉眼睛想把那玩意弄掉,蔬菜从他后面欺至,踢他的屁股,接着他把野兽扔到绳圈上,把他卷任使他无法动弹,然后狠揍野兽。观众嘘声四起,向蔬菜投纸杯,蔬菜冲观众伸中指。我正在好奇这场比赛会如何了结,但这时麦克过来叫丹恩和我进更衣室换戏服,因为下一场就是我跟屎蛋比赛。
我换上尿片和园锥帽之后,有人敲门,问:笨瓜-在不在?丹恩说:在。那家伙说:你要上场了,出来吧。我们就出场了。
丹恩推着轮车跟在我后头走上甬道时,屎蛋已经在擂台上。他在场上跑来跑去跟观众扮鬼脸,呃,他穿着那件紧身衣着起来可真像个屎蛋。总之,我爬上擂台,裁判把我们叫到一起,说:好,两位,我要求比赛精采、干净——不准挖眼睛,或攻击腰带以下的部位,或是咬人、抓人之类的鸟动作。我点头说:嗯。屎蛋就狠瞪我。
铃响了,我和屎蛋绕着彼此打转,他伸脚绊我但是没绊倒,我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摔到绳圈上。这时我才发现他身上抹了一种滑滑的鬼东西,让人抓不住他。我想抱住他的腰,但是他像条鳗鱼似的从我手中溜走。我抓住他的胳膊,但是他也抽脱,还咧嘴笑我。
接着他埋头冲撞我的肚子,但是我让开一步,屎蛋飞过绳子,落在前排看台上。观众嘘他,鸡猫子喊叫,但是,他拿着一把折叠椅爬回擂台上。他拿着椅子追我,我没有防御工具,拔腿就跑。但是屎蛋用椅于砸我的背,朋友,那可真痛。我试图夺下椅子,但是,他拿它敲我的头,我困在角落无处可躲。接着他踢我的小腿,我弯腰抱住小腿,他又踢我另一只小腿。
丹恩坐在擂台旁边的突角上,对裁判大叫要屎蛋放下椅子,但是没有用。屎蛋用椅于砸了我四、五下,把我打倒在地上,然后压在我身上抓住我的头发拿我的头撞地板。接着他抓住我的胳膊撇我的手指。我望向丹恩,说:这是搞什么鬼?丹恩想进入场中,但是麦克站起来抓着丹恩的领子把他拖回去。接着突然铃声响了,我得以回到我的角落。
听着我说,这杂种用椅子砸我的头,想弄死我。我必须做什么动作反击。
你要做的是翰掉比赛,麦克说。他并不想弄伤你——他只是想演得精采些。
我可不觉得精采。我说。
只要在场上再待几分钟,然后让他把你压倒,麦克说,记住,你要赚这五百块就得输掉比赛——不是赢。
他要是再用椅子打我,我就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了。我说。我望向观众席,珍妮坐在那儿神色难过又难为情。我渐渐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
总之,铃声又响,我上场。屎蛋想抓住我的头发,但是,我把他抛开,他像棍子似的转到绳圈内。接着我勾住他的腰把他抬起来,但是他从我手中滑脱,一屁股摔在地上,连声呻吟抱怨,揉着屁股,接着我只知道,他的经理居然塞给他一支橡胶头通马桶器,他就用那玩意敲我的头。唔,我夺下它,用膝盖将它掰成两截,起身追他,但是,我看见麦克在那儿猛摇头,因此任屎蛋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扭到我背后反锁。
那狗娘养的差点扭断我的胳膊。接着他把我按到帆布地板上,用肘敲我的后脑。我可以看见麦克在那儿点头微笑赞许。屎蛋从我背上下来,伸脚踹我的肋腔和小腹,接着他又拿起椅子敲我的头八、九下,最后用膝盖顶住我的背,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就那么趴着,他坐在我的头上,裁判数到三,比赛应该就此结束。屎蛋起身朝我的脸吐口水。场面难堪极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由自主哭了起来。
屎蛋绕着擂台高视阔步,丹恩上台推着轮车到我跟前,用毛巾揩我的脸,接着我只知道珍妮也跑上台,抱着我哭着,观众呐喊吆喝,还扔东西到擂台上。
走,咱们离开这儿。丹恩说。我站起身,屎蛋跟我吐舌头做鬼脸。
你的绰号取得真贴切,我们离开擂台时珍妮对屎蛋说,真可耻。
她这话大可连我也算上。我这辈子从没有感到这么羞辱过。
返回印第安那波里的一路上气氛尴尬。丹恩和珍妮没说几句话,我在后座全身酸疼。
你今晚的表演真精采,阿甘,麦克说,尤其是最后哭起来——观众爱死了!
那不是表演。丹恩说。
哦,得了,麦克说。听我说——总得有人输嘛。这么着——下一次我让阿甘赢。你觉得如何?
应该没有下一次了。珍妮说。
他今晚赚了大钱,不是吗?麦克说。
让人狠打一顿才拿五百块,不算大钱。珍妮说。
呃,这是他的第一场比赛。这样吧——下一场我给他加到六百块。
一千二如何?丹恩问。
九百,麦克说。
让他穿游泳衣,别穿尿片纸帽如何?珍妮说。
观众喜爱这身打扮,麦克说。这是他的卖相啊!
你去打扮成那样看看?丹恩说。
我又不是白痴。麦克说。
你给我闭上鸟嘴!丹恩说。
唔,麦克言而有信。第二场比赛对手叫人蝇。他戴了个像苍蝇似的小啄,面具上装着两个突出的大眼睛。我可以在台上把他扔来扔去,最后坐在他头上,领到我的九百块。而且,观众还疯狂呐喊:我们要-笨瓜-!我们要-笨瓜-!这笔交易倒不赖。
接下来,我跟神仙比赛,他们甚至让我用仙杖敲他的头。之后,我交手过许多家伙,丹恩和我勉强存了五千块可以做养虾生意了。但是,同时,我渐渐相当受到观众欢迎。女人会写信给我,甚至还有人卖圆锥纸帽当纪念品。有时我上场,观众中会有近百人戴纸帽,鼓掌欢呼我的绰号,令我觉得陶醉的,你知道吧?
在这同时,珍妮和我感情融洽——除了摔狡这件事之外。每天晚上她回到公寓之后,我们自己弄晚饭,然后三人坐在客厅计划如何着手养虾生意。我们打算去贝特河,巴布的家乡,在墨西哥湾附近找块沼泽地。我们得买些大铁丝网和小网子,还有一条小船和虾饲料。丹恩说,在等候第一批收获期间我们得有地方住,还得买些日用杂货,此外还要有门路把虾子卖到市场上。总而言之,他估计要五千块左右才负担得了头一年的花费——之后,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如今有问题的是珍妮。她说我们已经存到五千块,何不收拾行李南下?唔,她这话有它的道理,但是老实说,我还不想走。
是这样的,打从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以来,我从没觉得有过什么真正的成就。或许在中国大陆打乒乓球那段时间有一点这种感觉,但是那只维持了几个星期。可是现在,你知道,每个星期六晚上,我都会听到人们的欢呼喝采声。而且他们是对我喝采——不管我是不是白痴。
你应该听听我痛宰大头磨子的时候观众的欢呼声,那家伙七场时全身粘着百元大钞。还有阿马利洛恐怖艾尔,我给了他一记原地抱摔,结果赢得了东区冠军锦带。之后,我还跟巨人朱诺比赛,他有四百磅重,披了一块豹皮,拿着一根硬纸棍。
但是有-天,珍妮下班回家,说:阿甘,我俩俩得好好谈谈。
我们出门到一条小溪附近散步,珍妮找了个地方坐下,然后说:阿甘,我觉得摔咬这码事已经过头了。
怎么说?我问,其实我多少心里明白。
我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万块了,几乎是丹恩所说养虾需要费用的两倍。我奇怪你为什么还是每个星期六都要上台拿自己耍宝。
我没有拿自己耍宝,我说,我得考虑我的观众迷。我现在是很出名的人,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狗屎,珍妮说,什么是-观众迷-?什么叫-出名-?那些人只是一堆混球,花钱看这种屁玩意。一堆成年人穿着吊带裤上台,假装要伤害对方。谁听说过有人自称-蔬菜、-屎蛋-什么什么的——还有你,自称是-笨瓜-!
那有什么不好?我问。
呃,那你认为这种事给我什么感受?我爱上的男人是个众所周知的-笨瓜-,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次洋相——而且还上电视!
上电视可以赚到外快。我说。
去它的什么外快,珍妮说,我们不需要外快!
谁听说过有人不需要外快的?我说。
我们不是那么迫切需要它,珍妮说,我的意思是,我只想找个安静的小地方位下,你可以找份正经工作,例如养虾——我们或许可以买栋小屋子,有个小花园,养条狗什么的——或许甚至生孩子。当年跟裂蛋表演我已经出过名,但却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并不快乐。如今我快三十五了,我想安定下来……
呃,我说,我觉得好像应该由我来决定我干不干这一行。我不会干一辈子——时候到了我会退出。
唔,我也不会等一辈子。珍妮说。但是我不认为她是当真的。
第二十章
那件事之后我又比赛了两场,当然,两场都赢了,过后有一天,麦克把丹恩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听着,这个星期你要跟-教授-交手。
那是何许人?丹恩问。
他来自加州,麦克说,在当地非常抢手。他正要争夺西区冠军。
我无异议。我说。
不过有件事,麦克说。这一次,阿甘,你得输掉。
输?我说。
输,麦克说。听我说,你已经一连赢了几个月。得偶尔输一场来刺激你的知名度,你明白吗?
为什么?
简单。观众喜欢倒楣蛋。这样下一场你才会赢得风风光光。
我不喜欢。
你打算付多少?丹恩问。
两千。
我不喜欢。我又说。
两干块是笔大钱。丹恩说。
我还是不喜欢。我说。
但是我接受了这笔交易。
珍妮近来举止怪异,但是,我把它归根为神经质什么的。有天,她回到家,说:阿甘,我忍耐到极限了。请不安再去摔跤了。
我不得不去,我说。反正,这次我得输。
输?她说。我把麦克说的话照样解释给她听,她说,
噢,妈的,阿甘,这太过分了。
命是我的。我说-一管它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两天,丹恩从外面回来,说要跟我谈谈。
阿甘,我大概有法子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我问什么法子。
我在想,丹恩说,我们还是尽早退出这一行的好,珍妮不喜欢,而且,咱们要想做养虾生意,也该着手进行了。不过,他说,我想我有法子既可以退出,又可以赚上一大笔。
怎么说?我问。
我跟镇上一个家伙聊天。他经营赌场,他说风声已经传开了,这个星期六你会输给-教授。
然后呢?我说。
然后,要是你赢了呢?
赢?
痛宰他。
我会跟麦克结怨。我说。
去他的麦克,丹恩说。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要早咱们拿存下的一万块去赌你会赢呢?赌率是二比一呐。你痛宰他,咱们就有两万块了。
可是,我会惹上一身的麻烦。我说。
咱们拿了两万块离开此地,丹恩说,你知道有了两万块咱们可以怎么用法吗?咱们可以大做养虾生意,还可以剩下一大笔钱。反正我已经在考虑退出摔跤这玩意。
唔,我心想丹恩是经纪入,而珍妮也说过我得退出这一行,况且两万块的确是不赖的生意。
你认为呢?丹恩说。
好,我说,好。
跟教授交手的日子到了。比赛要在韦恩堡举行,麦克来接我们,这会儿在屋外猛按喇叭,我问珍妮准备好了没有。
我不去,她说。我看电视转播。
可是你一定要去啊。我说,然后要丹恩解释原因。
丹恩把我们的计划告诉珍妮,说她非去不可,因为我痛宰教授之后需要有人开车送我们回印第安那波里。
我们两个都不会开车,他说,所以,比赛结束之后得有辆跑车在体育馆外面接我们回到这儿,拿了那两万块然后走人。
唔,我不沾这种事。珍妮说。
可是有两万块啊。我说。
但也是诈财。她说。
呃,他这些日子做的事才是诈财,丹恩说,输赢都是事先计划好的。
我不干,珍妮说。
麦克又在按喇叭,于是丹恩说:呢,咱们得走了。比赛结束之后再见了——无论输赢。
你们该感到羞惭。珍妮说。
等我们揣着两万块钞票回来,你就不会这么生气了,丹恩说。
总之,我们就出发了。
赴韦恩堡途中我没怎么说话,因为,要那样对付麦克我觉得有点儿难为情。他待我并不太坏,不过,话说回来,就像丹恩说的,我也替他赚了不少钱.所以应该会扯平。
我们抵达体育馆,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巨人朱诺被神仙痛宰。接下来是女侏儒捉人大赛。我们进入更衣室,我换上尿片和纸帽。丹恩找人打电话到计程车公司,安排一辆车子在外面等我们。
有人敲门,上场的时候到了。我和教授是今晚的主角。
我出场时他已经在擂台上。教授是个精瘦的矮个子,蓄胡子、戴眼镜、穿黑袍,还戴着方帽。他这身打扮可真像个教授。我当下决定要让他吃下那顶方帽。
唔,我爬上擂台,司仪说;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这话引来一阵嘘声,他接着说:今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北美职业摔跤协会国内最优秀的两名选手——-教授-对抗-笨瓜-!
这时响起一片嘘声和喝采声,教我弄不清观众是高兴还是生气。不过反正无所谓,因为铃声响起,比赛开始了。
教授已经脱下袍子、眼镜和方帽,绕着我转,一面对我晃着指头,仿佛在责骂我。我想抓住他,但每次他都闪开,继续晃指头。双方就这样持续了一、两分钟,他才犯了个错。他跑到我背后想踢我屁股,但是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甩到绳圈上。他像颗小弹珠似的从绳圈弹回来,我顺势绊他一跤,正想用腹压的招术跳到他身上,他却一骨碌翻回他的角落,等我抬头一看,他手里拿了一把大戒尺。
他拿着戒尺呼呼拍手心,好似要用它揍我屁股,但等我再抓住他时,他竟然用戒尺戳我的眼睛,想把它挖出来。我跟你说,朋友——那可真痛。我跟跑转圈子,努力恢复视力,他却从背后冲过来,放了些东西在我的尿片里面。不消多久我就明白那是什么东西——蚂蚁!天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但是蚂蚁开始咬我,我难受极了。
丹恩在那儿叫我解决他,但是有蚂蚁在裤子里要解决他谈何容易。总之,铃声响了,第一回合结束,我回到角落,丹恩努力把蚂蚁弄掉。
他这招真龌龊。我说。
放手解决他,丹恩说,咱们担不起失败。
教授出场做第二回合比赛。他对我做鬼脸,接着他挨得很近我得以抓住他举起来作螺旋桨转圈。
我把他转了大概四、五十圈,直到我相信他铁定晕了,才用全身力气把他扔到观众席上。他落在看台大约第五排,一位正在织毛衣的老太大身上,她拿起雨伞就打他。
问题是,螺旋桨这一招也让我付出了代价。眼前的东西净在打转,但我心想没关系,因为昏眩一会儿就会过去,反正教授已经被解决了。但这一点,我料错了。
我刚要从昏眩中恢复平衡,突然间有东西绊位我的足踝。我往下一看,该死的,居然是教授回到了擂台上,而且,拿了那位老太太正在织的——球毛线,这会儿把我的脚绑住了。
我奋力想挣脱,但是教授拿着线球绕着我转,把我缠成了一具木乃伊。没多久,我手脚被缚,无法动弹。教授停下来,把毛线系了个漂亮的结,然后站在我面前,鞠个躬——就好像他是个魔术师,刚变了一招把戏似的。
接着他阔步走到他的角落,取了一本厚厚的大部头书本好像是字典——然后走回来又鞠躬。接着他拿书敲我的头。我束手无策。他起码敲了我十几下我才倒下。我无奈无助,只听到观众的喝采声,任凭教授坐在我肩上压住我——赢得了比赛。
麦克和丹恩进入场中,解开毛线,把我扶起来。
太棒了!麦克说,真是太棒了!我都没办法设计得这么妙!
哦,闭嘴,丹恩说。然后他转向我。呃,他说,这可真妙——你让-教授-用机智给打败了。
我一声不响。我难过极了。这下子一切都输光了,但只有一件事我确定不疑,就是我再也不摔跤了。
比赛结束,我们不需要逃亡用的计程车了,所以丹恩和我搭麦克的汽车回印第安那波里。一路上麦克不停的说我这么输给教授实在太棒了,下一场一定会让我赢,而且让大家赚上几千块。
车停在公寓外面,麦克回头递给丹恩一个信封,里面是我这场比赛的两千块酬劳。
别拿。我说。
什么?麦克说。
听我说,我说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
丹恩插口:他要说的是,他再不摔跤了。
你说笑?麦克说。
不是说笑,丹恩说。
呃,为什么?麦克问。有什么问题,阿甘?
我来不及回答,丹恩就说:他现在不想谈。
唔,麦克说,我大概了解。你们进去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就来,咱们好好谈谈,好不?
好。丹恩说完,我们下车。等麦克走了之后,我说:你不该拿这笔钱的。
呃,咱们现在只剩这些了。他说。别的全没了。几分钟之后我才明白他的话是多么正确。
进了公寓,噢,天,珍妮也走了。她的东西都不见了,只留给我们几块干净床单和毛巾和锅什么的。客厅茶几上留了一张字条。是丹恩先发现的,他念给我听。
亲爱的阿甘:
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曾试图跟你谈谈我的感受,而你似乎并不在意。你今晚要做的事尤其不好,因为它是不诚实,我恐怕无法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或许我也有错,因为,我已经到了需要安定下来的年纪。我想有个家,有栋屋予,上教堂之类的事。我从一年级就认识你了,阿甘——将近三十年了——看着你长得又高又壮又善良。等我终于明白自己多么喜欢你时——你来波士顿的时候——我是世上最快乐的女孩。
过后,你吸大麻,还跟那些女孩胡搞,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想念你,示威活动期间你到华盛顿来看我,我好开心。
但是,等你被送上太空,又在丛林中失踪四年,我想我变了。我不像以前那么满怀幢憬,只想找个地方过单纯的日子就满足了。所以,现在我必须去找它。
你也变了,亲爱的阿甘。我不认为你真能阻止这种改变,因为你始终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是,我俩的想法不再契合。
我含泪写这封信,但是我俩必须分手了。请不要找我。祝福你,我亲爱的——再见。
爱你的,珍妮
丹恩把信递给我,但是我任它落在地板上,自己就那么呆站在那儿,毕生头一回恍觉当白痴的真正滋味。
第二十一章
呃,我就这样成了一个可怜的混球。
丹恩和我那天晚上住在公寓,但第二天一早就收拾行李,因为没有理由再留在印第安那波里了。丹恩过来对我说:呐,阿甘,把这钱拿去。他把麦克给的两干块摔跤酬劳递给我。
我不要。我说。
唔,你还是拿去得好,丹恩说,因为咱们只剩这些了。
你留着。我说。
起码拿一半,他说。听我说,你得有路费,才能去你要去的地方。
你不跟我去?我问。
恐怕不了,阿甘,他说。我闯的祸够大了。昨晚我一夜没睡。我想到是我要你答应拿我们的全部财产去孤注一掷,而且珍妮明明就快受不了我们了,我还要你继续摔跤,你被-教授-打败并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而为。该怪我。我实在不是好人。
噢,丹恩,这也不是你的错,我说。要是我没有被什么-笨瓜-头衔冲昏了头,自以为了不起,相信他们说我的那些屁话,我根本不会惹出这些事。
无论如何,丹恩说,我不觉得应该再跟着你。你现在有别的事要做。去做吧。忘了我。我不是好人。
晤,我跟丹恩谈了许久,但是,怎么说也劝不住他,过后他拿了他的东西,我抱他下楼,望着他坐在小轮车上,衣物堆在腿上,自己滚着车轮上了大街。
我到车站买了去木比耳的车票。旅程预定是两天两夜,经过路易斯维尔、纳许维尔、伯明翰,然后到木比耳。我这个凄惨的白痴就这么一路呆坐在车上。
我是夜间经过路易斯维尔的,第二天在纳许维尔换巴士。换车要等三个小时,于是我决定到镇上逛逛。我在一个午餐摊子买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冰茶,沿街走着,突然看见一家饭店前面有个大招牌,写着:欢迎光临大师西洋棋邀请赛。
这招牌勾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在丛林期间曾跟大山姆下过几年棋,所以我就走进饭店。他们是在舞厅内举行棋赛,有一大群人围观,但是旁边有块牌子写:入场费五元。我不愿花一毛钱,所以我就隔着门往里看了一阵子,然后独个儿到大厅坐坐。
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个小老头。他满脸皱纹,看起来性情乖戾,穿了件黑西装,打领结,而且他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副棋盘。
我坐在那儿看,他每隔一会儿就会移动一枚棋子,我渐渐明白他是在跟自个儿下棋。我估计还有一个多小时巴士才会离城,所以就问他要不要人跟他下棋。他只看看我,然后低头继续看棋盘,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半天,老头子已研究棋盘将近半小时,这会儿他把自主教移到黑侍卫七,正要放开手,我说;失礼。
老家伙好像坐到大头钉似的跳了一下,隔着茶几瞪着我。
你要是走这一步,我说,就会空门大开,先损失你的骑士,然后就是你的皇后,你就走投无路了。
他低头看棋盘,手始终未放开主教,然后他把棋子移回原位,对我说:也许你说得对。
唔,他继续研究棋盘,我估计该回车站了,但是正要离开时,老头说:失礼,不过,你刚才那番评论非常敏锐。
我点个头,他又说:这样,显然你下过棋,何不坐下来跟我下完这一盘?你用白棋。
我没办法下棋,我说,因为我得赶搭巴士等等。于是,他点个头,用手跟我微微敬个礼,我就走回车站。
等我到了幸站,巴士居然已经开走了,要到明天才有下一班车。我什么事也做不好。唔,这下子得打发一天的时间,所以我又走回饭店,那个小老头还在跟自个下棋,而且似乎快赢了。我走过去,他抬头看看,示意我坐下。我接下的棋局情况很不妙——小卒半数已经阵亡,城堡也没了,只剩一个主教,而且我的皇后就要被吃掉了。
我花了将近一小时才扳回劣势,而每次劣势稍有改善,小老头就咕哝摇头。最后,我牺牲一子诱他人毂,他中计了。又下了三手,我将死他。
该死,他说,你究竟是谁?我告诉他名字,他说:不,我是说,你在哪儿下过棋?我甚至不认识你。
我说我是在新几内亚学会下棋,他说:老天!你是说,你从未参加过区域比赛?
我摇头,他就说:唔,不管你知不知道,我可是前任国际大师,你刚才那局棋根本不可能赢,结果你却消灭了我!
我问他怎么没在里面跟其他人比赛,他说:哦,我以前参加。我将近八十岁了,如今是年轻人的天下。现在的光荣属于年轻人——他们的脑子比较敏锐。
我点个头,谢谢他跟我下棋,然后起身要走,但是他说:呃,你吃过晚饭了吗?
我告诉他几个小时之前我吃过三明治,他就说:唔,让我请你吃顿晚饭如何?不管怎么说,你让我领教了一盘精采的棋赛。
我说好,我们就走进饭店餐厅。他是个好人。名叫崔伯先生。
听我说,吃晚饭当中,崔伯先生说,我得再跟你多下几盘才能确定,但是,除非你刚才赢棋纯属侥幸,否则,你可能是未被发掘的最聪明的天才棋士之一。我想资助你参加一、两项比赛,看看结果如何。
我告诉他,我打算返乡做养虾生意等等,但是他说:唔,这可能是你毕生难得的机会,阿甘。你可以凭棋赛赚大钱呐,你知道。他要我今晚考虑考虑,明早告诉他结果。于是我和崔伯先生握手道别,我回到街上。
我闲逛了好一阵子,但是纳许维尔没啥可看的,最后我坐在公园里的长板凳上。我一直在努力思考现在要怎么做才对,但是对我而言思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的多半是珍妮和她现在在哪儿。她要我别找她,但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她并没有忘记我。我在印第安那波里让自己出了大洋相,我知道。我觉得那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努力做对的事。如今,我已不确定什么是对的事了。我是说,如今我身上没有几文钱,得弄些钱才能着养虾生意,而崔伯先生说我去参加巡回棋赛可以赚大钱。但是好像每次我不回家做养虾生意,反而跑去做别的事,我就会身陷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又不知何去何从了。
我没有思索多久,一名警察就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
我说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他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夜间坐在公园里想事情,要我离开。我走到街上,那个警察一直跟着我。我不知道要去哪儿,走了一阵子见到一条巷子,我就走进去找了个地方坐下歇脚。我坐了还不到一分钟,那个警察经过又见到我。
好了,他说,出来。我走到街上,他说,你在巷子里做什么?
我说:没什么,他就说:我想也是——你在街头游荡,被捕了。
呃,他把我带回去关进牢房,第二天早上他们说我可以打一通电话。当然,除了崔伯先生我没有旁人可找,于是我就打电话找他。大约过了半小时,他来到警察局把我保出来。
之后,他在饭店请我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又说:听我说,你何不让我替你报名参加下星期在洛杉矾举行的区际锦标赛?冠军奖金是一万块。我负责你的一切花费,奖金平分。我看你是需要一笔奖金什么的,而且,老实告诉你,我也会很开心。我当你的教练兼顾问。如何?
我还是有些疑虑,但是,我心想试试无妨。所以,我就说愿意试一阵子,等我存够了养虾生意的钱就退出。我和崔伯先生握手,我们成了合伙人。
洛杉矶真是五光十色。我们提早一星期抵达,白天大部分时间崔伯先生在磨炼我的棋艺,但是,过了一阵子他摇头说没必要教我,因为我已经精通每一步棋。所以,我们就进城观光。
崔伯先生带我去迪斯尼乐园,玩了些游乐项目,然后安排参观影城。影城里同时在招各种影片,到处有人跑来跑去,喊什么第一次,或是卡、拍之类的屁话。他们在拍的影片当中有一部是西部片,我们看见一个家伙被扔过一块玻璃窗大概十次——他才演好。
总之,我们站在一边看他们拍这场戏的时候,有个家伙上前问失礼,请问你们可是演员?
我说:啊?崔伯先生就说:不,我们是棋士。
那家伙说:唔,真可惜,因为这位大块头,看起来正适合我的影片里的一个角色。说着他转身捏捏我的胳膊,说:哇哇,你可真是个壮汉——你肯定你不会演戏?
我演过一次。我说。
真的!那家伙说,什么戏?-
李尔王。
太好了,小兄弟,他说,太好了,你有没有-傻个-卡?
什么卡?
电影演员工会卡——哦,无所谓,他说,这样吧,小伙子,那玩意弄得到,没问题-我要知道的是,你都躲到哪儿去了?我是说,瞧瞧你这模样!标准的沉默壮汉典型——另一个约翰-韦恩。
他不是约翰-韦恩,崔伯先生怏怏仰乐说,他是世界级棋士。
唔,那更好,那家伙说,一个聪明的沉默壮汉典型。非常罕见。
没有外表那么聪明,我想老实说,但是,那家伙说这些都无所谓,因为演员不必一定要聪明或诚实或什么的——只要能上镜头说台词。
我叫费德,他说,我拍电影,我要你来试镜。
他明天要参加棋赛,崔伯先生说。没时间演戏或是试镜。
唔,总可以挪出一点时间吧?不管怎么说,这可能正是你一直在找的出头机会。你何不也一起来,崔伯,我们也让你试镜。
我们会尽量试试看,崔伯先生说,走吧,阿甘,咱们还有点儿工作要做。
改天见,小伙子,费德先生说。可别忘哆。
于是,我们就走了。
第二十二章
第二天早上,棋赛就要在贝弗利山饭店举行。我和崔伯先生提早抵达,他替我报名参加一整天的比赛。
基本上,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花了大约七分钟就解决了第一个家伙,他是个区域大师,也是某所大学的教授,这一点使我暗自高兴。我毕竟打败了一个教授。
接下来是个十七岁左右的男孩,我大概不到半小时就解决了他。他大发脾气,又哭又闹,他妈妈不得不把他施走。
第-天和第二天我跟各种对手下棋,但是,都很快就打败了他们,这倒令人松口气,因为,我跟大山姆下棋时都得坐在那儿不能上厕所什么的,因为,我一起身他就会挪动棋子作弊。
总之,等我比到决赛时,中间有-天的休息时间。我跟崔伯先生回到饭店,发现拍电影的费德先生的留言。字条上写:今天下午请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安排明早试镜。上面还留了电话号码。
唔,阿甘,崔伯先生说,这件事我不敢说。你认为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过,坦白讲,这码事听起来挺刺激,拍电影上银幕什么的。也许我还会认识玛丽莲-梦露之类的大明星呐。
哦,我想应该无妨,崔伯先生说,我想可以打个电话约个时间。于是他打电话到费德先生那儿,确定我们去的时间和地点,然后突然他捂住话筒问我:阿甘,你会不会游泳?我说:会。他就对话筒说:他会。
他挂上电话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知道我会不会游泳,崔伯先生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猜想等我们到了那儿就会知道了。
我们去的那个片厂跟上次那个不一样,门口的警卫带我们去试镜的地方。费德先生正在那儿跟-个长得酷似玛丽莲-梦露的女士争执,但是一见到我,他立刻堆满笑容。
啊,阿甘,他说,你来啦,太好了。你这就走进那扇门到-化妆及服装部门-,他们给你准备好之后就会要你出来。
于是我走进那扇门,里面有两位女士,其中之一对我说:好,脱下衣服。我又紧张了,但是我照做。等我脱完衣服,另一位女士递给我一件滑稽的橡胶衣服,上面布满了鳞片什么的,还有有蹼的手脚。她叫我穿上它。我们三个合力花了将近一小时才勉强替我穿上。接着她们指点我化妆部的方向,到了那儿,他们叫我坐在一张椅子上,一个小姐和一个先生把一张巨大的橡胶面具套在我头上,与服装接在一起,然后把接缝涂满。弄完了,他们叫我回到片场上。
蹼足使我几乎走不动路,蹼手让我难以开门,但是最后我办到了。我发现自己在户外,有一个大湖,还有香蕉树之类的热带植物。费德先生见到我,往后一跳,说:太好了,小伙子!你是这角色的绝佳人选!
什么角色?我问。
他就说:哦,我没告诉你吗?我在重拍-黑湖来的怪物。连我这样的白痴也猜得到他想要我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费德先生示意方才跟他争执的那位女士过来。阿甘,他说,介绍你认识玛丽莲-梦露。
呃,当时拿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打昏!真是她!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低胸礼服什么的。幸会。我隔着面具说。但是玛丽莲-梦露转向费德先生,气得像只黄蜂。
他说什么?是在说我的xx子,是不是!
不,宝贝,不是,费德先生说,他只是说很高兴认识你。你听不清楚,因为他戴了面具。
总之,费德先生说剧情是这样的:玛丽莲-梦露会在水里挣扎,然后昏倒,接着我要从她身体下面出现,抱她走出水面。可是,等她苏醒过来,抬眼一看见我,立刻吓得尖叫:放下我!救命!强暴!等等的屁话。
但是,费德先生说,我不要放下她,因为当时有坏人在追我们:我要把她抱进丛林。
呃,我们就试拍这场戏。第一次拍完,我觉得挺不错,而且真正抱着玛丽莲-梦露在怀里实在教人兴奋,即使她不停的叫:放下我!救命!警察!
但是费德先生说不够好,要我们再来一遍。这-遍也不够好,结果这场戏拍了大概有十五遍。中间休息时,玛丽莲-梦露总是在挑剔、抱怨、咒骂费德先生,但是他不停的说什么:好极了,宝贝,好极了!之类的屁话。
不过,我自己也渐渐出了个大问题。由于穿着这身怪物服装已将近五个小时,而衣服上又没有拉链或什么可以让人拉开尿尿,我胀得快炸了。可是我不愿提这件事,因为这可是真正的电影,我不想惹怒任何人。
可是我总得想法子解决,于是我决定下次入水时,我就尿在衣服里面,尿会从我的裤腿或什么的流入湖中。呃,费德先生一会儿喊:拍!我就进水里尿尿。玛丽莲-梦露一阵挥舞挣扎,然后昏倒,我潜入水中抓住她,把她抱上岸。
她醒来就动手打我,嚷嚷:救命!杀人!放下我!等等,但接着她突然停止呼喊,说:那是什么气味?
费德先生喊:卡!然后他起身说:你刚才说什么,宝贝?剧本里没有那句话。
玛丽莲-梦露就说:去它的剧本:这儿有什么东西好臭!接着她突然看着我说:喂,你——管你是谁——你是不是尿尿了?
我好难为情,不知所措。我呆站着,抱着她,然后我摇头,说,呃,没有。
那是我毕生头一句谎话。
哼,总有人尿了,她说,因为我一闻就知道是尿!而不是我尿的!所以一定是你!你竟敢尿在我身上,你这个大蠢蛋!接着她开始用拳头打我,还喊叫;放我下来,滚开!等等,但是我以为这场戏又开始拍了,于是我抱起她往丛林走。
费德先生喊,拍!摄影机又开始转动,玛丽莲-梦露又打又抓又喊,从没有那么激烈过。这就对了,宝贝——太好了!继续!我看见崔伯先生也坐在场边一张椅子上,好橡在摇头,别开目光。
唔,进入丛林走了一小段路之后,我停下来回头看看是不是费德先生应该喊卡!的地点,但是他像个疯子似的跳跳蹦蹦,打手势继续拍,还喊着:太好了,宝贝!正是我要的!把她抱进丛林里!
玛丽莲-梦露仍在抓我打我,尖叫:滚开,你这恶心的畜生!之类的话,但是我照吩咐继续走。
突然间,她嘶喊:我的天!我的衣服!
在这之前,我一直没留意,但这会儿我低头一看,该死的,她的衣服方才被什么东西勾住,整个给扯掉了!玛丽莲-梦露一丝不挂在我怀里!
我停下脚步,说:噢喔!转身把她抱回去,但是她尖叫:不,不!你这白痴!我不能这样回去!
我问她要我怎么做,她说得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她想清楚再说。于是我一直往丛林深处走,突然间,不知从哪儿出现一个大东西穿过树梢,吊在蔓藤上向我们荡过来。那东西荡过我们,我看得出是一只猿猴,接着他又荡回来,落到我们跟前。我差点昏死过去。他居然是公苏!
玛丽莲.梦露又开始呼天抢地,公苏抱着我的腿紧紧搂着我。我不知道我穿着这身怪兽装他是怎么认出我的,我猜大概是他闻出我的气味还是什么。总之,玛丽莲-梦露终于说:你认识这只该死的狒狒?
他不是狒狒我说,他是只纯正的猿猴,名叫公苏。
她神色有点滑稽地看着我,说,既然他是只公的,为什么叫苏?
这事说来话长。我说,
总之;玛丽莲-梦露一直挤命用手遮住身体,但是公苏知道怎么办。他从香蕉树上扯了两片大叶子交给她,她把自己遮起一部分。
我后来才晓得,原来我们已超过了我们的丛林外景地,跑到另一个正在拍泰山电影的片场上,公苏是去当临时演员的。我在新几内亚获救之后不久,白人猎人出现,捉走了公苏,把他卖给洛杉矾的一个驯兽师。打那以后他们就一直用他拍电影。
总之,目前无暇闲聊,因为玛丽莲-梦露又在挑剔骂人,说:你得带我去找些衣服穿!唔,我不知道在丛林里哪儿找得到衣服,即使是片场,于是我们就继续走,希望能遇上什么。
果然遇上了。突然间我们来到一片篱笆前,我猜想篱笆里面应该有地方可以弄到衣服给她穿。公苏在篱笆中间找到一块松脱的木板,他取下木板让我们钻过去,但是我一跨到另一边,脚下是空的,我和玛丽莲-梦露滚下一个山坡。我们一路滚到山脚,我回头一看,要命!我们居然滚到一条大马路边上!
哦,我的天!玛丽莲-梦露大叫,我们在圣塔蒙尼卡公路上!
我抬头看,公苏跳跳蹦蹦滑下山坡。我们三个就那么站在路边上,玛丽莲-梦露上下移动香蕉时,极力想遮住身体。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问。汽车呼啸而过,我们的模样一定很奇特,但是,居然没有人稍微注意一下。
你得带我找个地方!她吼道,我得找衣服穿上!
去哪儿?我说。
随便!她尖叫,于是我们走上圣塔蒙尼卡公路。
走了一阵子,远远瞧见一座山上有白色的大字好莱坞,玛丽莲-梦露就说:咱们得走下这条鬼公路,到罗迪欧大道,我可以买些衣服。她一直忙着遮体——每次对面有车子来,她就把香蕉叶遮住前面,后面有车来,她又把叶子移到后面遮住屁股。要是前后都有来车,那景况可真精彩——就好像跳扇子舞似的。
于是我们走下公路,越过一大片田野。那只该死的猴子非跟着我们不可吗?玛丽莲-梦露说。我们的样子已经够可笑了!我一声不吭,但是我回头看看,公苏脸上出现一种痛苦的表情。他也从未见过玛丽莲.梦露,我想他是觉得伤心。
总之,我们一直走,但仍然无人理会我们。最后我们来到一条很忙碌的大街,玛丽莲-梦露说:老天——这是日落大道!这下于我要怎么解释我光天化日光着屁股过街啊!这一点我倒可以理解。我庆幸自己穿了这身怪物服装,这样就没有人会认出我——即使我是跟玛丽莲-梦露走在一起。
我们走到红绿灯前,信号转为绿色,我们三个过街,玛丽莲-梦露跳着她的扇子舞,对车上的人婿然微笑,好像她是在舞台上。我羞死了,她压着嗓门对我嘶声说。我被亵渎了!等这件事过了之后,我会要你好看,你这该死的白痴!
坐在车上等红绿灯的人有些按喇叭还挥手,因为他们认出了玛丽莲-梦露,过了街之后,有几辆车子转弯跟着我们。等走到威尔夏大道,我们已经引来了为数可观的群众;人们从屋里、店里出来跟着我们,玛丽莲-梦露的脸红得像猪肝。
你休想再在这城里工作!她对我说,同时对群众嫣然一笑,但是她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又走了一会儿,她说:啊——终于到了——罗迪欧大道。我望向街角,果然,有家女装店。我拍拍她的肩膀,指指那家店,但是,玛丽莲-梦露说:呃——那是波巴加洛。这年头谁要是穿上波巴加洛的衣服就惨了。
于是,我们又走了一会儿,她说,到了——佳尼——这儿有上等货。于是我们走进去。
店门边有个男店员,留着短髭穿着白色西装,口袋冒出一条手帕,我们进门时,他十分审慎地瞅着我们。我可以效劳吗,女士?他问。
我要买件洋装。玛丽莲-梦露说。
你想买什么款式的?那家伙说。
随便,你这笨蛋——你看不出怎么回事吗!
呃,男店员指向两架洋装,说那儿可能有她适合的尺码,于是玛丽莲-梦露定过去翻弄研究。
两位先生有我可以效劳之处吗?那家伙对我和公苏说。
我们只是陪她来。我回头一看,群众围在店外,鼻子贴在玻璃窗上。
玛丽莲-梦露拿了八、九件洋装到后面试穿。过了一会儿她出来说:你觉得这件如何?那是一件类似褐色的洋装,上面有一大堆腰带和吊带,而且是低领。
哦,难说,亲爱的,店员说:不知怎的——它不太适合你。于是她又到后面穿上另一件,店员说,唔,好极了!你看起来真美!
我买了。玛丽莲-梦露说。店员就说:好——你要怎么付帐?
什么意思?她问。
呃,是现金、支票,还是信用卡?他说。
嘿——笨蛋——难道你看不出我身上没带那些东西?你以为我把它放在哪几了!
女士,请——咱们别粗野好吧。店员说。
我是玛丽莲-梦露。她告诉那家伙,待会儿我会派人来付帐。
我很抱歉,小姐,他说,可是我们不这么做生意。
可我是玛丽莲-梦露!她吼道,你不认得我?
听清楚了,小姐,那家伙说。来店里的客人有一半都说自己是玛丽莲-梦露、法拉-佛西,还是苏菲亚-罗兰什么的。你有身份证件吗?
身份证件!她吼道,你以为我会把证件藏在哪儿?
没有证件,没有信用卡,没有钱——就没有衣服。店员说。
我就证明我是淮,玛丽莲-梦露说着,突然扯下她的上半身洋装。这种地方谁还有我这种xx子!她尖叫。店外的群众猛敲玻璃,吆喝欢呼。但是,那佼店员按下一个小按钮,接着一名大块头保安人员走过来,说:好了,各位被捕了。乖乖跟我走就不会有麻烦。
(未完待续)
([美]温斯顿·葛鲁姆著,于而彦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