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亚洲是红二代的一个另类,也是共产党官场的一个异数。别的红二代固然野心勃勃、舍我其谁,但一般还含光养晦、隐而不露;其他太子党虽然胆大妄为、飞扬跋 扈,但普遍还巧言令色、挂羊头卖狗肉。但刘亚洲完全不同,除了“以天下为己任”,对共产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过分的使命感,企图用自己的理想和方向重新塑造中国,思考和实践的都是“大思路”、“大战略”、“大启示”、“大格局”、“大气派”、“大手笔”外,他 有才气、个性鲜明、头脑活跃、视野开阔、妄自尊大,锋芒丝毫不加掩饰。他还志在“为天地立心”,热衷立言、立说。我本来以为自己手里的四大卷是他最完整和 唯一授权的一套海外文集,后来发现,他仅在香港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的“战略文集”就有无数个版本。即便身为无法无天的盖世太保,这种不谨慎的出圈行为也不符合共产党官场的惯例,突破了共产党容忍的边界和底线,违背了共产党的家规和私法。也因此,他在民间虽然声誉卓著,但在党内却一直非议不断,仕途更与自我期 望相距甚远,最后提前草草收场,最高的职务甚至比起只会编故事的平民加女流铁凝来都差的十万八千里。等到了刘亚洲看不起的习近平时代,则不光权力定于一 尊,思想也要垄断成铁板一块: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习近平及其思想之外,非但无法容得下另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和他的刘亚洲 主义与刘亚洲战略,习近平甚至都不可能容忍自己望尘莫及的刘亚洲任性的自比“天骄”和自由的炫耀血统。由此,刘亚洲最终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曾经一度有传言说,刘亚洲是习近平的“国师”和“军师”,是习近平治国、治军思想和战略目标与构想的主要建构者。我也相信,尽管刘亚洲看不起习近平,但共同的红色血统、政治利益和前途运会使他从心底拥戴习近平的上位并自觉主动、心甘情愿的以老弟兄的身份竭尽全力辅佐他打下天下和坐稳江山,期望能成为开国元 勋,并按照自己的蓝图帮助习近平成就伟业。在最初始,习近平确实愿意借助刘亚洲,但自古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敌国破、谋臣亡”,更别说刻薄寡 恩、狭隘多疑、残狠猜忌、外宽内忍的习近平了。据说,刘亚洲曾致信习近平,提出“调整新疆政策,不赞成暴力治疆”等等进言,被警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连一 个军队国防大学上将政委、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老兄弟都无法建言和表达自己意见,可见习近平的人品多差、行为多么危险。对习近平来说,战略决策、军国大计除 了自己之外容不得任何人关心、思考和插嘴:让你考虑你才能考虑、需要你思想你才可以思想、允许你讲话你才有权讲话,如果没让、不需要、未允许你却主动考虑、思想甚至讲话了,就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的“野心家、阴谋家”,就是“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方针,破坏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不用说刘亚州这种姿势太高、有恃无恐,给当道描画江山、为老百姓指点迷津的气派,即便是王沪宁,为习思想添砖加瓦、献言献策、注解阐释可以,如果敢越俎代庖,那也要死无葬身之地。最终,人算不如天算,刘亚洲到头来白白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习近平利用红色后代太子党们一厢情愿的举帮推戴,以红色后代太子党群体代言人的身份承袭了大统,但他不需要也不允许别的红色后代太子党鸡犬升天、咸与接班、共掌 朝纲和并据鼎司,八旗分享同治变成了一家一姓独霸,寡头贵族政治变为了个人恐怖极权。习近平不需要老弟兄、开国元勋和世袭罔替的云台凌烟阁功臣以及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他只需要宦官、弄臣和奴才。于是,和团派几乎一摸一样,几年之内太子党基本上全军覆没,一个接一个被清除出舞台,归位到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地方;剩下的,则再也不敢痴心妄想、当仁不让、天降大任的以为“天下是我们各家共同的”和自命有责于国家兴亡。于今举目四顾,皇孙寥落、贵胄凋零,合国之大再找不出一个红三代、红四代可备位选帝侯。“我死了哪管洪水滔天”,习近平不是惦记着千秋万代的陈云,身后谁来“永葆江山不变色”不是他考虑的问题;相反,他和历史上所有的暴君一样,敌人投降归顺后可以赐封一个违命候,而对自己人却绝不会心慈手软、养痈遗患。刘亚洲钦佩的秦始皇,当初机关算 尽、手段用绝,构筑了一堵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钩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以此确保子孙后世千秋万代、国祚永延、富贵永续、万无一失;他绞尽脑汁、千 算万算,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身后仅仅经年,二代们就一个接一个死于非命;可将这些二代们粉身碎骨、屠戮的干干净净的,不是他既蔑视又仇视和甚于防川的刑徒髡钳死囚贱民,而是那个最红最正宗的嫡二代之一的胡亥。还是那个千年铁律:专制制度不仅能一口吞噬掉他的敌人,反噬起自家人来也同样不吐骨头;人治的国家里不会有真正的铁帽子王和免死金牌。在极权下,玉石俱焚、无一完卵。
当然,这一节刘亚洲不会完全想不到。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观念和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头脑懵懂、仍然停留在红卫兵层次和阶级斗争时代、对当今世界毫无认知的习近平格格不入。刘亚洲寄希望习近平改革军队,但习近平大张旗鼓进行的“军改”完全是为了他个人的私利,和刘亚洲打破既得利益、强军富国的初衷毫无关系, 而且还连带着收拾了用完即弃的刘亚洲自己。聪明的刘亚洲比谁都更快的明白,在“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习近平铁打一统江山里,他的元勋梦注定 无法成真,至于能否像曹爽一样“但为富家翁足矣”还要看老弟兄的心情。于是,在日甚一日的熏天淫威下,他不但低下高傲的头颅,向习近平缴械、输诚、逢君之恶,把自己“血性”的思想专利无偿转让给了习近平, 而且连身上自带的精神血性、意志和气概,也一点点泯灭、消解、坍塌直至荡然无存。不过这,也仅仅是延缓了一步步向他逼近的噩梦般的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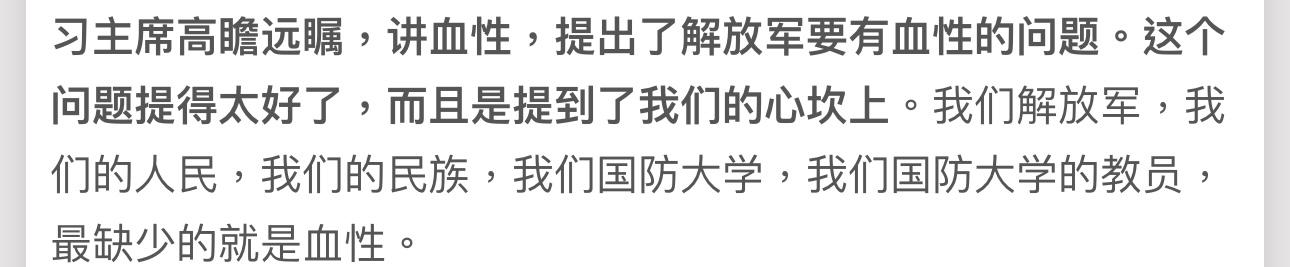


二
刘亚洲在一篇文章里写到:“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没想到一语成谶。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也许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刘亚洲一生,费尽心力救党护国,殚思竭虑的维护和试图延长这个党这个政权的统治,不想看着它走向绝路和死路。为了这个目的,他的贡献远远胜过绝大多数比他地 位职务享配香火脂膏高得多的尸位素餐、沐猴而冠者;他该想的想了、该做的做了,不该他想的做的他也越界了。看到满党满国醉生梦死、私利熏心、浑浑噩噩、唯 唯诺诺、人云亦云、只磕头不说话、既没血性又没灵魂、眼里唯有富贵荣华的文武官员,他急火攻心、忍无可忍,发自灵魂、振聋发聩的呼叫和呐喊。但他如同“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的马相伯一样, 不但没有唤醒和撼动任何人,反而把自己搞得形神交瘁、狼狈不堪。他以为自己一片忠心、天日可表,坦荡赤诚、无私无畏;不过,要是遇到一个一心作死的君王, 那就只能是痴心妄想、一枕黄粱了。《红楼梦》里说“文死谏、武死战”,刘亚洲文人好武、不文不武、能文能武,却终于没能像他倾情向往的那样为党为国尽忠玉碎、战死沙场;那么,他算是死在犯颜直谏吗?似乎也不太像。
刘亚洲全力维护一个邪恶残暴、神人共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权,最后却被这个政权无情抛弃,就像袁崇焕、岳飞一样,成了这个政权末日征程的人祭和覆灭前的殉葬品。刘亚洲一向对徐才厚、郭伯雄深恶痛绝和鄙夷入骨,说他们一辈子没有过一块骨头、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一辈子没说过一句真话、一辈子没提过一次反对 意见、一辈子都在谋取私利;可最后,一辈子为党国呕心沥血又被党国卸磨杀驴般出卖,还得忍受着文丐们谩骂、侮辱、栽赃、诬陷、诛心、把一切脏水往身上泼的刘亚洲自己,下场还不如徐才厚和郭伯雄。
按照共产党的一贯家规,一个同伙一旦失势,立即就从神变成了鬼、从伟人变成了贼顽、从雄狮变成了蟑螂、从战友变成了寇仇,从始至终、从里到外都无恶不作、恶贯满盈。过去刘少奇、林彪是这样,今天的刘亚州同样如此。义愤填膺、疾呼痛陈中国党和中国军队腐败堕落、痼疾顽症的嫉恶如仇的正义化身,而今成了诋毁、抹杀、掩盖党和军队光辉形象的用心卑鄙、肮脏险恶者;不遗余力为党国的命运忧患奉献,夜以继日为军队谋划前途、设计未来的“国宝”、“战略大师”、“中国军队的灵魂”,而今成了处心积虑反党反军反华反人民、企图颠覆共和国的罪大恶极分子;中国崛起的宏图大略、我军强盛的方向蓝图,而今成了誓必斩草除根、彻底清除的“流毒”和“有害信息”:“刘亚洲‘两面人’的嘴脸逐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言论和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隐藏在军队中的‘第五纵队’,是中国军队中的头号汉奸,是妄图将中国变为西方殖民地的带路党的领头人”。刘亚洲深知共产党家史和家丑,对这一套自然谙熟于心,只是没想到过有朝一日会原样炮制加诸于自己。刘亚洲的结局,固然是咎由自取和共产党的家务事,但我仍然为他鸣不平:这些杂碎们需要怎样恶毒无耻的心肠和刻骨怨毒的仇恨,才能编造出如此阴狠、下流、龌龊的文字!在这种极度的冤屈和凌辱下,即便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权斗高手刘少奇也会像岳飞和袁崇焕一样死不瞑目,即便是悍匪巨盗、据啸山林出身的高岗也会像“义无再辱”的王国维一样愤懑盈腔、悲忿轻生。再没有了说话自由、百口莫辩的刘亚洲心理所受的折磨与摧残,可想而知,
中国国内《红色文化网》上署名“贺兰峰”的《刘亚洲为谁殉道?》一文登出后,海外群起引述,认为是党国最高层对刘亚洲的定性和结论;还有人根据文中为批判引用的言论认定刘亚洲的民主自由倾向。其实,对由一群极左文丐们把持的《红色文化网》一类地方上的东西不必过于计较和认真。就像他们扣给刘亚洲的一大堆帽子全是谎言一样,他们引用刘亚洲的话也全是断章取义、李代桃僵,甚至凭空编造。在这些极左文丐们的心里,只有毛泽东是四个伟大,只有江青、张春桥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余哪怕习近平,在他们眼里也是阶级异己分子、变色龙、两面派——只是他们不敢说罢 了。结果仅仅几天,“贺兰峰”的文章就被删除,归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之列。文革以后的历代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党齐 心协力,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转变共产党只懂得政治倾轧和权力争夺的传统,于是刻意用腐败堕落、经济犯罪来完成与掩盖权力斗争和对异己的清洗。到了头脑懵 懂,热衷、酷爱和擅长“斗争”,脑筋还停留在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敌我矛盾”年头,同时又要威胁、恫吓和公开提醒因其为所欲为和非法长期执政而催生的党内潜在反对派的习近平,偏偏反其道而行,不但不回避,而且大张旗鼓、毫不掩饰的把经济犯罪和腐败问题上升、嫁祸、联系到“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上彻底蜕变”、“违反政治规矩”、“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危害政治安全”、“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分裂党”和“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搞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上去。但是,习近平毕竟还没有愚蠢到和文丐们一样的程度,他仍然明白:笼统的讲“政治斗争”、“政治罪行”甚至“野心家、阴谋家”都可以,但不能提“党内路线斗争”,更绝对不可以具体提哪一些高层势力在走哪种和自己针锋相对的另一条路线,一旦党内特别是军队内的高级当权派成了全民皆知的“普世价值倡导者”和“第五纵队内奸”,那对自己和中共的影响、反弹、震撼与破坏力就远远大于这样的定性和结论给自己带来的收益 和好处了。
刘亚洲晚年的地覆天翻告诉他自己——可惜为时已晚——也告诉后来人:在中国共产党为非作歹、穷凶极恶和下台覆灭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状态可循,在民主自由与专制极权之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在普世价值和反文明反人类之间容不得半点妥协和含糊。刘亚洲从前或许想探索一种中间、妥协的第三条道路,把维持世袭罔替 的共产党天下和遵循普世价值、顺应历史潮流相结合,结果不人不鬼、身败名裂,如今他恐怕悔青了肠子。
三
刘亚洲成名作《恶魔导演的战争》一书里,曾经写到了两个囚徒,这就是《红色旅和它的两次大绑架》文中被红色旅绑架囚禁的莫罗和多齐尔。在刘亚洲笔下,意大利前总理莫罗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意大利‘国魂’和实际领袖”;在被红色旅袭击、浑身染满惨死的司机和护卫鲜血后,莫罗“挺胸,阔步,象走向中世纪刑场的布鲁诺”一样迎着敌人,被目睹者称为“意大利最勇敢的男子汉”;但很快,莫罗就软弱了,在恐怖分子要求下给意大利政府写了几十封信,一再恳求释放他们的同伙以换回自己的生命。多齐尔是北约南欧地面部队司令部职位最高的美国将军,曾在越南服役,同样被“红 色旅”绑架囚禁;恐怖分子要他提供北约军事秘密,他断然拒绝;“红色旅”以死亡威胁,他毫不理睬;甚至当恐怖分子的手枪已经对准他额头时,他也只是一声不响的闭上眼睛。刘亚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也会成为那些生生不息、永无绝迹的政治囚犯中的一员。此时此刻在冰冷死寂绝望的牢房里,刘亚洲表现出的会像自己写过的两个囚徒中的哪一个呢?他会像一生自期、自许和自诩的那种真在战场的血与火中气壮山河、而不是只在纸上的枪林弹雨里出生入死过的宁死不屈的铁汉多齐尔吗? 当本来就勤于思考、天马行空,现在又有了无穷无尽时间的刘亚洲在铁监里“忆往事,思今吾”,回望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历程、拷问自己的灵魂和内心世界时,他将如何理解、认识、解释和自洽今天的结局和面临的一切呢?一腔壮志烟消,一怀霸业化为泡影,满腹“万字平戎策”成为弊履,在“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一刻,他是否能像莫罗那样,顿悟到政治的残酷、官场的无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诞与无聊?抑或,在对死亡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下,他的意志、他的信念、他的英雄情 怀和想象伴随着他的凌云壮志一起轰然粉碎、化为齑粉,然后也像莫罗一样,明知没有任何意义,但还是要强迫症似的一遍遍的写信向习近平哀哀求告。
不论怎么评价刘亚洲,都必须承认他有着极度自觉的历史感和责任感。他渴望建立不世功业,热切能在青史留名,在乎历史定位和后世评说。而今,“繁华落尽成一梦”,一世功名如尘同土、一生事业付之东流、毕生宏图转眼成空。不但万事皆休,而且被全部身心仰仗的自家人彻底否定、打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成为全党戟指、全军唾弃、记入鬼册打进恶三道永世不得翻身的“塞思黑”。他是心如死灰、彻底绝望,陷入“总把他乡当故乡”和“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虚幻与色空?是像岳飞一样,仍旧壮怀激烈,无怨无悔的沉浸在“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的往昔峥嵘岁月和荣光辉煌,对“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霸业未竟和臣子恨未雪死不瞑目,执着幻想着江水倒流、日出西方的有朝一日逐臣钦犯能在宣室中重新纵谈四海?是如同他曾书写过的青年时代卡斯特罗在巴蒂斯塔的法庭上对着全世界大声说:“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如同薄熙来被定谳无期后仍然在家书里表达着顽强不屈和坚定信念:“把我牵连进去,真冤枉,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我会在监狱中静静地等……再大的苦难我也能承受”?是如同他随时随地大义凛然告诫全军高级将领的那样“有骨头、有骨气”、“做老虎、做狮子”宁死不折?还是求仁得仁,用生命实践着自己的誓言:“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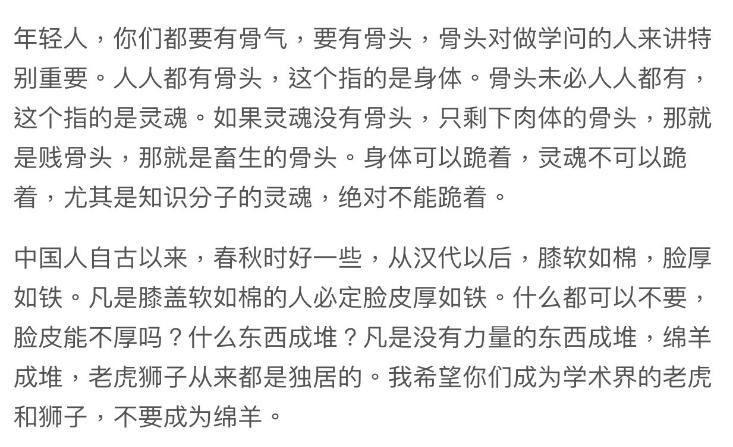
其实,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当年苏共先后为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平了反,但在是否为托洛斯基昭雪的决定上费尽心思、百般踌躇、左右为难、前后逡巡。还没有等到他们拿定最后主意,这个难题却突然一下就彻底解决、化为乌有了——因为苏共已经被一脚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共产党治下荒谬的世界里,像铁凝一样写小说写成了国家领导人,既非空前,也不会绝后;但刘亚洲这样一天飞机没开过的文人,靠着写小说和报告文学写成了空军上将,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各国对中国军费连年增长惶恐不安,其实也是多虑:共产党养了不计其数的口诛、笔伐、声讨、舞功、床征、肉战将军,公帑再多,也分配不过来呀!
(完)
来源:《北京之春》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