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清华历史学本来名气很大,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变成苏联式的工科大学,这门学科在清华就中断了。我到清华时,该系恢复创设未久,主要人员都是原社科系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基础课教师。所以,那时系里搞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带过两届研究生外,主要是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农民史选修课。到了世纪初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开设“成套的”历史系专业课,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史专业课。当时历史系已经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师,但仍然没有秦汉这一“断代”的专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来“补缺”,开设秦汉史专业课。这样一直到2009年侯旭东教授入职清华、我向他交棒为止,我在清华大约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汉史课程。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二级学科”分类中,我是属于“专史”而非“断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时期跟随赵俪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当时的重点也放在明清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农民史和农村改革问题。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多次“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并非我“专长”的工作,比如参加陕西通史项目承担宋元卷和这次去教授秦汉史,这倒也并不全是出于“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考虑。因为我本身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在专史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些时段,觉得还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贡献,或者更不客气地说,对该“专业”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所以还是“义不容辞”或者说是“趣不容辞”地接受了。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从所谓“五朵金花”的时代过来的。由向达先生首创的“五朵金花”之说,指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
古史分期
土地制度
农民战争
资本主义萌芽
民族融合
这些讨论具有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未必一直能够自由讨论,在“文革”时期一度万马齐喑、“金花”凋零之后,改革初年又重新绽放,并且发展到最高潮。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花”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头看,这种史学作为五四以后传入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其演变成经学化、神学化的“官史学”之前,曾经确实带来了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至少在两个方面,它的突破和后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第一,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史学除了大中华就只有“四夷传”的狭隘眼界。
第二,它打破了单纯叙述王朝兴衰、铺陈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传统“断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逻辑、社会演变作为历史的主线。
我以为,我们的思想解放,在摒弃经学化、神学化、官学化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谱”的模式去。如果考虑到当年“新史学”还可以出现“十批判书”这样的作品,“官史学”就一度只能歌颂“千古一帝”,即便后来学界“告别革命”而回归“保守”,淡化意识形态而转趋西方“学术前沿”,还是盛行“子路颂秦王”与新瓶装旧酒,就能够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属于典型的“金花”史学,而在这派史学无法回避的“古史分期”问题上,我当时持明确的“魏晋封建论”观点,视秦汉为“前封建”的“古典”社会(我从不用当时流行的“奴隶社会”概念),因此发表过若干以秦汉横向比较罗马、纵向比较隋唐的考证著述。在调入清华前,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还开过“古代社会形态学”和“封建社会形态学”两门选修课。即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道与心路”都已发生重大改变,我现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概念分析周秦、汉魏之别,但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当年新史学的影响是不会消灭的。我后来使用的“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等概念,也明显带有当年新史学的烙印。所以在清华开设秦汉史课时,这些学术经历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汉史课程与一般“断代秦汉史”有很大区别。
我假设学习秦汉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通史阶段的秦汉史知识,没有必要花时间再讲一遍这四个王朝(我认为前后汉完全是两个王朝,中间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应为四个朝代)的兴衰概要,所以绝大部分课时都用来讨论这四朝的制度和观念演变。尤其是分析“周秦之变”和“汉魏之变”。前者要讲清楚中国是何以从“三代”走进帝制的,这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深层次影响。而后者则要说明这一由四个王朝组成的“第一帝国”如何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机,导致秦制后来发生了不同于一般所谓“合久必分”的长时段紊乱,但周制却复兴无望,最终在经历数百年“中间期”后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国。换句话说,我不想花时间给学生讲一套“四姓之兴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时间内梳理一下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的“世道与心路”,以给今人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而且对两者的认识紧密相关。对前者认识的深浅,关系到后者的成败;对后者的体验亦能加深对前者的理解。而在这两者之间次一等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汉魏之变了。如果本书能够促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讨论,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虽然年头不算很长,但当时“超星图书馆”做了全程视频录像,据说流传甚广,至今海内外仍有不少受众。当时只是做了课程PPT,并没有成书的讲义。后来我不再讲授这门课,也没有想到要出版讲义。但是,近年来好几位有心的读者却分别根据课程录像,整理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给我,并与书界的朋友一起,极力鼓动我出版。浙江财经大学的刘志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校对引文,去除语病,划分章节。他们的热心和奉献令人感动,也使我觉得出这本书不仅有它的价值,也还要对得起学生、读者和听众朋友们的厚爱。
当然,从我过去写的秦汉相关论文,到课程开设期间乃至视频传播中,各种评价也都存在。赞同的声音就不说了,批评的意见林林总总,常见的就是说我的秦汉史不合常规,有“以论代史”的色彩。对此我这里做一点回应: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有过“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论。改革时期由于对过去史学官学化的不满,“论从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论带史”则被讥为“以论代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那时用以“代史”的“论”其实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经论证的理论教条,而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地塞进教条编织的框框里,还要不断根据上面的需要而改变叙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对嬴政先生从大批到大赞),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难道这能叫“论”?其实这种思维不改变,即便换了一套意识形态氛围,比如不再讲“五种社会形态”而改为追随“国际学术前沿”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从“反传统”变成“颂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那种“教条多而论证少”的弊病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讲“史”和“论”的关系,其实就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其实就是论据与论证的关系。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无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我们看过去“金花”时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来也是旁征博引,不仅史料要“掉书袋”,理论更要“掉书袋”。一篇文章几十个注,史料引证不多,“经典作家语录”引证倒是不少。有人说这是“以论带史”,有人嘲曰“以论代史”。其实这并不是“论”多了,而恰恰是“论”极其贫乏的表现。史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经学。离开经典作家,你就不会思考了?
说实话,我受“经典作家”影响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关知识产权的前人具论外,我是不主张理论上掉书袋的。我的论证主要是自己的思考,当然思考并非凭空,接受各种启发非常重要。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启发其实是不可少的。例如本书中关于商鞅“坏井田”究竟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关于“乡举里选”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等等,我的一些新见其实都来自生活经历。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亲身经历过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而我关于小共同体具有“温情的等级制”的看法,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其实也来自常识。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大人物忽视常识却迷信教条”造成的。当然常识不一定对,“证伪常识”往往是重大科学发现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阳东升西降,显然围着地球转”的常识证伪,而开创了近代天文学。但是常识可以证伪,却不能无视。实证研究者哥白尼和一个无视常识而高叫“太阳就是从西边升起”的妄人,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当然,研究历史要靠史料,史料的书袋必须得掉。但是秦汉史在这一点上也不同于其他“断代”,因为这一时期存世文献较宋明以后要少得多,没那么多书袋可掉。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近古时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义更加有赖于论证。再就是秦汉史既然很难发现新史料,对前人研究推陈出新就更重要,而与“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话”相比,对前人研究无论推陈还是出新,也更需要论证。所以秦汉史研究相对于宋元明清而言,其实就是一个论据相对有限、而更倚重论证的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并非治“断代史”出身的学人,我在秦汉史方面的论证对不对,还是要敬请方家赐正。
这本书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刘志先生整理的《秦汉史》课程实录视频文稿为基础写成。但从课程录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近20年,期间秦汉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张家山竹简《汉律》的发表、里耶秦简的发现,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都有重大价值,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当年授课时这些都还没有。我历来主张旧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写作的“时代坐标”。但是这本书不同。一是它过去未出版过,是作为新书出版的。二是当初作为讲义是面对学生,现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读者,对学生我应该给他们以与时俱进的知识,而不是提供一个“时代断面”而已。当年授课时,我的讲义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现在出书也应该如此。所以这次成书我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比视频记录稿多了近一倍,至于成效,就期待读者的批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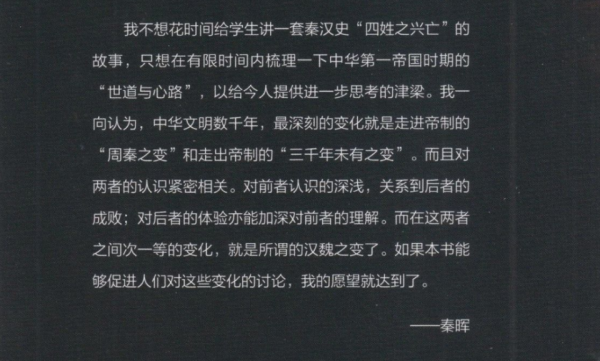
来源:秦晖《秦汉史讲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