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石剑峰
2014-11-19 13:41 来自 文化课
博尔赫斯中年失明,此后口授诗歌、寓言和故事,但越来越多借助“谈话”这一媒介以分享他未成文的文字;博尔赫斯忘年挚交、艾米莉·狄金森诗歌奖获奖诗人威利斯·巴恩斯通,记录下博氏耄耋之年炉火纯青的思想,录下他“惊人的坦率、困惑和睿智”。这本《博尔赫斯谈话录》中文版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出版,在此次理想国再版之际,译者诗人西川进行了重校精译。
《博尔赫斯谈话录》是博尔赫斯晚年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1976年,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的对话活动。1980年春,他作为帕登教授重返印第安纳,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还访问了芝加哥、纽约和波士顿,一路上边走边谈。本书为这两次美国之行中接受访谈的记录结集,共十一篇对话,涉及博尔赫斯对时代、宗教、哲学、文学和写作的诸多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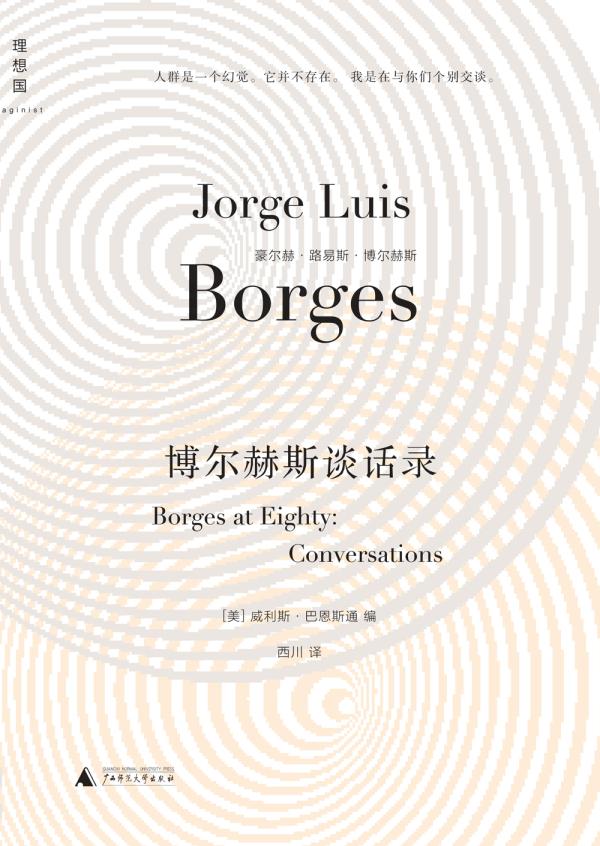
《博尔赫斯谈话录》书封
【《博尔赫斯谈话录》选摘】
豪尔赫·奥克朗代尔(以下简称奥克朗代尔):在座的诸位都想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所了解。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下简称博尔赫斯):但愿我了解他。我对他已然感到厌倦了。
奥克朗代尔:你能否带着我们浏览一下你自己的图书馆?哪些书是你青年时代所爱读的?
博尔赫斯:我现在喜爱的书就是我从前喜爱的书。我最初读的是斯蒂文森、吉卜林、《圣经》,我曾先后读过爱德华·威廉·雷恩和伯顿的两种《一千零一夜》的译本。我现在依然在读着这些书。我一生中读的书不很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读。1955年我的视力弃我而去,使我难于阅读,从那时起我就没读过什么当代作品了。我想我一辈子也没读过一份报纸。我们能够了解过去,但是现在却远远地避开我们。只有历史学家们,或那些自诩为历史学家的小说家们才能了解现在。至于今天所发生的事,那是宇宙全部神秘的一部分。
所以我更喜欢重读。我在日内瓦学习过法文和拉丁文。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甚至忘记了拉丁文是一种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使用一种蹩脚的拉丁文,因为我说的是西班牙语,但是对于拉丁文,我总是充满了向往,一种怀乡之情。而这也正是许多作家所感受到的今非昔比。我的英雄之一,萨缪尔·约翰逊就很成功地做了用英文写拉丁文的尝试 。克维多、萨韦德拉·法哈多和贡戈拉用西班牙文写出过很好的拉丁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当回归拉丁文,我们都在努力这样做。让我回到正题上来。在日内瓦我自学了德文,因为我想要阅读叔本华的原著。我找到了一种十分惬意的学德文的方法,我建议大家都这样做,如果你一点儿德文也不懂。就这样试试看:找一本海涅的《漫歌集》——这很容易——再找一本德英词典,然后就开始读。刚开始时你会感到为难,但两三个月后你就会发现,你在读着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也许你不能理解它,却能够感受它,那就更好,因为诗歌并不诉诸理性而是诉诸想象。
当我的视力下降到无法阅读之时,我说:这不应该是结束。正如一位我应该提到的作家所说的那样:“不要大声自怜。”不,这应该是一种新经验开始的证明。于是我想:我要探索我祖先使用的语言,他们或许在摩西亚,在当今称作诺森伯兰的诺森布里亚说过这种语言。我将回到古英语。因此我和几个人,其中包括玛丽亚·儿玉,开始学习古英语。我记得一些诗歌片断,很好的诗歌,其中没有一行感伤的话。这是武士、牧师和水手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这一点,在基督身后大约七个世纪左右,英吉利人就已经面向大海了。在早期诗歌里,你发现大海比比皆是。在英格兰的确如此。你会发现像“on flodes æht feor gewitan”(航行于大洋的惊涛骇浪)这般非同凡响的诗行。我是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远航至此的,我很高兴来到你们大陆的中心,这也是我的大陆,因为我是个十足的南美人。我的大陆就是美洲。
自那以后我接着学习了冰岛文。实际上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学习冰岛文了,因为我父亲曾送给我一本《弗尔松萨迦》,这本书由威廉·莫里斯译成了英文。我陶醉其中。我父亲后来又送给我一本日耳曼神话手册。但是这本书更应该叫做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既然德国、英国、荷兰,陆上斯堪的纳维亚都已忘记了所有有关神祇的故事。记忆保留在冰岛。两年前我曾去冰岛朝圣—我记得威廉·莫里斯称之为“北方神圣的土地”—不过我的朝圣从我小时候读莫里斯译的《弗尔松萨迦》和那本日耳曼神话手册时就已经开始了。冰岛为我们保留了关于北方的记忆。我们都受惠于冰岛。我很难说清我到达冰岛时的心情。我想到萨迦,想到埃达。当我想起埃达时,我想到一首名为《格陵兰诗篇》的诗。它不是格陵兰北欧人写的就是格陵兰北欧人唱的。诗所讲的是Attila,这是撒克逊人的叫法,北欧人称之为Atle,日耳曼人则称之为Etzel。我已经谈到冰岛,我已经对你们讲了我去到那里、看到那里的人们时,看到我周围那些和蔼可亲的巨人时,我是怎样感觉的。我们所谈的当然是关于古老北方的萨迦和埃达。
我已经说过那几乎是一座神秘的岛屿。现在我要接着谈第二个同样神秘的岛屿——依我看所有的岛屿都是神秘的。去年我去了趟日本,我发现了一些于我颇为陌生的东西。不论你们相信与否,那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度。这种经验我们在东方以外几乎无法获得。瞧,日本有两种文明——我们的西方文明和他们自己的文明。一个佛教徒同时又可以是一个神道教徒,他也许还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就像我的祖先或者路德教教友,诸如此类的人一样。人们谈到日本人,或许也谈到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但那种温文尔雅完全是深层的。我在日本呆了三十多天,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他们从不向我唠叨什么奇闻轶事。他们从不跟我谈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生活的确是隐蔽的——我也不跟他们谈我的生活,而我却感到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可以交谈,不仅仅谈论我们身边具体的事,我们也有真正的话题,比如宗教和哲学。
巴恩斯通:错误有个人的、职业的和文字上的。有些错误把我们引向灾难,有些却为我们带来好运。
博尔赫斯:我的一生是一部错误的百科全书。一座博物馆。
巴恩斯通:用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话说,我们应当选择林中的哪条小路?你能否告诉我们,当你在生活中走错了路,你都碰到过怎样的灾难或好处?
博尔赫斯:你是指我错写的书吗?
巴恩斯通:是的,还有你错爱上的女人和你错花的时间。
博尔赫斯:是的,但我有什么办法?所有这一切,错误的女人、错误的行为、错误的事件,所有这一切都是诗人的工具。一个诗人应当把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不幸,视为对他的馈赠。不幸、挫折、耻辱、失败,这都是我们的工具。我想你不会在高高兴兴的时候写出任何东西。幸福以其自身为目的。但是我们会犯错误,我们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们变为诗歌。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我就会觉得我生命的每一时刻都具有诗意。我生命的每一时刻就像一种黏土,要由我来塑造,要由我来赋之以形态,把它炼成诗歌。所以我觉得我不该为自己的错误而抱歉。这些赋予我的错误产生于极其复杂的因果之链,或者毋宁说无止境的结果与原因之链—也许我们的错误并非始于原因——以便让我将它们转化为诗歌。我有一件良好的工具:西班牙语。当然我也受惠于英语,受惠于我对拉丁文的记忆,以及另一种我所热爱的语言:德语。如今我正在学习古英文,也在努力对日语有所了解,我希望我能继续下去。我当然知道我已经八十岁了,我希望我会随时死去,但我又能拿死亡怎么办呢?只好继续生活,继续做梦,既然做梦是我的任务。我不得不时刻沉浸在梦境之中,然后这些梦就只能变成话语,而我也只能抓住它们,尽我最大或者最糟的努力运用它们。所以我想我不该为我的错误而抱歉。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我从不翻过头来重读,我并不了解它们。我是不得不写时才写点东西。一旦它发表了,我就尽量把它忘记,这也很容易。既然我们是在朋友们中间,我就告诉你们:当你们走进我的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北梅普街上的家,希望你们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来访——你会发现那是一座挺不错的图书馆,但其中没有一本我自己的书,因为我不允许它们在我的图书馆里占一席之地。我的图书馆只存好书。我怎么能和维吉尔或斯蒂文森比肩而立?所以我家里没有我自己的书,你一本也找不到。
奥克朗代尔:博尔赫斯,既然你说到你的家,我就想说,你是生有定处而又到过所有的地方。
博尔赫斯:不,不,不是所有的地方。我希望去中国和印度。不过,我已身在那里,既然我读过吉卜林的著作和《道德经》。
奥克朗代尔:或许你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大多数人从没去过,或将要去的地方,讲讲老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中你长大的那块地方,讲讲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和它的历史。
博尔赫斯:我对它实在所知甚少。我出生在城里贫民窟颇为集中的一边,名叫巴勒莫,但我对那个地方从未感到过兴趣。巴勒莫使我感兴趣是在1929年左右,在我还是一个小孩时,我所记住的都是我读过的书。和那个地方相比,那些书要真实得多。所以说实在的,我的记忆里装的是斯蒂文森、吉卜林,《一千零一夜》和《堂吉诃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书了,以后一直没放下,特别是第二部,我要说这部分写得最好。第一部或者可以无伤大雅地略去,除了第一章,那写得的确精彩)。所以关于我的童年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一点点。我还记得我祖上的照片,我还记得几把曾经东拼西杀的刀剑—你们管那叫西方的胜利,而我们管那叫Laconquista del desierto(征服荒漠)。我爷爷打过红种印第安人,或如我们所称的潘帕斯草原印第安人——Los indios pampas。但是我自己只是零零星星地记得一点那时的事。我的记忆主要是关于书籍的。事实上,我几乎记不清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记日子。尽管我知道我旅行过十七八个国家,可我说不清我先到过哪儿,后到过哪儿,我也没法告诉你们我在一个地方呆过多久。整个这一切就是地区、意象的大杂烩。所以看起来我们又回到了书本上。别人一跟我说话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总是回到书本上,回到引文上。我记得我的英雄之一爱默生,曾经就此警告过我们。他说:“让我们当心吧,生活本身也许会变成一段长长的引文。”
奥克朗代尔:为什么你想去中国旅行?你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什么?
博尔赫斯: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在我捧读赫伯特·阿伦·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时我就这么觉得。我多次读过《道德经》的许多种译本。我认为阿瑟·韦利的译本最好,但我也读过卫礼贤的译本和法文译本,西班牙文的译本也有好多种。此外,我在日本呆过一个月。在日本,你始终能够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的阴影。这与政治无关,这与日本文化是它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无关。在日本,人们感受中国就像我们感受希腊。我当然知道我永远搞不懂中文,但是我要不断地阅读翻译作品。我读过《红楼梦》,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我读的是英文和德文两种译本,但是我知道还有一种更加完备的,也许是最忠实于原文的法文译本。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红楼梦》这部书就像它的书名一样好。
奥克朗代尔:我想请你把我们带到某个你不曾去过的地方。
博尔赫斯:我要说那个地方是过去,因为现在是很难改变的。现在的某些东西既坚固又僵硬。但是说到过去,我们则时时都在改变着它。每当我们想起什么,我们都稍稍改变了我们的记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整个过去,感谢人类历史,感谢所有的书籍,感谢所有的记忆,因为说到底,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过去,而过去则是一种信念。比如我说“我于189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就是信念。我根本记不得我的出生。如果我父母告诉我“你生于三世纪的廷巴克图”,我当然也会相信他们。但是我对这一事实毫不怀疑,因为我想他们不会对我撒谎。所以当我说我于1899年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所做的其实是对于一种信念的信服。
要回到过去,过去是我们的财富。这是我们惟一拥有的东西,它可以由我们来支配。我们可以改变它,我们可以把那些历史人物想象成别的样子。合成过去的不仅仅是具体发生过的事件,而且还有梦境,这一事实非常之好。我要说对我们来讲,麦克白属于现在就像他属于过去,就像瑞典的查理、尤利乌斯·恺撒或玻利瓦尔。我们有书,而这些书实在都是梦。每一次我们重读一本书,这本书就与从前稍有不同,而我们自己也与从前稍有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踏踏实实地依靠“过去”那个巨大的集市。我希望我能够继续寻找通向那个集市的道路,并将我对生命的切身体验投入其中。
(注:本文有删节)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