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
我们能不能出门?这件事不再由我们自己决定。我虽然在捂汗,但还算幸运的是,我还能出门。很多地方都限制人们进出小区。
一个在湖北某县城的朋友说她所在的小区已经被限制出入好几天,社区通知昨天开始完全禁止出入,买菜都不行。
昨天早上,她家人赶快带着口罩和通行证出门买菜,很多人在菜市场抢菜,她家人去买土豆的时候前面一个人打算买完所有的土豆,她家人请求他留一些,她家人才买到一点土豆。下午,她家人想再出去买一些东西就出不了小区了。这如同武汉封城时的套路,临时通报,没有告知居民生活如何得到保障。
政府在应对传染病的时候,除了控制病毒本身,还要将人们的恐惧考虑在内。可是恰恰相反,有的地方开始鼓励举报,举报一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奖励1万元,病人自觉去医院也会奖励一些钱。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地被消耗,恐慌却在被加强。这几天周围被管控得越来越严,超市限制进入的人数、周边被封起来的地方越来越多、更多的隔离区域。而很多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穿制服的人都成了无能者。我感到深深地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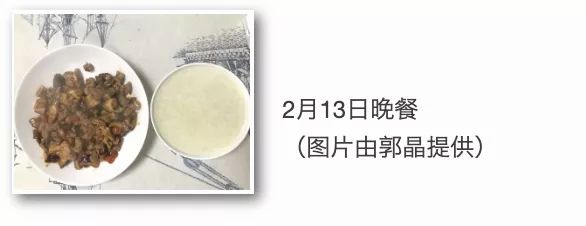 昨晚的晚餐是香菇炒肉加稀饭。晚饭后和朋友们聊天。有人在学英语,大家分享了一些学习经验,大体上说是要经常用,多听和看英文的文章和节目。当然,张口说也很重要,我们学英语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昨晚的晚餐是香菇炒肉加稀饭。晚饭后和朋友们聊天。有人在学英语,大家分享了一些学习经验,大体上说是要经常用,多听和看英文的文章和节目。当然,张口说也很重要,我们学英语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有人说:“学习一门语言学的不仅是一个技能,还是一种文化。”日本记者伊藤诗织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黑箱》,她曾到中国多个城市分享她的经历,有个朋友参与了她的活动,这个朋友说伊藤诗织讲日语就特别谦卑,讲英语的时候就很有力量。
现在大家都宅在家里,我们就讲到一些宅文化。很多宅在家里的人自嘲为肥肥,他们中一些人有全职工作,但可能是螺丝钉类的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可能是父母帮忙安排的工作。肥肥花很多时间玩游戏,他们喜欢二次元。游戏和二次元的文化里充满了性别歧视,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来呈现。很多肥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甚至父母还为他们提供生活照顾。

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消极抵抗,因为阶层固化,年轻人缺乏试错的机会,很多人看不到上升的空间,那是一种“努力也没用”的绝望。
可是女人依然宅不起,社会从来不会让女人轻易地被照顾,女人如果闲在家里,受到逼婚的压力更大,女人在家不做家务也会被指责。很多人开始在进行性别逃离,男人不想承担社会加给他的养家糊口的责任,女人则不想再作为“贤妻良母”照顾家庭。
有人说她昨晚梦到没有戴口罩,在梦里东躲西藏的。我们讲到梦。很多人都曾梦到过考试,梦里经常要没有做好准备就考试,或者考试的时候想抄别人却抄不到。我时不时地梦到自己回到初高中的时候,梦里对考试总是很着急。考试会有一个结果,它可以用来判定我们是不是好学生。我们从小就背负着这个压力。
大学毕业后,我们可能不需要再通过考试证明自己,可还是会有一些时候对自己充满怀疑,似乎需要一些标准来证明自己。其实,某一次的成绩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是很悲哀的,可是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我觉得读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上大学后我开始看一些社会学方面的书,关注社会议题,参与行动,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我的世界不断被拓宽。
有几个人还经常梦到厕所。有人梦到急于上厕所却找不到厕所,有时候是真的尿急,有时候好像是某种焦虑。有人在梦里当着很多人的面上厕所,会有一种羞耻感。
我偶尔梦到初中的厕所,它在教学楼的后面,光线被遮挡,很阴暗。厕所没有隔间,是一排坑,大概有二三十个,供约一千人用。夏天下雨,厕所就开始有积水,要隔一段距离垫一个砖块踩着进入。夏天还会有很多蛆,上厕所要不踩到是不可能的。那里很脏,是一个我想要逃离的地方。
今天八点左右下了雨,雨声很大,我就起了床。我打开窗户,微风吹过,竟然没有感到寒冷,反而是一种清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天气就发生了变化。我倚着窗户,在窗前站了好一会。

楼下,有人开车出门。路上很少人。我想今天要不要出门。每天出门不再是必须,但也没有计划,而是临时的决定。
每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出门,我担心真的不能出门了我会后悔,可是今天更重要。我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似乎都不紧急,没想到我是在这样的处境里变得有点拖延的。最后,我没有出门,从一些琐碎的工作做起,慢慢定下心来。
来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