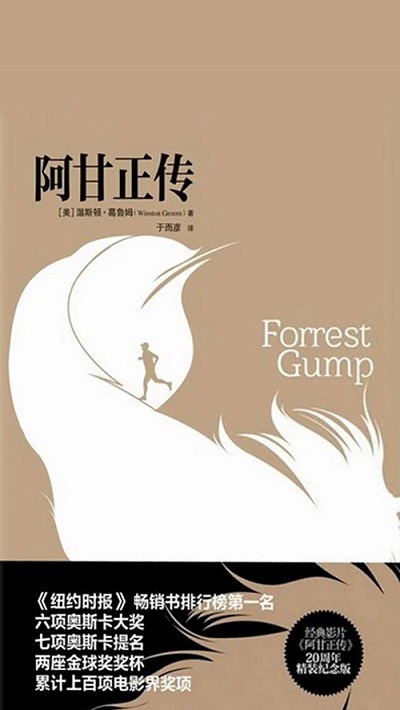第十五章
呃,就这样,我们种起棉花。一亩又一亩的棉花田,顺着山势起起落落,有整个宇宙那么多。要说我这辈子有什么是确定不移的事儿,那事儿就是:假如我们逃出这地方,我绝对不当个棉农。
打从在丛林中遭遇大山姆和食人族的头一天起,确实发生了不少事情。首先,弗芮区少校和我说服了大山姆,不要逼我们把可怜的公苏送给他的族人煮来吃掉。我们说,让公苏帮我们种棉花要比拿它打一顿牙祭用处大得多。所以,现在公苏天天戴着一顶草帽,背着一个麻布袋,跟我们一起种棉花。
还有,我们到那儿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星期,大山姆走进我们的草屋说:喂,阿甘老弟,你会不会下棋?
我说:不会。
他就说:唔,你是个哈佛人,或许愿意学学。
我点头,就这样我学会了下棋。
每天傍晚我们做完农事回来,大山姆就取出棋盘,我们围炉下棋到深夜。他教我各种棋步,头几天他还教我战略。但是后来他就不再教了,因为我赢了他一、两盘。
过了一些时日,棋局愈下愈久。有时候会持续好几天。因为大山姆对他的下一步举棋不定。他对着棋盘研究好半天,才挪动-枚棋子,但是我总会赢他。有时候他会好气他自己,用根棍于敲他自己的脚,或是拿他的头去撞石头什么的。
以哈佛人来说,你是个很不错的棋士。他会说,要不他就说:呃,阿甘——你刚才为什么下那一步棋?我什么也不肯说,或者只是耸耸肩,弄得大山姆总是暴跳如雷。
有天,他说:你知道,阿甘,我真高兴你来到此地,我才有下棋的对手,我也高兴救了你,没把你下锅煮了吃。只有一个遗憾,我实在想赢你一盘。
说着,大山姆舔舔舌头,这么一来不必是白痴也知道:我要是让他赢了一盘,他就心满意足了,那么他就会当场把我煮了当晚餐。实在让人提心吊胆,朋友,明白我的意思吧?
在这同时,弗芮区少校遇上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一天,她跟公苏和我一起从棉花田回来的时候,有只粗大的黑胳膊从一堆树丛伸出来,招呼她过去。我和公苏停下来,弗芮区少校走到树丛前面,问:是谁在里面?突然间,大胳膊伸长,抓住她,将她拉到树丛里。公苏和我对望一眼,立刻往她那儿跑过去。公苏先抵达,我正要跳人树丛中,公苏拦住我。它摇头挥手要我走开,我们走到一边等待。树丛里传出各种声响,而且枝叶抖动得厉害。我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从弗芮区少校的声音听起来,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所以公苏和我就继续打道回村子。
大约过丁一个小时,弗芮区少校跟一个大家伙回来了。那家伙眉开眼笑,她则牵着他的手。她带他进了草屋,跟我说:阿甘,我介绍你认识古洛克。
嗨!我说。我曾在村子附近见过这家伙。古洛克咧嘴笑着点头,我也点个头。公苏则在一边搔着下裆。
古洛克要我搬过去跟他住,她说,我想我会搬过去,因为咱们三个住这儿是有点挤,你说是不?
我点头。
阿甘,你不会跟任何人泄漏这件事吧?她问。呃,她以为我会跟谁泄漏?我倒想知道。不过我只摇摇头,弗芮区少校就拿了她的零碎东西跟古洛克去了他的住处。事情就是这样。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终于一年年过去。每天我和公苏及弗芮区少校都在棉花田里工作,我开始觉得自己是罗马神话里吃狼奶长大的雷摩斯大叔什么的。晚上,我在棋盘上痛宰大山姆之后,便跟公苏钻进草屋,坐下来聊聊。我们已经到了可以用手语,做表情,咕咕哝哝聊天的程度。过了一段时日,我可以拼凑出它的一生经历,原来它跟我的经历差不多悲惨。
公苏还是小猿猴的时候,有天它的爸爸妈妈在丛林里散步,几个家伙拿网子把它们捉走了。它跟着叔叔婶婶勉强过了一段日子,后来因为食量太大被撵走,它就独个儿自立更生。
它的日子还过得去;整天在大树间晃荡,吃香蕉,直到有一天它对外面的世界起了好奇心,于是它荡过一棵又一棵大树,来到丛林边的一个村落。它口渴,于是坐在一条小溪旁喝水,这时有个家伙划着独木舟经过。公苏从没见过独木舟,因此它就那么呆呆望着它,那家伙就把独木舟划到它那儿。它以为那家伙是要载它一程,但,结果那家伙用桨敲公苏的脑袋,把它像猪似的捆绑起来,接着它只知道自己被卖给了另一个家伙,送到巴黎在一项展览会上展示。
展览会上有另一只长胶棕毛的巨猿,名叫杜丽丝,它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母猿。过了一阵子,它俩相爱了。举办展览的家伙带他们环游世界,而无论走到哪儿,最吸引观众的就是将杜丽丝和公苏关在一个笼子里,让大家看它俩做爱——就是那种展览。总之,公苏觉得很难堪,但那是他俩活命的唯一机会。
有次它们在日本展出,有个家伙开价买下了杖丽丝。它走了,公苏不知道它去了哪儿,它又孤零零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公苏对人世的态度。它变得愤怒不平,展览中它龇牙闷吼,最后它会拉屎,然后。把屎扔出笼子,撤在那些花钱来开眼界的人身上。
这样过了一阵子,主办展览的家伙受够了,把公苏卖给了太空总署,就这样它最后到了新几内亚的丛林。我多少了解它的感受.因为它仍然孤零零想念杜丽丝,我也孤零零想念珍妮,而且,没有一天不挂念她。可是,咱俩同病相怜,这会儿都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大山姆的棉田收获好得出乎想像。我们收割了一捆又一捆棉花,让他们在新搭的大草棚里整理。终于,有一天.大山姆说他们准备造一条大船——驳船——载运棉花,然后奋力突破小黑人的势力区,到城里卖掉棉花赚一笔钱。
我都设想好了,大山姆说。首先我们把棉花拍卖,拿到钱。然后用那些钱买些我的族人需要的物品。
我问他是哪些物品,他说:哦,你知道的,老弟,珍珠、饰物啦,或许还买面镜子、还有手提收音机,一盒上等古巴雪茄、两箱酒。
原来如此。
总之,又过了几个月,我们收割了当季最后一批棉花。
大山姆的驳船差不多完工了,于是,在动身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们举行了一项盛大的庆祝仪式,同时驱赶邪灵。
全部落的族人围着火唱着噗啦噗啦,敲着鼓。他们还把那个巨大的锅拖了出来,架在火上煮着,但是大山姆说它只是象征仪式。
我们坐在旁边下棋.我跟你说,朋友——我兴奋得快炸了!只要让我们到了城镇附近,我们立刻逃之夭夭侥公苏也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它也坐在那儿搔着腋下,咧嘴笑得好开心。
我们已经下了一、两盘棋,正要结束另一盘棋局时,突然间,我低头一看,该死,大山姆要把我将死了!他笑得好得意,我可以在黑暗中瞧见他的牙齿,于是我心想:得赶紧摆脱将死的局面。
问题是,我脱不了困。因为我心里一直在打着如意算盘,不知不觉在棋盘上把自己困死了。无路可走。
我研究棋盘好半天,火光照在大山姆微笑的牙齿上,清清楚楚反映出我紧蹙的眉头。于是我说:啊,呃——我要尿尿。大山姆点个头,还在咧嘴笑;容我说一句,这可是我记忆中头一回因为说这句话脱困,而不是惹祸上身。
我走到草屋后面尿尿,之后,并没有回去下棋,我钻进草屋向公苏说明情况。接着我悄悄溜到古洛克的草屋,小声把弗芮区少校叫出来,把情况也跟她说了一遍,并且说还是趁大伙被煮熟之前赶紧逃走好了。
于是,我们都决定放手一搏。古洛克说他要一起走,因为,他爱上了弗芮区少校——反正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总之,我们四个立刻悄悄溜出村子,来到河边,正要坐上土著独木舟的当日,突然间,我抬头一看,大山姆带着大约千名土著站在我面前,神情阴狠又失望。
省省,老弟,他说,你真以为骗得了咱这老狐狸?
我告诉他:噢,我们只是想在月光下泛舟——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唉,他说,他明自我的意思,接着他的手下抓住我们拖回村落。巨锅在那儿噗噗滚沸,他们把我们绑在木桩上,情况看来不太妙。
晤,老弟,大山姆说,事情这么转变实在很不幸。不过,不妨这么看它,起码你知道自己填饱了一、两个饥饿的肚子,可以聊感安慰。还有,我必须告诉你——你无疑是我所遇到的最高强的棋士,而我在耶鲁四年中拿了三年西洋棋冠军。
至于你,女士,大山姆对弗芮区少校说,我很遗憾不得不结束你和这位古洛克老兄的热恋,不过,你了解我的苦衷。
不,我不了解,你这诡诈的野蛮人,弗芮区少校说。你究竟会得到什么好处?你应该自惭!
也许我们可以把你和古洛克放在同一个盘子里上桌,大山姆呵呵笑。自肉配黑肉——我个人要吃一条大腿,或者可能吃个胸——嗯,这倒满不错的。
你这恶毒、坏到极点的混蛋!弗芮区少校说。
随你说,大山姆说。好啦,盛宴开始!
他们解开我们,接着一群土人把我们拖到巨锅那儿。他们先擒起可怜的公苏,因为大山姆说它会是道佳肴,他们将它高举在巨锅上,正要扔进去的当口,且慢,一支箭从天而降,射中抬着公苏的一个家伙。那家伙倒下,公苏摔在他身上。接着箭如雨下,从丛林边射向我们,所有人惊慌大乱。
是小黑人!大山姆减道。快取武器!所有人都跑去拿长矛和刀。
我们四个既无长矛也没刀,于是又朝河边奔去,但是才跑了不到十尺,突然间被树丛间设下的罗网倒吊在半空中。
我们像蝙蝠似的挂在那儿,血液直灌脑门之际,一个小家伙从树丛间钻出来,哈哈笑我们。村中传来各种野蛮的声音,但是过了一阵子所有声音都静下来。接着一群小黑人出现,割下我们的网子,绑住我们的手脚,带回村落。
哎呀!他们已经捉住大山姆和他的族人,而且也绑住了他们的手脚。看来小黑人就要把他们统统扔进巨锅。
唔,老弟,大山姆说,看来你们侥幸保住了命啊?
我点头,但是我不敢确定我们是不是换汤不换药,终究得死。
这样吧,大山姆说,看来我和我的族人是完了,不过也许你们还有活命的机会。要是你能弄来你那支口琴吹上一、两首曲子,也许可以救你们的命。小黑人的酋长酷爱美国音乐。
谢了,我说。
别客气,老弟。大山姆说。他们把他高高抬到巨锅上面,突然,他对我喊:骑士落在主教三——然后小卒十落在国王七——我就是用这步棋打败你的!二声水花四溅,接着大山姆被缚的族人又开始唱噗啦噗啦。我们全体的情况都大大不妙。
第十六章
煮完了大山姆的全族人,取下他们的脑袋之后,小黑人将我们倒挂在长竿上,像猪似的抬入丛林。
你想他们打算怎么处置我们?弗芮区少校对我喊道。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吼道,这可以说是实话。我受够了这些鸟事。人的忍受力只有这么大的限度。
总之,走了一天左右,我们来到小黑人的村子,朋友或许已经料到了,丛林中的空地上是-间间小小的草屋。他们将我们扛到空地中央的一间草屋前,那间草屋四周站着许多小黑人——还有个蓄着长长的白胡子,没有一颗牙齿的小老头,像个婴儿似的坐在一张高椅上。我猜想他就是小黑人的酋长。
他们将我们从网子里倒到地上,给我们松绑,我们站起身,拍去身上的灰土,小黑人酋长叽叽咕咕说了些话,接着他爬下椅子,直接走到公苏面前,踢它的下裆。
他干嘛踢它?我问古洛克,他跟弗芮区少校同居期间已经学会讲一点英语。
他要知道猿猴是公的还是母的。古洛克说。
我心想,应该有比较客气的法子弄明白这一点,可是我没吭气。
接着,酋长走到我面前,又叽叽咕咕一番——大概是小黑人话什么的——我正准备下裆也挨一脚,但是古洛克说:他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跟那些可陷的食人族住在一起。
告诉他这可不是我们出的主意。弗芮区少校开口说。
我有个主意,我说。告诉他们,我是美国乐师。
古洛克把这话告诉酋长,酋长狠瞅着我们看半天,然后他问古洛克一句话。
他说什么?弗芮区少校追问。
他向猿猴奏什么乐器。古洛克说。
告诉他猿猴会奏长矛。我说,古洛克转述-遍,于是,小黑人酋长宣布他要听听我们演奏。
我取出口琴,吹了一首小曲——坎普镇竞赛。小黑人酋长听了一会儿,开始拍手跳起类似方块舞的舞步。
我吹完之后,他问弗芮区少校和古洛克会演奏什么乐器,我叫古洛克告诉他弗芮区少校会演奏刀子,古洛克不会演奏——他是经理。
小人酋长神情有些迷惑,说他从没听说过有人会演奏长矛或刀子,不过他吩咐族人给公苏几支长矛,给弗芮区少校几把刀子,说要看看我们会奏出什么音乐。
我们一拿到长矛和刀子。我就说:好——动手!公苏立刻用长矛敲小黑人酋长的脑袋,弗芮区少校用刀子威吓几个小黑人。我们逃入丛林中,小黑人紧迫在后。小黑人一直在后面向我们扔掷各种石头、箭镞和吹箭。突然间,我们跑到了河边,无路可逃,而小黑人就要抓住我们了。我们正打算跳进河里游泳逃生,突然对岸响起一声来福枪声。
小黑人们已经扑至,但是另-声枪声,他们立刻掉头逃回丛林。我们望向对岸,噢,天呐,对岸有两个身穿丛林夹克,戴着白色头盔的家伙。他们跨入一条独木舟,朝我们划来,等他们挨近之后,我瞧见其中一个的头盔上有美国太空总署的字样。我们终于获救了。
独木舟靠岸后,头盔有美国太空总署宇样的家伙下船走向我们。他一径走到公苏面前,伸出手,说:是甘先生吧?
你们这些混球,究竟他妈的躲哪儿去了?弗芮区少校吼道。我们困在这该死的丛林里将近他妈的整整四年了!
抱歉啦,女士,那家伙说,不过我们办事也有先后顺序,你知道。
总之,我们终于逃脱了比死还可怕的命运。他们把我们载上独木舟,往下游划去。其中-个家伙说:唔,各位乡亲,文明就在前面了。我看各位可以把你们的经历卖给出版商,赚一大笔钞票。
停船!弗芮区少校突然喝令。
两个家伙对望一眼,但还是把独木舟划到岸边。
我决定了,弗芮区少校说。我找到了生平头一个了解我的男人,我不打算放弃他。近四年来古洛克和我在这地方生活幸福,我决定跟他-起留在这儿。我们会回到丛林建立我们的新生活,养一窝孩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这人是食人族-个家伙说。
你去吃个痛快吧,老兄。弗芮区少校说完,和古洛克下船手牵手走回丛林。在他俩走出视线之前,弗芮区少校回头跟公苏和我挥挥手,然后两人消失了踪影。
我回头看看坐在独木舟尾的公苏,它在那绞着爪子。等等。我对那两个家伙说。我过去坐在公苏旁边,问它:你在想什么?
公苏没作声,但是它眼中有颗小小的泪珠,于是,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它抓住我的肩膀使劲搂我一下,然后跳下船圈到岸边-棵树上。最后,只见它吊着-根蔓藤荡过丛林,也消失了综影。
太空总署那名老兄摇摇头。呃,你呢,笨蛋?你可要跟着你的朋友们待在这个野蛮地方?
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半天才说:呃,不。然后坐回独木舟内。他们划着浆顺流而下之际,我心里当真掠过留下来的念头。可是我没办法这么做。我想大概我还有别的渴望要完成。
他们用飞机送我回美国,途中告诉我国内将会替我准备一项盛大的欢迎会,不过这话我好像曾经听过。不过,真的,飞机一降落华盛顿机场,就有大约百万人在那儿鼓掌欢呼,像是很高兴见到我。他们让我坐在-辆黑色大轿车的后座进城,说要带我去白宫晋见总统。没错,那地方我也曾经去过。
呃,到了白宫,我以为会见到那位请我吃早饭,看贝弗利山人电视节目的老总统,不过他们这会儿选了个新总统——一个头发往后梳得油光光,腮帮子鼓鼓的,鼻子像挂了个肉垂的家伙。
说说看,这位总统说,你这趟旅途刺激吗?
一个穿西装站在总统旁边的家伙附耳对总统说了句话,总统猛然又说:呃,啊,其实我的意思是你能逃离丛林生活之苦,实在太好了。
穿西装的家伙又附耳对总统说了句话,于是总统对我说:呃,你的同伴呢?公苏?我说。她叫这个名字吗?这下于他看看手里的二张卡片。这上面写的是一位珍妮.弗芮区少校,还说你虽然获救,她却被强拖回丛林了。
哪儿来的这一段?我问。
这儿写的啊!总统说。
事实不是这样。我说。
你是暗示我说谎?总统说。
我只是说事实不是这样。我说。
你给我听清楚了,总统说,我是你的最高统帅。我不是坏人。我不说谎!
很抱歉,我说,但是弗芮区少校的情形不是这样。你把卡片上这段话删掉,不过——
卡带!总统吼道。
啊?我说。
不,不,穿西装的家伙赶紧跟总统说,他说的是-卡片-——不是-卡带-——总统先生。
卡带!总统尖叫。我告诉过你不准再在我面前提这个字眼!你们统统是不忠不信的猪猡!总统用拳头猛捶他自己的膝盖。
你们统统不了解。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说过!就算听过见过,要不是我忘记了,要不就是最高机密!
可是,总统先生,穿西装的家伙说,他没有说那个字,他只说-
哦,你说我说谎!他说,你被解职了!
可是你不能解我的职,那家伙说,我是副总统啊。
呢,抱歉我得这么说,总统说,不过要是你到处骂你的统帅是个骗子,你绝对当不成总统。
唔,我想你说得对,副总统说,请原谅。
不,我请你原谅,总统说。
随便啦,副总统说,他看起来有点儿坐立难安。恕我失陪,我得去尿尿。
这可是我一整天听到的第一个明智的意见。总统说。
接着他转向我,对了,你不就是那个打乒乓球的家伙吗?
我说:嗯。
你有没有电视机?我问。
总统滑稽地看着我。嗯,有一台,可是近来我不大看电视。太多坏消息。
你有没有看过-贝弗利山人-这节目?我说。
还没播出呐。他说。
现在播什么?我问。
真相-——不过,你会不想看这个节目——净是屁话,接着他说,呃,我得去开个会,我送你到门口吧?去到外面阳台上,总统压低嗓门很小声的说,喂,你想不想买只表?
我说:啊?于是,他挨到我身边,掀起他的西装袖子,哎呀,地胳膊上起码有二、三十只表。
我没钱呐。我说。
总统放下袖子,拍拍我的背。唔,等你有钱了再来,咱们好商量,啊?
他跟我握手,一大群摄影记者拥上前拍照,然后我就走了。不过,我得说-句,那位总统看起来倒还像是个好人。
总之,这会儿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处置我了,不过我不必猜测太久。
大约过了一天热闹冷却下来,他们把我安顿在一家饭店里,但,有天下午两个家伙走进我的房间,说:听清楚了,阿甘,白吃的午餐结束了。政府不再负担这些——现在起你自己打发。
呃,好啊,我说,不过,给我一点路费回家如何。我现在有点缺钱。
省省吧,阿甘-,他们说。你用勋章打昏参议院记录员,没坐牢已经算你走运了。我们已经帮忙让你逃过牢狱之灾——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不再管你的鸟事啦。
于是,我不得不离开饭店。由于我没有行李,因此并不难行走,我就这么走上街。走了一阵子,经过总统住的白宫,出乎意料,白宫前面居然有一大群人,戴着用总统的脸孔做成的橡皮面具,还拿着什么标语。我猜想他-定很高兴这么受大家的拥戴。
第十七章
虽然他们说不肯给我一毛钱,但是我离开饭店之前,其中-个家伙借给我一块钱。我一见到公用电话就打电话到我妈妈住的贫民之家。但是,一名修女说:甘太太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
我问她去哪儿了,修女说:不知道——她跟一个新教徒跑了。我谢谢她,挂上电话。说起来,我是有点儿安心了。起码妈妈跟某个人跑了,不再待在贫民之家。我想总得找到她。但是,老实说,我并不急着找她,因为她铁定会为了我离家之事对我又哭又叫又骂,就好比天绝对会下雨那么铁定。
天果真下雨了。淋得一身湿的猫儿、狗儿和我找到一个遮雨蓬躲在下面,直到有个家伙出来把我撵走。我全身湿透又冷,经过一栋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看见人行道中央有个大大的塑胶垃圾袋。我走近时,袋子动了一下,好像里面有东西!
我停下来,走到袋子前面,用脚尖顶顶它。突然间,袋子往后跳丁四尺远,一个声音从袋子底下传出,说:滚开!
谁在里面?我问。
那个声音说:这是我的暖气栅,你去找你自己的。
你在说什么?我说。
我的暖气栅,那声音说,别碰我的暖气栅!
什么暖气栅?我问。
突然,塑胶袋略微抬高,一个家伙探出头来,眯眼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白痴似的。
你刚到城里还是什么?那家伙说。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我只想躲雨。
垃圾袋底下那个人模样真可怜,头发半秃,几个月没刮胡子,眼睛红通通布满了血丝,牙齿基本掉光了。
唔,他说,既然如此,我想让你待一下倒无所谓——拿去。他伸出手递给我另一个折好的塑胶袋。
我要怎么用这袋子?我问。
打开它,钻到袋子底下,你这笨蛋——你不是说想躲雨。说完他拉下垃圾袋重新遮住自己。
唔,我照他的话做了,老实说,真不赖。暖气栅底下会冒出热气,使袋子里头暖呼呼的,舒服又可以躲雨。我们罩着垃圾袋并排坐在暖气栅上。半天,那家伙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甘,我说。
啊?我也认识个家伙叫阿甘。很久以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丹恩。他说。
丹恩?丹恩?——喂,且慢。我说。我掀开垃圾袋,走过去也掀开那家伙的袋子,果然是他!没有腿,坐在一辆装着滑轮的小木车上。起码苍老了二十岁,我几乎认不出他。不过,是他,没错。是丹恩少尉!
从陆军医院出院之后,丹恩问到康涅狄格州想重拾教鞭教历史。但是历史这门课没有空缺,于是学校要他教数学。他憎恨数学,况且,数学教室在二楼;他没有腿,上楼吃尽了苦头。同时,他老婆跟一个位在纽约的电视制作人跑了,并且以性情不合为由诉请离婚。
他染上酒瘾,丢了工作,游手好闹了好一阵子。小偷把他家搬空了,而医院给他装的义肢尺寸不合。过了几年,他说,他索性放弃,过起流浪汉的生活。他每个月都会领到一些伤残抚恤金,但是他多半把它送给了别的流浪汉。
我也说不上来,阿甘,他说,我想我大概只是在等死吧。
丹恩给了我几块钱,叫我去街角买两瓶红匕首。我只买了一瓶,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份现成的三明治,因为,我已经一整天没吃过——点东西。
唔,老友,丹恩喝下半瓶酒之后,说,谈谈咱们分手之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我就说给他听。我告诉他,我去过中国打乒乓球,还有找到了珍妮,参力加裂蛋合唱团和示威游行,我还把勋章扔了,结果坐牢。
嗯,这件事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医院里,也想去参加游行,不过我想我不会扔掉我的勋章,你瞧!他说。他打开外套纽扣,里面的衬衫上挂满了他的勋章——紫心、银星——起码有十几二十枚。
它们让我想起一些事,他说,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事——战争,当然,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失去了太多东西,阿甘,不只是两条腿。还有我的锐气,我的灵魂。如今只剩下一片空白——原先我的灵魂所在之处,现在只有勋章了。
可是,你说的那个管理一切的-自然法则-呢?我问他,我们每个人都得配合的-万物规划-呢?
去它的,他说,那净是哲学屁话。
可是打从你告诉我之后,我就一直照着它去做。我顺势而行,尽力而为。尽量做对的事啊。
唔,也许它对你管用,阿甘。我原以为它对我也管用——可是瞧瞧我。瞧瞧我,他说,我有什么用?我是个他妈的缺腿怪物。一个混混。一个醉鬼。一个三十五岁的流浪汉。
还算好啊。我说。
哦,是吗?怎么个好法?他说。这话可难倒我了,因此,我继续跟他说完我的经历——被扔进疯人院,然后被送上太空,又掉在食人族的村子里,还有公苏、弗芮区少校和小黑人等等。
呃,我的天,阿甘小子,你可真是奇遇连连,丹恩说,那你怎么会落得跟我一起罩着垃圾袋,坐在暖气栅上面?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不打算久留。
那么,你有什么主意?
等雨一停,我说,我就去找珍妮。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会查出来。听起来你似乎需要援助。他说。
我望向丹恩,他两眼在胡子后面闪闪发光。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才需要援助,不过我不介意。
老丹和我那天晚上找了一家廉价教会招待所投宿,因为雨一直未停,丹恩付了一人五毛钱的晚饭钱,和两毛五的床铺钱。只要你肯坐在那儿听布道等等就可以免费吃晚饭,但是丹说他宁可睡在雨地里,也不愿浪费宝贵时间去听一个唯圣经是从的人说他对世事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丹恩借给我一块钱,我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波士顿找摩西,从前裂蛋合唱团的鼓手。果然,他还住在老地方,而且完全没想到我会联络-
阿甘——我真不敢相信!摩西说,我们以为你玩完了!
他说裂蛋散伙了。费波斯坦答允他们的钱统统被一些开支什么的耗干了,而且出了第二张唱片之后就没人再找他们签约。摩西说现在的人听一种新的音乐——滚石、老鹰,还有什么的——裂蛋的成员都离开了,找到了正经工作。
摩西说,很久没有珍妮的消息了。她去华盛顿示威游行,而我被捕之后,她又回来跟裂蛋合作了几个月,但摩西说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说有一次她在台上哭了,他们不得不用乐器演奏填塞那一场表演。之后,她开始喝伏特加,演出迟到,他们正打算跟她谈谈,她却索性不干了。
摩西说他个人觉得她的行为变化与我有关,但是她始终不肯谈,过了两星期她离开了波士顿,说要去芝加哥,打那以后五年来他没再见过她。
我问他是否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她,他说也许他还存着她临走前留给他的一个旧电话号码。他搁下电话,过了几分钟回来把电话号码告诉我。除此之外,他说:我一无所知。
我要他保重,还说我要是去波士顿一定会去找他。
你还吹口琴?摩西问。
呃,有时候。我说。
我跟丹思又借了一块钱,打电话到芝加哥。
珍妮-可兰——珍妮?一个家伙接电话说,对了——我记得她。一个满漂亮的小姐。好久了。
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她临走的说她要去印第安那波里。谁知道?她在-天波禄-那儿找到了工作。
哪儿?
天波禄-——轮胎工厂。你知道,做轮胎的——汽车轮胎。
我谢过那家伙,回去告诉丹恩。
唔,他说,我从没去过印第安那波里。听说那边秋天很美。
我们先是想拦便车离开华盛顿,但是运气不佳。后来-个家伙让我们坐在一辆运砖卡车的后面,坐到市郊,但是之后就没人肯载我们。我猜想大概我俩模样太奇怪——丹恩坐在他那辆小滑轮车上,我这大块头站在他旁边。总之,丹恩说咱们何不搭巴士,他的钱够买车票。老实说,拿他的钱我很不是滋味,但是,我觉得他想去,而且,让他离开华盛顿也是件好事。
于是,我们搭上赴印第安那波里的巴土,我把丹恩放在我隔壁的座位上,将他的滑轮车塞在上方的架子上。他一路喝红匕首,说这世界真是个鸟地方。也许他说得对。我也不知道。我终究只是个白痴。
我们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下车,丹思和我站在街上正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一名警察走过来说:不得在街上游荡逗留。予是我们就往前走。丹恩向一个家伙询问天波禄轮胎公司在哪儿,结果它在市郊,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走了一阵子,没有人行道了,丹恩没办法推他的小滑轮车,于是,我把他夹在腋下,把滑轮车夹在另一边腋下,继续走。
大约到了中午,我们瞧见一个大招牌上写着天波禄轮胎,推测到了地头。丹恩说他在外头等,我就走进去,柜台有个女人,我问她可不可以找珍妮-可兰。那女人看看一份名单,说珍妮在补胎部门工作,但是除了工厂员工,外人不得入内。呃,我呆站在那儿,不知该怎么办,那女人说:这样吧,甜心,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午休了,你何不到大楼旁边去等。也许她会出来。我就照这么做了。
一会儿出来了许多人,接着,我瞧见珍妮独个儿穿过一扇门,走到一棵树下,从纸袋里取出一份三明治。我走过去,悄悄来到她背后,她坐在地上,我就说:这三明治看起来可真好吃。她根本没抬头看。她一直盯着前头,然后说:阿甘,一定是你。
第十八章
呃,我告诉你,朋友——那是我毕生最快乐的重逢。珍妮哭着、搂着我,我也一样;补胎部门的其他员工站在一旁纳闷怎么回事。珍妮说再过三小时她就下班,叫我和丹恩到对街的小洒馆喝杯啤酒,等好。然后她带我们去她的住处。
我们去了小酒馆,丹恩喝了些涟漪酒,因为他们没有红匕首,不过他说涟漪酒更好,因为它比较芬芳。
酒馆内还有别的顾客,玩飞镖、喝酒,在桌上比腕力。有个大块头好像是酒馆内腕力最厉害的家伙,不时有人会过去跟他较量,但总是赢不了他。他们还拿它下注,一把五块十块什么的。
过了-阵子,丹思小声对我说:阿甘,你觉得自己赢不赢得了那边比腕力的大老粗?我说不知道,丹恩就说:唔,这是五块钱,我打赌你会赢。
于是,我起身走过去跟那家伙说:我可不可以坐下来跟你比腕力?
他抬头看我,微微笑着说:只要有钱,欢迎你试试。
我就坐下,两人彼此握住对方的手,然后有人说:开始!比赛开始了。其他家伙都是嗯嗯啊啊,像狗拉屎似的拼命用力,可是大概才十秒钟我就把他的胳膊扳倒在桌上,打败了他。其他人都围在桌子四周发出喔啊声,我还听到老丹大叫喝采。
呃,对方并不太高兴,但他还是付给我五块钱,然后站起身。
刚才我的手肘滑了一下,他说,不过下次你再来,我要跟你再比试一下,听到吗?我点头,然后回到丹恩那儿,把钱给他。
阿甘,他说,咱们也许找到了一个轻松赚钱糊口之道。我问丹恩可不可以给我两毛五去柜台买个松花蛋,他给了我一块钱,说:随你爱吃什么都行,阿甘。咱们现在有法子谋生啦。
珍妮下了班到小酒馆接我们去她的住处。她住的是一间小公寓,离公司不远,里面摆设了些可爱的玩意,比方说填充玩具,还有在卧房门上接个彩珠帘。我们去杂货店买了一只鸡,珍妮烧晚饭给丹恩和我吃,我把和她分手之后我的遭遇一五一十告诉她,
她对弗芮区少校很好奇,不过等我说她跟一个食人族跑了之后,珍妮似乎放心不少。她说这些年来她的日子也不顺心。
离开裂蛋之后,珍妮就跟她在和平运动中认识的一个女孩一起去了芝加哥。她们上街示威游行,多次被关进牢里,珍妮说最后她疲于上法庭,况且,她也担心自己成了前科累犯。
总之,她跟大约十五个人同住在一栋屋子里,她说他们跟她不是那么气味相投。他们不穿内衣或者根本一丝不挂,而且不冲马桶。她和一个家伙决定合租一间公寓,因为他也不喜欢他们原来住的地方,但是结果并不成功。
你知道,阿甘,她说,我甚至试过去爱他,可是我办不到,因为我总想着你。
她写过信给她妈妈,请她联络我妈妈弄清楚我关在哪儿,但是,她妈妈回信说我们家烧毁了,我妈妈住在贫民之家,但是,等那封信寄到珍妮手里,我妈妈已经跟那个新教徒跑了。
总之,珍妮说她身无分文,听说轮胎公司正要雇人,于是就来到印第安那波里,得到这份工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我即将上太空,可是,她已来不及赶到休士顿。她说她惊恐的看着我的太空船坠落,她以为我死了。打那以后,她就把时间全放在补胎上。
我把她抱在怀里,两人就这样依偎半天。丹恩自己滚着滑轮车进浴室,说他要尿尿。他进去之后,珍妮小声问他怎么尿,难道不需要协助?我说:不需要,我见过他自己尿尿。他可以自己来。
她摇头说:这就是越战带给我们的下场。
这一点也没啥争议。看见一个断腿的人不得不尿在帽子里,再把尿倒进马桶,实在令人心酸怜悯。
我们三个人就在珍妮的小公寓里安顿下来。珍妮给丹在客厅一角铺了个地铺,她还在浴室地板上放了个瓶子好让他不必尿在帽子里。每天早上她去轮胎公司上班,丹恩和我坐在家里聊天,然后去珍妮公司附近那家小酒馆等她下班。
刚开始的头一个星期,比腕力被我打败的那个家伙要求给机会让他赢回那五块钱,我给了他机会。他又试过两、三次,结果总共输了大概二十五块,过后他就不再来了。但是总有别的家伙想赌赌运气,过了一、两个月,有些人从镇上和外地小镇跑来找我挑战。丹恩和我每个星期大约赚上一百五十到两百块左右,这笔收入可真不赖。小酒馆的老板说他要举办全国大赛,让当地电视台转播等等。但是在这个计划实现之前发生了另一件事,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
一天,有个家伙走进酒馆,他穿着白色西装和夏威夷衬衫,颈子上挂着许多金饰。他坐在吧台看我解决另一个挑战者,然后过来坐到我们的桌子。
我叫麦克,他说,我听说过你们。
丹恩问他都听到些什么,麦克说:听说这家伙是世上最有力气的男人。
那又怎样?丹恩问,那家伙说:我有个点子可以让你们赚大钱,远远超过你们在这儿赚的三毛两文。
怎么说?丹恩说。
摔跤,麦克说,不过,不是这冲动动胳膊的小玩意——我指的是真正的摔跤。有擂台,还有成千上万花钱的观众。
跟谁摔跤?丹恩问。
随便谁都行,麦克说,职业摔跤手有一项巡回比赛——-蒙面人-、-奇大汉-、-乔治老大-、-脏猪-——数得出来的统统有。一流摔跤手每年可以赚上十万、二十万。咱们先慢慢让你这位老弟暖身。教他些擒拿法,传授他一些窍。啊,我打赌他三、两下就会成为大明星——让大家都赚大钱。
丹恩看着我,说:你认为呢,阿甘?
我不知道,我说,我有点想回老家做养虾的小买卖。
养虾!麦克说。啊,小伙子,干这个赚的钱起码是养虾的五十倍!不必一辈子干这一行——只要花几年工夫,然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银行里存着钱,养一窝金鸡呐。
或许我还是问问珍妮的意思。我说。
听着,麦克说,我这可是给你毕生难逢的机会。你不要,尽管说,我立刻走人。
不,不。丹恩说。接着他扭头对我说,听我说,阿甘,这家伙说的话不无道理。我是说,要不然你怎么赚到足够的钱去养虾?
这样吧,麦克说,你甚至可以带着你这位朋友一起。他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只要你想退出,随时可以。你怎么说?
我想了一下。听起来是满不错,但通常这种事都有诈。话虽如此,我还是张开了我的大嘴巴,说出那个要命的字:好。
呃,就这样我成了职业摔跤手。麦克在印第安那波里市中心的一家健身院有间办公室,每天丹恩和我都会搭巴士到那儿,学习摔跤的正确方法。
简单说,职业摔跤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任何人应该都不会受伤,但是,看起来像会受伤。
他们教我各种技术——反扼颈、穿裆胯、原地抱摔、打桩、锁肘等等的。还有,他们还教丹恩如何对裁判吼叫,造成混乱局面。
珍妮对于摔跤这件事并不热衷,因为她说我会受伤,我说不会有人受伤,因为这玩意是唬人的,她说:那有什么意思?这话问得好,我找不出合理的回答,但是,我还是盼望能替我们赚些钱。
一天,他们教我一招叫腹压的技术,我要凌空压到对方身上,但是,对方会在最后-刹那身滚身滚开。可是不知怎的,我老是搞砸它,有两、三次对方来不及翻开我已压在他身上。最后,麦克走进场中,说:老天,阿甘——你是白痴不成!你这样子会伤到别人,你奇壮如牛啊!
我就说:对——我是白痴。麦克说:什么意思?丹恩就把麦克叫过去解释了一番,麦克说:老天爷!你在说笑不成?丹恩摇头。麦克看看我,耸耸肩说: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吧。
总之,大约过了一小时,麦克从他的办公室跑到场中。
我想到了!他吼道。
想到什么?丹恩问。
他的绰号!我们得给阿甘一个摔胶的绰号。我刚才想到了。
是什么?丹恩说-
笨瓜-!麦克说。咱们给他穿条尿布,戴上一顶圆椎纸帽。观众一定爱死了!
丹恩想了想。难说,他说,我不太喜欢。听起来你好像想拿他耍宝。
这只是给观众看的。麦克说,他得有个绰号。所有大明星都有绰号。还有什么绰号比-笨瓜-更好!
叫他-外星人-如何?丹恩说。这比较恰当。他可以戴一顶塑胶头盔,插上些天线。
已经有个家伙叫-外星人-了。麦克说。
我还是不喜欢,丹恩说。他看看我,问,你认为呢,阿甘?
我才不在乎。我说。
晤,事情就是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之后,我终于以摔跤手的身份初试啼声。大赛前——天,麦克带着一盒尿片和黑色圆推纸帽走进健身院。他说明日中午会再来,载我们去参加我的第一场摔跤赛,地点是蒙夕。
那天晚上,珍妮回家之后,我进卧房穿上尿片和圆锥帽,回到客厅。丹恩正坐在他的小车上看电视,珍妮在看书。我进门时,他俩都抬起目光。
阿甘,这是什么玩意?珍妮说。
这是他的戏服。丹恩说。
这么打扮把你弄成个傻瓜似的。她说。
咱们这么想嘛,丹恩说,就好比他在演戏什么的。
他还是像傻瓜,珍妮说。真不相信!你竟然让他打扮成这副样子去公共场所?
都为了赚钱呐,丹恩说。他们还有个家伙绰号-蔬菜-,拿萝卜叶当裤吊带,还弄个挖空的西瓜戴在他头上,再挖两个眼洞让他看见。还有个家伙叫-神仙-,背上装了一对翅膀,还拿着一根仙杖。那家伙大概有二百磅——你该瞧瞧他那模样。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珍妮说,这件事我一点也不喜欢。阿甘,你去脱下它。
我回到卧房脱下戏服。也许珍妮说得对,我心想——可是男人总得赚钱谋生。何况,这打扮比明晚我的摔跤对手好得多。他自称屎蛋,穿了件紧身衣,衣服上画得像一团粪。天知道他身上会是什么气味。
(未完待续)
([美]温斯顿·葛鲁姆著,于而彦译,重庆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