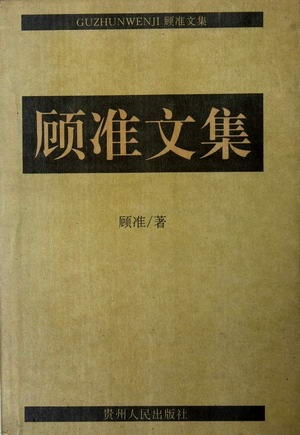顾准(一九一五——一九七四)早年是一个共产党干部,一九五二——一九七四年间因为独立见解,受到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在贫病交加、众叛亲离中死去。这种个人苦难给了他思索民族苦难的契机,其间,他完成了“从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以中国社会的实践,否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合理性,写下了三十五万字的译、著,是为《顾准文集》。
其中,他的译文《希腊的僭主政治》尤其是他为此译文所写的跋文《僭主政治与民主》,对理解中国现实社会,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十九世纪的英国学者格罗托(一七九四——一八七一年)在他的《希腊史》中曾经提到,“僭主政治”是传统王政过渡到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个人专政的形态。所谓僭主政治,是指“无限制的个人专政”。“大约在公元前六八零——六七零年之间,在西库翁建立了俄尔塔格拉的僭主专政。而值得注意的是,科林斯、西库翁、墨加拉这三个城市,在同世纪中经历了类似的政体变迁。三个城市都有一个僭主上台执政,俄尔塔格拉在西库翁,库普塞罗斯在科林斯,特阿格尼斯在墨加拉。这种政体变迁同时发生于希腊世界的不同部份,大陆的、岛屿的、殖民的不同城邦。在公元前六五零——五零零年间,许多城邦中不同的僭主和僭主王朝代兴亡交替。而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年中间,虽然还有僭主,但却越来越罕见,因为政治焦点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民主政治的兴起。”
格罗托所分析的希腊僭主政治,其实也存在于中国先秦的西周、东周、春秋时代,如“共伯和”废周厉王,后来的“陪臣执国命”等等。“僭主”概念也适用于现代政治史,如英国克伦威尔、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俄国列宁-斯大林、意大利墨索里尼、西班牙佛朗哥、中国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北韩金日成、北越胡志明、土耳其凯末尔、伊朗霍梅尼、埃及纳赛尔……所以,它对中国政治形态的深入研讨,具有意义。
在古代希腊,僭主的权力具有以下几种起源:
一、作为行政长官,逐渐变质,不守承诺,窃取足够的权势,不再理睬推选他出山的人们对他的限制。如现代的拿破仑、袁世凯。
二、作为煽动家,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以无权者的斗士的名义挺身而出,博得人民的好感,受到拥戴,推翻旧政权,自立为僭主。如现代的希特勒、霍梅尼。
三、甚至用不着受拥戴的藉口,干脆运用一支军队,夺取政权。如现代的列宁-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推动性的政治权威人物中,洪秀全只算得一个传统型人物,尽管他运用了基督教的旗号。而清廷里掌蹄带尾的人士除了光绪,都缺乏现代意义。在分析其余诸位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时,可以发现:曾国藩、李鸿章,是权臣而不是僭主,袁世凯先是权臣后是僭主,蒋介石、毛泽东是僭主,邓小平则始终是以权臣而非僭主的身份在操纵中国政治,因为他始终不是国家主席,又不是共产党的领袖,后来甚至不是军队的统帅,但却莫名其妙地控制着中共政权的独裁权力。
可以说,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权臣,是为袁世凯那样的半僭主进而为蒋介石、毛泽东那样的僭主,登上历史舞台而做准备,而邓小平这样始终名不正、言不顺的“以权臣之名而行僭主之实”的人,则可能恰恰在不自觉地为中国一百年以来僭主时代,悄悄画上句号。环顾当今中国,政治领袖的权臣化,不仅体现在邓小平身上,而且体现在邓小平任命的所谓“第三代核心”身上,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其实只是一批技术官僚,而完全不能构成任何意义的政治权威。结果,政治领袖的权臣化,注定中国社会即将进入无政府状态,所谓第三代集体领导核心,将被历史证明,仅仅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无僭主的权臣集团。
在表面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的僭主化,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僭主过程有相似之处:英国革命产生克伦威尔,法国革命产生拿破仑,俄国革命产生列宁-斯大林,德国革命产生希特勒,意大利革命产生墨索里尼,日本革命产生军部的独裁……事实似乎表明,绝大多数传统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产生至少一个独裁的僭主,甚至被他的追随者集团称为“国父”。
中国似乎也是如此。但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革命因而漫长得多,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至少四个“国家”: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袁世凯的中华帝国、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邓小平,由于他的“改革”已经完全推翻了毛泽东体制,变化幅度并不小于蒋介石对北洋政府的改革,所以该不该把它算作又一个“国家”,另当别论。其中,至少产生了三位“国父”: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虽然,袁世凯被称作卖国贼,不被任何人承认,而毛泽东紧跟斯大林,避免国父的提法,但显然他觉得自己比国父还大,简直是秦始皇再世。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完成国家统一,完成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国的僭主,却是实现国家分裂,把大一统的世界帝国,变成一个分裂的、不伦不类的区域性国家。
其它国家的僭主,都是在实现民族统一的过程中,发动对外战争,跻身列强行列,即使像俄国这样的破产国家,也只是经历短短几年的内战,而后就在世界大战中成为世界霸权。但中国,却在经历了三十八年内战和外侵(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后,又经历四十多年迄今不息的内乱,没有稳定的制度(即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假的,远远无法比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性),没有社会规范(传统规范被消灭,共产党规范也宣告失败),没有是非,没有信用,没有法律。僭主政治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被证明没有完成它在其它社会中的“统一→强盛→扩张”等应急功能,反而造成“分裂→衰弱→内乱”,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如此反差的奥秘究竟何在?
迄今探讨中国近代命运的著名学者,大都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民族差别:
西方社会是从一千年来的欧洲小邦政治向大规模的近代世界政治过渡。如十九世纪欧洲的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如英、法、德、意、西等等),都经历由更小规模的政治实体(如意大利的大群城邦、德国数百小国、法国英国的贵族领地)几百年演化而来的历史。及至二十世纪,在这些中等国家的两翼,又兴起了世界规模的超级大国:俄、美。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受两翼边缘制约的战略形势就更明显,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现代世界的国际秩序。这种演变终于使得欧洲的小邦日益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获得新的世界地位。欧洲文明内部正日益趋同,而这一趋向又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壮大同步。这耐人寻味。这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是道德理想或经济制度,而且是世界型政治的伴生物——正如民族主义是中等规模列强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封建主义则是小邦政治的意识形态。
在列强秩序走向超级大国的进程中(这离世界帝国还有一步之遥),出现“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吼叫,不是偶然的。它是要求冲破国界,完成超国家的政治组合。
但反观中国,不仅置身这一世界主流之外,而且成为它的受害者,因为中国近代以前的大一统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反。现代欧洲文明走向趋同,中国恰恰在这同化压力下趋于分裂,这意味着一种退化,美其名曰“再生”也可以:中国早在秦汉时代已形成自身的“天下一统”,自身趋同运动早在两千年就完成了。在古代技术所能允许的条件下,中国形成自己的世界型文化。
战国七雄,近似欧洲的八国列强:春秋兼并战争,近似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最后统一于秦,与当今欧洲文明正经历的世界趋同,又很近似。所以孙中山曾经断言,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甚至无政府主义理论,尽管他和康有为相似,是以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去“发掘”古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脉络,如《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等观念。尽管那是对西汉盛世的即类似于罗马屋大维“黄金时代”等世界帝国的理想描述,而不是基于对古代中国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反感。
秦汉以来的中华世界帝国这一政治结构,绵延两千年颠扑不破,作为全球历史上时间跨度仅次于埃及的政治奇迹,在空间上大于埃及数十倍,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值得我们引为自豪。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经历却一再说明,如继续坚持这一世界主义的结构,中华民族就无法立足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列强并争的国际社会,更遑论在其中成为发达国家!
不少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指出,中国传统应该对中共“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失败负责,他们列举马克思-恩格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义的分析,指出所有对资本主义发展感到忧虑的社会力量其中包括封建力量,联合起来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这分析即使适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但比对中共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试验却南辕北辙。因为中共以其国际主义的背景全力毁坏中国传统,有系统地消灭后者来扩张自己。他们用西方的真理向民族开刀,造成中国人的无数悲剧。中国共产党僭主政治的病态,迫使我们超越它,只有超越它,中国的现代化才有机会。如果超越共产党僭主专政?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最好搞联邦制。这就为深入有关问题提供了议题。联邦制实际上是以西式的法治为保障的。使联邦得以联而不散或联而不僵的,显然是法律。是既高于任何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又高于各邦利益之上的契约。宪法至高无上,所以各邦法律不能和联邦法律相悖。是什么纽带与轴心使联邦系统得以制度化地运转?是由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独立的司法机构,是法院型的社会仲裁者。据此分析,由于中国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联邦制并不可行。若行之,则难免走向宏观失控。
再如,还有一种探讨也不是为积极的:
在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政体中,初分可以有三大类:(一)君主立宪制,如英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等;(二)共和联邦制,如西德、美国等;(三)民主中央集权制,如法国、意大利等。其中,第三类是较不稳定的。而在这三类政体中,君主立宪制又是最接近中国传统政体的,再加上日本试行君主立宪政体(“近代天皇制”)的成功,所以从康有为以来的思想家们,多有在中国确立立宪君主的善良的愿望。他们希望,以此中和之轴去防止来自两方面的危险:(1)传统的专制君主所推行的违背民意的政策;(2)失去控制的暴民所引出的僭主政治。这确是一条改良的渐进之路,比突变之途较少破坏与风险。
其实,统治权有分离的思想,早在先秦时代“王霸论”的论争中就已被感觉到了。先秦思想家们区分王霸尽管多从统治权和道义性上着眼,但还是不自觉地总结了西周诸王的间接统治与春秋战国诸王们的直接统治。王道,无非就是以西周封建制为代表的那种间接统治,这种政治秩序的象征性颇为强,藉助于“礼”以为社会精神的轴。霸道,无非就是封建制崩解之际的实力政策代表的那种直接统治,这种政治秩序已很少象征性,主要以“刑”为治国的杠杆。平实说来,这“刑”与现代社会的规则性“法治”相去太远,它主要是霸主们意志的表现,而“礼”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法,是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的社会秩序的规则。间接统治,也就是规则的统治、象征性的秩序、非个人的社会裁判制。
这就是“王道”的原始意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理解这层古义,有助于超越失轴状态。
但中国专制君主的传统模式毕竟未能脱胎出立宪君主的革新模式,中国终于一步步走上了全方位革命的大破大立之路。这是因为,现代君主立宪的基础是法治,其君主不过是稳定民心的摆设,减小社会内耗的缓冲阀。君主立宪的实质仍是宪政,是宪法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意味着,即使君主本身也得受制于宪法。在君主制模式中,君主与宪法互为表里,两者的共生关系便合成了社会主轴。在此,“君”不过是“宪”的人格化,犹如裁判员是游戏规则的人格化一样。“宪”是高于一切个人意志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则高于党派利益、高于政府职能、高于国家元首。正如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皇权高于一切,君主立宪社会是法律高于一切。所以它实际上还是一种法制社会。法律的判断是终极性的,不可逾越的,甚至国王与执法者自身都不能免受法律的审判。正因为法律是社会的契约,宪法本身也就可以通过程序化的、技术性很强的方式来讨论、表决,直到予以修正。用这种方式使之充分体现社会意志,使之在法律的框架以内不断损益,臻至完善。
显然,现代中国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所以君主立宪之路便是不通的。总起来说,中国社会的失轴状态,是个悬而未决的大文化问题。建轴需要各种条件的齐备,仅有单项的准备(即便是达到了“突破”、“先进”的程度也是枉然)是不行的。而在这种条件中,思想上的明晰和理解,则为至要者。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事,正在使这些条件趋于成熟。
中国今天所面临民族目标和社会任务实际上很是简明,也是贯穿中国近代丝毫未变的问题:富国健民,在列强缔造的国际环境下保护我们的种族、发展我们的文化。而要确实做到,我们必须认清中国形势与欧洲、日本是何等不同。甚至这决定了我们改造社会的具体做法,可能与他们恰巧相反。中国的这一特点,造成中国现代化事业两难,但不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扭转中国历史,为此,我们必须准备迎接一种新型的政治权威观念。
它将在扬弃僭主政治的历史性遗产的过程中,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
《顾准文集》比较失败的地方,是对韩非子等法家人物的评论有失公允。这大概是激于义愤,激于对毛泽东之流“批儒评法”运动的荒谬性而发。在那样特殊的背景下,顾准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是可以谅解的。
还有,他过于强调西方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而忽略“东方存在”如基督教精神运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压力、甚至蒙古人的武装入侵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他的思想不失敏锐、深刻,但是历史的视野不够。这不能不归咎于那个时代的通病。但他的气节却令人肃然起敬。无论如何,他是中国大陆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年间的文化大黑暗时代中,一位以传世之作来揭露共产党僭主专政的政权本质的学者,是中国的罕见脊梁。他在众叛亲离的孤独中呕心沥血,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写下了不屈不挠的见证。□
(《顾准文集》,顾准遗著,陈敏之编,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版)
(《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