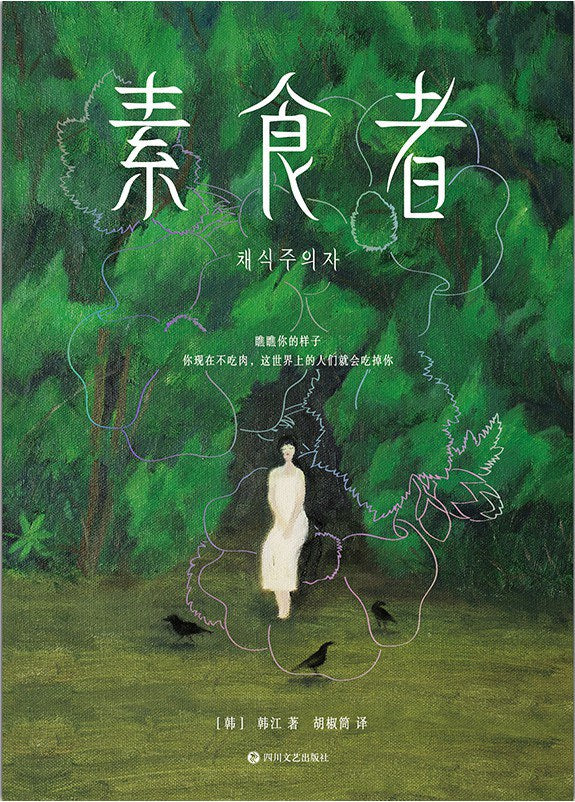J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总是把“Take it easy”当口头禅挂在嘴边的他,今天看起来有些忐忑不安。
“我好紧张。”
他一边给J泡咖啡,一边又在脑海里脱光了J的衣服。感觉很好,跟她很相配。
J看过前天下午拍摄的影片后兴奋不已。
“太难以置信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啊!这种影片怎么可能出自前辈之手?其实,我一直觉得前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啊,对不起……”
J的眼神和声音洋溢着平时不曾表露的好感。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怎么说好呢……前辈好像被巨人一手抓起,丢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瞧瞧这些色彩!”
虽然年轻的J特有的感受和浮夸的表达令他感到反感,但J说的一点没错。当然,以前他也能感受到色彩的美感,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感受到无数种色彩。这就好像色彩充斥着他的身体,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不受控制地从他的体内爆发了出来。一股非常强烈的感觉,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经验。
他曾经觉得自己很阴郁。他很阴郁,总是躲在黑暗里。他此时经历的缤纷色彩是过去那个黑白世界里所不存在的,虽然那个世界美丽而宁静,但他却再也回不去了。他似乎永远失去了那种宁静所带来的幸福,不过他无暇感受失落,因为忍受眼下这个激烈世界所制造出的刺激和痛苦就足以让他筋疲力尽了。
在J的鼓励之下,他终于面红耳赤地说出了酝酿已久的话。当他拿出舞蹈演出的小册子和素描本恳请他成为男模特时,J顿时感到不知所措起来。“为什么是我呢?不是有很多专业的模特和戏剧演员吗……”“你的身材好,过于完美的身材不适合,你刚刚好。”“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跟这个女人一起摆出这些姿势?我不行!”
他哀求、诱惑,甚至威胁J,想方设法希望他能答应下来。
“没有人知道的,因为不会露脸。难道你不想见见这个女人吗?这也会给你的创作带来灵感的。”
说要考虑一晚的J,隔天一早便打来了同意的电话。然而,J并不知道他真正想拍的是他们做爱的场面。
“……她怎么还不来?”
J望着窗外问道。即使J不问,此时的他也正感到坐立难安。他等在工作室里,因为她说自己能找到这里,所以没有去地铁站接她。
“是啊,不然我出去看看。”
就在他拿起夹克站起身时,传来了有人敲打半透明的玻璃门的声音。
“啊,终于来了。”
J放下咖啡杯。
她穿着跟那天一样的牛仔裤,但换了一件厚实的黑毛衣。可能是刚洗过头,没有染过色的乌黑秀发还湿漉漉的。她先看到他,然后看到J后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她摸着自己的头发说:
“我很小心地洗了头……生怕洗掉脖子上的花。”
J笑了笑。也许是看到她的朴素外表,所以不再紧张了。
“脱衣服吧。”一
“我吗?”
J瞪大了眼睛。
“她已经都画好了,只剩下你了。”
J面带尴尬的笑容转过身去,脱下了衣服。
“内裤也要脱。”
J迟疑了片刻后,脱下了内裤和袜子。跟自己预想的一样,J身上既没有肌肉也没有赘肉,除了从肚脐到大腿根长满了茂密的阴毛,全身的皮肤都很白皙光滑。面对J的身体,他的嫉妒之心油然而生。
跟那天一样,他让J趴下,然后从颈部开始作画。这次他选择的是青绿色系。他用大画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朵朵像是随风摇摆、纷纷凋零的淡紫色绣球花。
“翻身躺过来吧。”
接着他以J的性器为中心,画了一朵如同鲜血般的巨大红花。她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把摄像机里尚未用完的带子换成了新的,然后回头对她说:
“脱衣服吧。”
她脱掉衣服。虽然光线不像那天明亮,但画在她两个乳房间的金色花朵依然绚烂夺目。与J形成对比的是,她显得泰然自若,仿佛在说“赤身裸体比穿衣服更自然”。竖起膝盖坐在床垫上的J,因看得着迷而僵住了表情。
虽然他没有下达指示,但她却主动走到了J的身边。她像是模仿J的坐姿一样,竖膝坐在了白床垫上。那张无言的面孔与灿烂的肉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接下来怎么做?”
J问道。
出于不管怎样都要控制住局面的压力使然,J依旧红着脸。
“让她坐在你的膝盖上。”
J不知道她是他的小姨子,他像称呼陌生人一样称呼她。接下来,他拿起摄像机走到他们身边。当她坐在J的膝盖上时,他低声说道:
“拉近一点。”
J用颤抖的手拉过她的肩膀。
“你一次也没做过吗?发挥点演技吧,哪怕摸一下她的胸也好啊。”
J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这时,她缓缓地转过身,面对J坐了下来。她用一只手搂住J的脖子,另一只手抚摩起了画在J胸前的红花。房间里只能听到三个人的呼吸声。不知过了多久,她像是事先看过他的素描本一样,跟鸟儿互相爱抚似的把脖子贴靠在了J的脖子上。
“好,非常好。”
他从不同角度捕捉着同一个场面,最终找到了最佳角度。
“很好……继续,就像现在这样躺下去吧。”
她温柔地推着J的胸口,让他躺在了床垫上,然后伸出双手,抚摩起了J身上一直延伸到小腹的红色花瓣。他拿着摄像机来到她背后,捕捉着她背上开满的紫色花朵,以及随着她的肢体动作而晃动的胎记。他心想,就是这样,如果能再进一步的话……
她缓缓地前倾趴了下去,乳房贴在了J的胸口上。她的臀部悬在半空,他立刻转移到侧面捕捉他们的身体。她像猫一样弓起的背脊与J的肚脐之间空出了距离,她缓缓起身,笔直地坐在J的小腹上。这时,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不可以……我是说也许……”
他轮流看了看她和J。
“……也许可以假戏真做?”
她的表情毫无动摇,但J却像被开水烫到了似的一把推开了她,说:
“什么?你是要拍黄片?”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做也行。但如果能自然地……”
“我不拍了。”
J站起身来。
“等一下,我不会再提出那种要求了,按现在做的就可以了。”
他一把抓住J的肩膀。也许是太用力了,J“啊”的一声,推开了他的手。
“喂……不要这样嘛。”
听到他急促且恳切的口吻,J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下来。
“我能理解……毕竟我也是搞创作的。但怎么能这样呢?她是谁?人家不像是妓女,就算是妓女也不能做这种事啊!”
“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对不起!”
虽然J又坐回到床垫上,但刚才散发出的既兴奋又性感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J像受到处罚似的板着脸,抱着她躺在了床垫上,这时,她闭上了双眼。他看出了假若刚才J同意的话,她是会欣然接受的。
“那就这样动一下身体吧。”
J很不情愿地缓慢地前后移动着身体。他看到她的脚蜷缩得厉害,双手紧紧地搂着J的背。她的身体栩栩如生、热情似火,这足以抵消J无动于衷的反应。对J而言,这样的姿势是痛苦难耐的。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捕捉下了自己想要的画面。
“现在可以了吧?”
J问道。此时的J连额头都红了,但这不是因为兴奋,而是觉得尴尬难堪。
“最后一次……绝对是最后一次。”
“够了,真的够了。在丑态百出以前赶快结束吧。我充分得到了灵感,也明白了那些色情演员的感受。真是够悲惨的。”
J不顾他的挽留,甩开他的手,穿起了衣服。他咬紧牙关望着自己的作品,只见那些尚未凋零的花朵都被单色的衬衫掩盖住了。
“……我不是不理解,所以你也不要骂我是个猥琐的家伙。我今天才知道自己比想象中还要保守。虽然出于好奇心答应了做这件事,但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也意味着我还有没开窍的地方……总之,我需要时间。对不起了,前辈。”
J的言语里带着真情实感,他多少受到了伤害。J用眼神跟他道别后,礼貌性地看了一眼站在窗边的她,然后便匆匆离开了。
“对不起。”
当J的车发出嘈杂的引擎声开出院子时,他向穿上毛衣的她道了歉。她没有回应,但就在她套上牛仔裤,拉锁拉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朝着虚空扑哧笑了一下。
“笑什么?”
“下面都湿了……”
他像是挨了谁一拳似的呆望着她。她一脸为难的表情弓着腰站在那里。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手里还拿着摄像机。他放下摄像机,大步朝J离开的门口走去,锁上了门。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反锁了一下。接着他以近似跑步的速度冲向她,一把搂着她倒在了床垫上。
当他把她的牛仔裤拉到膝盖处时,她开口说道:
“不行。”
她不光是嘴上拒绝,还用力推开了他,然后起身提上了裤子。他仰头看着她拉上拉锁、扣紧扣子。他站起来靠近她,把她那尚留有热气的身体推向墙边。他强吻她的嘴唇,并试图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就在这时,她再次用力地推开了他。
“为什么不行?因为我是你姐夫吗?”
“跟那没关系。”
“你不是说那里湿了吗?”
“……”
“你喜欢上那家伙了?”
“不是,因为花……”
“花?”
瞬间,她的脸变得苍白,咬红的下唇微微地在颤抖。她一字一句地说:
“我想做……从来没有这么想做过。是他身上的花……是那些花让我无法抵挡,仅此而已。”
她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玄关走去,他注视着她的背影,跟着朝正在穿运动鞋的她喊道:
“那……”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近似于一种悲鸣。
“如果我身上画了花,到时你就会接受我吗?”
她转身愣愣地看着他。她的眼神仿佛在说,当然了,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啊。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到时候……也可以拍下来吗?”
她笑了。那是朦胧的,似乎什么都可以接受的,像是根本没有必要问的,抑或是在安静地嘲笑着什么的笑容。
死掉该有多好。
死掉该有多好。
那就去死吧。
死掉算了。
紧握着方向盘的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流下眼泪,几次想要打开雨刷后才发现原来模糊不清的不是车窗,而是自己的眼睛。他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会不断闪现像咒语一样的话:“死掉该有多好。”然而体内仿佛存在着另一个人在不停地回答说:“那就去死吧。”如同两个人交流的对话,竟像咒语一样让浑身颤抖的他平静了下来。但这是为什么,他也不得而知。
他觉得胸口,不,是全身都在燃烧,于是打开两侧的车窗。在夜风和车辆的轰鸣声中,他驱车驰骋在被黑暗笼罩的公路上。颤抖从双手开始蔓延至全身,就连牙齿也出现了撞击。他感受着浑身的颤抖,脚踩油门。当他看到时速表时,不禁错愕不已,立刻用抽搐的手指揉了揉眼睛。
从公寓正门走出来的P穿着黑色的连衣裙,外面披着一件白色的开衫。P与他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恋爱后,跟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小学同学结了婚。多亏了丈夫在经济上的支持,她才能兼顾好家庭与工作。P已经办过数次个展,而且在江南的收藏家之间也颇受欢迎。正因为这样,P周围总是环绕着嫉妒和闲话。
P很快认出了他那辆前后打着闪灯的车。他拉下车窗喊道:
“上车!”
“这里很多人认识我,连警卫都知道我是谁。你这个时间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先上车,我有话跟你说。”
P只好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好久不见。突然找你,对不起啊。”
“是啊,好久不见。这一点也不像你,难道是想我了,所以突然过来?”
他焦躁地捋了一把刘海说: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什么事?”
“说来话长,去你工作室说吧,工作室离这儿不远吧?”
“走路五分钟……到底什么事啊?”
P是个急性子,她提高嗓门急着想问清楚是什么事,她那女强人特有的活力曾令他倍感压力,但现在都不以为意了,甚至还开始欣赏起了她这一点。他突然萌生出想要拥抱P的冲动,但这仅仅是出于往日的旧情使然。此时,他浑身上下充斥着对刚刚送回家的小姨子的欲望,那欲望正如同浇了石油的火焰一样熊熊燃烧着。他转身离开时,对她说:
“你在家等我,我马上回来。”之后,他便驾车赶到了这里。他必须找一个可以画出令自己满意的花的、熟悉自己身体的、能够帮自己解决燃眉之急的人。
“幸好我老公今天加夜班,万一让他误会了多不好。”
P一边打开工作室的灯,一边说道。
“刚才你说的素描本给我看看。”
P接过素描本,表情严肃地翻看着。
“……有点意思。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样运用色彩。不过……”
P摸着下巴继续说道:
“不过,这不像是你的风格。这个作品真的能发表吗?你的绰号可是‘五月的神父’啊。那种有思想意识的神父,刚正不阿的圣职者的形象……我以前也是喜欢你这一点。”
P隔着角质框眼镜盯着他。
“难道如今你也要转型了吗?但这尺度也太大了吧?当然,我也没资格说三道四。”
他不想跟P争论什么,于是不声不响地脱起了衣服。P略感惊讶,但她很快放弃了似的在调色板上挤好颜料。P一边挑选画笔一边说:
“这都多久没见过你的身体了。”
幸好P没有笑出来。但就算P不带着任何用意地笑了,他也会认为那是残酷的嘲笑。
P非常用心地在他身上缓慢作着画。画笔很凉,笔尖碰触皮肤的触感很痒,但又很像麻酥酥的、执拗的、很有效果的爱抚。
“我尽量避免画出自己的风格。你也知道,我很喜欢花,也画了很多花……你画的那些花很有张力,我会尽力模仿出那种感觉。”
当P说“差不多画好了”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时分。
“谢谢。”
由于长时间裸露着身体,他打着寒战。
“如果有镜子的话,很想让你看一下,但这里没有镜子。”
他低头看着起满鸡皮疙瘩的胸口、腹部和大腿,那里画着一朵巨大的红花。
“很满意,比我画得好。”
“不知道后面你满不满意,你的画好像都把重点放在了背部。”
“肯定满意,我相信你。”
“虽然我尽力想要模仿你的画,但还是难免有些自己的味道。”
“太感谢你了。”
P这才露出笑容。
“其实,刚才你脱下衣服的时候,我有点兴奋……”
“然后呢?”
他急忙穿上衣服,心不在焉地问道。穿上夹克后,这才稍稍暖和了些,但身体还是很僵硬。
“现在不知怎么……”
“怎么了?”
“看着满身是花的你,让人觉得很心疼……觉得你好可怜。之前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P走到他面前,帮他系上了最后一颗衬衫扣子。
“吻我一下吧,谁叫你大半夜把人家找出来的。”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P便吻了下去。过去数百次的亲吻回忆覆盖在他的双唇上,他觉得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不知道这是因为回忆还是友谊,抑或是对于自己即将跨越疆界的恐惧。
因为时间已晚,所以他没有按门铃,而是轻轻地敲了两下门。他等不及她来开门,于是转了一下把手。正如预料中的那样,门开了。
他走进昏暗的房间,路灯的光亮从阳台的玻璃窗照射进来,借助那点光亮可以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他还是碰到了鞋柜。
“……你睡了吗?”
他把提在双手和挎在双肩上的摄像设备放在玄关,然后脱下皮鞋朝床垫的方向走去。刚迈出几步,他便看到黑暗中一个模糊的人影坐了起来。虽然四下昏暗,但还是可以看到她赤裸着身体。她站起身向他走来。
“开灯吗?”
他的声音略显嘶哑。只听她低声回答说:
“……我闻到了味道,那是颜料的味道。”
他发出呻吟声,扑向了她。当下他把照明、拍摄都忘在了脑后,喷涌而出的冲动彻底吞噬了他。
他发出咆哮声,将她扑倒在床垫上。黑暗中,他肆意亲吻着她的嘴唇和鼻子,一只手揉捏着她的乳房,另一只手解着自己的衬衫扣子。剩下最后两颗扣子时,他干脆用力一把扯了下来。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如同禽兽般的喘息和怪异的呻吟。当他意识到这些声音出自自己时,不禁感到全身战栗,因为他觉得只有女人才会呻吟。
他抚摩着她那被夜色笼罩的脸,轻声说了一句:
“对不起。”但她没有回应,而是淡定地反问道:
“可以开灯吗?”
“……为什么?”
“我想看清楚。”
她起身朝开关走去。显然她没有因这场不到五分钟的性爱而感到疲惫。
室内突然亮了,他用双手蒙住眼睛,稍后适应了光线以后才放下手。他看到站在墙边的她,那满身绽放的花朵依然很美丽。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褶皱下垂的小腹,于是立刻用手遮挡了起来。
“不要遮……很好,花瓣像是有了皱纹。”
她缓缓走向他,弯下身来。她像对J那样,伸出手指抚摩起了他胸前的花朵。
“等一下。”
他起身走到玄关,将三脚架调到最低,然后把摄像机固定在了上面。接着,他抬起床垫竖放在了阳台上,再把带来的白床单铺在了地上。最后,他安装了一盏像是M工作室那样的照明灯。
“躺下来好吗?”
她躺下后,他估摸着两个人身体缠绵在一起的位置,调整好摄像机的方向。
她修长的身体躺在耀眼的照明下,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身体叠在她的身体上。此时,他们的身体是否会像她和J一样,展现出叠放在一起的花朵呢?又或者是花朵、禽兽和人类结合成一体呢?
每换一种体位,他都会调整摄像机的位置。当拍摄到J拒绝的后背体位时,他用特写镜头长时间地拍摄下她的臀部。
所有的一切近乎完美,正如他期待的那样。在她的胎记之上,他身上的红花反复地绽放和收缩,他浑身战栗。这是世上最丑陋的,也是最美丽的画面,是一种可怕的结合。
永远,这一切永远……当他无法承受满足感而浑身颤抖时,她哭了出来。在近似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她一直紧闭着双眼,即使嘴唇不停地微微抖动,她也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她仅凭身体向他传达出敏感的喜悦。是时候结束了。他坐起身来,抱着她靠近摄像机,伸手摸索着开关关掉了电源。
这幅画面在无法抵达高潮与尽头的状况下持续进行着,在沉默中、在欢乐里、永远地……但拍摄只能到此为止。她的哭声渐渐平息后,他让她躺了下来。最后几分钟的激情使得她的牙齿相互碰撞,发出嘶哑且刺耳的尖叫声。当她气喘吁吁地喊“停……”时,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安静了。
在墨蓝的晨光里,他长时间注视着她的臀部。
“真想把它移到我的舌头上。”
“……什么?”
“这块胎记。”
她略感惊讶,转身看向他。
“这块胎记怎么还会留在屁股上呢?”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大家都这样,但有一天去澡堂才发现……只有我身上有。”
他用搂着她的腰的手抚摩着那块胎记,他希望与她分享那块如同烙印般的斑点。他想要吞噬它、融化它,让它流淌在自己的血管里。
“……我是不是再也不会做梦了?”
她以若有若无的声音喃喃自语着。
“梦?啊,脸……对了,你说过梦里的脸。”
他感受着睡意缓缓来袭,接着问道:
“什么脸?谁的脸?”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熟悉的脸,有时候是陌生的脸,也有布满血迹的脸……有时候还会梦到腐败溃烂的脸。”
他勉强抬起沉重的眼皮望着她的双眼,只见她那丝毫不显疲惫的眼中闪烁着微弱的光。
“我以为是因为肉。”
她说道。
“我以为不吃肉,那些脸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并没有。”
他很想集中精神听她讲话,但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地缓缓闭了起来。
“所以……我终于知道了。那都是我肚子里的脸,都是从我肚子里浮现出来的脸。”
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犹如安眠曲一样,把他推入了深不见底的睡眠中。
“现在不害怕了……再也不会害怕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她还在睡着。
阳光明媚。她的头发就跟动物的鬃毛一样凌乱,褶皱的床单包裹着她的下体。满屋子充斥着她的体味,那是一股如同新生儿般的乳臭味,刺鼻的酸味里还夹杂着既甜又令人作呕的腥味。
不知道几点了。他从丢在地上的夹克口袋里掏出手机,已经下午一点了。他从早上六点多一直睡到现在,整整死睡了七个小时。他先穿好裤子,然后整理起了照明灯和三脚架,但摄像机不见了。他记得拍摄结束后,为了防止摄像机摔在地上,特地移到了玄关处,可是现在却不见了。
他心想,也许是她早上起来放在了其他的地方,于是转身走向厨房。就在他转身来到洗碗槽时,看到了有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那是六厘米录像带。就在他诧异地捡起录像带回过头时,突然发现餐桌上趴着一个女人。那是他的妻子。
她手里握着手机,用包袱裹着的餐盒放在一边。显示屏开着的摄像机掉在餐桌下面。妻子明明听到了他靠近的声音,但还是一动不动。
“老……”
眼前的状况令人难以置信,他感到一阵眩晕:
“老婆。”
妻子这才抬起头,站了起来。但他很快便意识到,她没有要向自己走来,而是在阻止自己靠前。妻子静静地开口说道:
“我一直联系不到英惠……上班前过来看一眼,正好今天拌了几样素菜。”
她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但却极力保持着冷静地做出辩解。他知道,妻子只有在极力想要隐藏情绪时,才会这样放慢语速,发出低沉且微微颤抖的声音。
“……我看门没锁,直接进来了。看到满身都是颜料的英惠觉得很奇怪……那时你的脸朝着墙,盖着被子,所以我没有认出来。”
妻子用握着手机的手捋了一下头发,她的双手正在剧烈地颤抖。
“我以为英惠交了新的男朋友,看到她身上画着那些东西,我还以为她又发作了。我本想一走了之的……可转念一想,我应该保护她,也想看看是怎样的一个男人……我看到玄关那里放着的摄像机很眼熟,照你之前教我的方法把带子倒了过去……”
妻子一字一句冷静地说着。他可以感受到妻子拿出了所有的勇气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看到了里面的你。”
她眼里充斥着难以形容的冲击、恐惧和绝望,但面部的表情却显得异常麻木。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裸露的上身让妻子感到厌恶,于是手忙脚乱地找起了衬衫。
他捡起丢在浴室门口的衬衫,边套上袖子边说: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知道你很难理解……”
她突然提高嗓门打断了他的话。
“我叫了救护车。”
“什么?”
妻子的脸色煞白,为了躲避想要靠近自己的他,往后退了几步。
“你和英惠,你们都需要治疗。”
他用了几十秒的时间才搞清楚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你是要送我进精神病院?”
这时,床垫那头传来了沙沙作响的声音。他和妻子都屏住了呼吸,只见一丝不挂的英惠拽开床单站起身来。他看到两行泪从妻子的眼中流了出来。
“你这个混蛋!”
妻子强忍着眼泪,压低嗓音喃喃地说:
“你居然对精神恍惚的英惠……对那样的她……”
妻子湿润的嘴唇不停地哆嗦着。
英惠这才意识到姐姐来了,她一脸茫然地望着他们。那是毫无情感流露的空洞眼神,他第一次觉得她的眼睛跟孩子一样,那是一双只有孩子才可能拥有的、蕴含着一切,但同时又清空了所有的眼睛。不,或许那是在成为孩子以前,未曾接纳过任何事物的眼睛。
英惠缓缓地转过身,朝阳台走去。她打开拉门,顿时一股冷风灌进了屋子。他看着她那块淡绿色的胎记,上面还留有如同树液干涸般的痕迹。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世间所有的风霜雨雪,刹那间变成了老树枯柴,哪怕是当下死去,自己也无所畏惧了。
她把发出闪闪金黄色的胸部探过阳台的栏杆,跟着张开布满橘黄色花瓣的双腿,恰似在与阳光和风交媾。他听到渐渐由远及近的救护车的警笛声、邻里的惊叫和叹息声、孩子的叫喊声,以及赶来围观的人们聚集在巷口的嘈杂声。几个人急促的脚步声正回荡在走廊的楼梯里。
此时,如果奔向阳台越过她依靠着的栏杆,应该可以一飞冲天,从三楼掉下去的话,头骨会摔得粉碎。他可以做到,也只有这样才能干净地解决问题。但他仍然站在原地,像是被钉在了那里一样。他在这仿似人生最初也是最后的瞬间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如同炽焰的肉体,那是比他在夜里拍下的任何画面都要夺目耀眼的肉体。
(胎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