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劼《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与历史成因》
有些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之外的评论毛泽东的著述,虽然不乏独到的见解,或者揭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但我觉得它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作者在执笔展开论述前就已将毛泽东设定为一个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的恶棍和流氓,似乎就算毛泽东放个屁都能从中嗅出邪恶的意味来。以这样的视角所展现的毛泽东发迹史,基本就成了他坑蒙拐骗、不择手段往高处爬的历史,同时这只老狐狸周围的同志和敌人们都显得十足的单纯和低智。
 就算毛泽东再罪孽滔天,研究者也不应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学。李劼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与历史成因》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评述毛泽东的论文,作者着重于从历史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毛泽东现象的成因,展现了毛泽东是怎样逐渐成为中共党魁并修炼成毛太祖的。
就算毛泽东再罪孽滔天,研究者也不应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学。李劼的《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与历史成因》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评述毛泽东的论文,作者着重于从历史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毛泽东现象的成因,展现了毛泽东是怎样逐渐成为中共党魁并修炼成毛太祖的。
李劼以“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谜语开篇。在早期共产党内周恩来所握有的势力和资源远高于毛泽东,但最终前者却对后者俯首称臣,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让贤,为毛泽东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还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们后来几十年的相处看,那种君臣地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李劼认为,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是由他内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所决定的。
 李劼指出了毛泽东所具有的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与许多中共领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未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这种把握全局的能力在当时党内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以自己那超强的话语能力把所思所想生动形象地灌输给他的同志们,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那种不是真理也要煞有介事地装成真理的气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的这种话语能力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很雷人,雷得他那些大部分属于毫无文化的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同志们身心亢奋、血脉沸腾、山呼万岁,最后雷遍全国百姓。这显然是抽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哲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也是我当年被迫学习毛泽东理论课后最深切的感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李劼指出了毛泽东所具有的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与许多中共领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一种宏观视野,连同因此而来的战略眼光,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重要的是他对形势从未失去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毛泽东这种把握全局的能力在当时党内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以自己那超强的话语能力把所思所想生动形象地灌输给他的同志们,那种强词夺理的本事,那种不是真理也要煞有介事地装成真理的气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毛泽东的这种话语能力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就是很雷人,雷得他那些大部分属于毫无文化的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同志们身心亢奋、血脉沸腾、山呼万岁,最后雷遍全国百姓。这显然是抽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哲学所无法达到的效果,也是我当年被迫学习毛泽东理论课后最深切的感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最初无意于做什么缔造时代的伟人,他只是投民众所好诚挚而充满激情地做一个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流氓。他若在西方讲他的毛语大约会被当做神经病,而在中国,我们会忍不住暗暗惊叹,这哥们太实在太生猛了!如李劼所言,毛泽东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如果说马列主义是一个软件的话,毛泽东就是这个外来软件汉化版的缔造者,以简单粗暴的话语形式很神奇而神经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这个烂到骨子里的系统内顺畅的兼容。这一点,周恩来是做不到的,用李劼的话说,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文化。
毛泽东最初无意于做什么缔造时代的伟人,他只是投民众所好诚挚而充满激情地做一个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流氓。他若在西方讲他的毛语大约会被当做神经病,而在中国,我们会忍不住暗暗惊叹,这哥们太实在太生猛了!如李劼所言,毛泽东最大的成功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把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如果说马列主义是一个软件的话,毛泽东就是这个外来软件汉化版的缔造者,以简单粗暴的话语形式很神奇而神经地实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这个烂到骨子里的系统内顺畅的兼容。这一点,周恩来是做不到的,用李劼的话说,儒雅的周恩来比起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显得很没文化。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这种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主要源于他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深切了解。这种了解也许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养,更关键的是个人阅历、人生遭际以及敏锐而深厚的洞察力,民国乱世具有这种能力并能予以系统话语表述的至少有四个人: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和毛泽东。前两者学识渊博、坚守学术,在此不赘述。鲁迅和毛泽东的共同点除了他们都对中国人的那点卑贱小九九了然于胸外,还有他们同时又都缺失西方近现代宪政民主意识的觉悟和训练。他们的不同点在于,鲁迅就像他所自白的“孺子牛”一样辛劳、忧愤、刚毅和倔强,他清楚中国的本质性症结所在,但他却寻不到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出路,只能越活越纠结,或者说是越活越拧巴,拧巴到最后就是那一个都不饶恕的临终遗言;毛泽东则不会傻得让自己纠结,他很想得开,他深谙搞不过就加入其中的混世之道,在发觉自己年轻时代的纯真理想难有市场后,他适时转向最终跑到井冈山落草。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就是个提着脑袋出来混的,混得下去混出名堂才是王道!
 让曾怀有理想的毛泽东搞不过最终加入其中的,便是李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或者说是国民劣根性。与一般民众和他的同志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得心应手地利用其让自己做大。李劼说,毛泽东的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只是他走上历史舞台的表层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
让曾怀有理想的毛泽东搞不过最终加入其中的,便是李劼所言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或者说是国民劣根性。与一般民众和他的同志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得心应手地利用其让自己做大。李劼说,毛泽东的宏观能力和话语能力只是他走上历史舞台的表层政治文化原因,毛泽东的崛起更为重要的人文原因在于命运意义上的、经由精英人物的选择、从而在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所获得的一致认同。如果说政治文化原因是意识层面上的历史选择,那么文化心理原因则是其民族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历史效应。毛泽东的走上神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包括中共领袖们在内的内心认同,这种认同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不如说更是下意识的顶礼膜拜。
接下来李劼通过分析共产党从“五四党”到“山党”的嬗变和毛泽东从曾国藩向洪秀全的转向,揭示了这种民族集体无意识在那个变革时代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性负面影响。作者从历史文化心理的角度追根溯源至《山海经》中中国最为始源的文化精神,具体而言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文景观和对弱者的权利和心声的关切。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后儒家教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知识分子大多流于趋炎附势,《山海经》中所展现的文化精神已处于边缘地位,甚至是难觅踪迹。直至帝制时代后期,《红楼梦》对这种上古的文化精神作出了现代性的阐释。李劼说,《红楼梦》不在于时间向度上的历史进取,不在于如何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在于确立起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一种不以历史意志更不以任何帝王的权力为转移的文化标高。
 在肯定了这种正面的文化标高后,李劼概括出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中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种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种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再有一种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折腰的历史循环。李劼指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并不是他后来做成的,他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这种戏剧性转变,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中的历史成因。
在肯定了这种正面的文化标高后,李劼概括出中国晚近文化历史格局中三种不同的人文景观:一种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人文精神标高,一种是从曾国藩到变法维新、到清末民初的革命志士、再到“五四”文化领袖及其早期共产党人的前仆后继,再有一种便是从洪秀全到孙中山、最后到毛泽东的江湖草莽们为江山美人折腰的历史循环。李劼指出,毛泽东早年向往的并不是他后来做成的,他早年向往的那种曾国藩式的文化英雄和经世楷模,与他后来做成的洪秀全式的草班帝王截然相反。毛泽东在文化选择上的这种戏剧性转变,既有他个人的心理成因,也有整个文化嬗变中的历史成因。
毛泽东父亲的专断和暴虐管教使他自小便有对强权压制的反抗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养成以暴易暴的与他父亲一样的专断暴力意识。毛泽东的父亲对他的性格和意识的这种影响,我想只有有过类似成长经历的人才能切实理解。随着父亲的逐渐老去和儿子的长大成人,父子间的紧张关系大多会在脉脉的血缘亲情中逐渐消弭,但已经在儿子心中酿成的心理创伤和阴影却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毛泽东在雄踞延安甚至坐镇北京后,一提到他的父亲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足见得父亲对他的心理伤害和扭曲之深。纵使如此,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算得上是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他虔敬地抄写曾国藩日记,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中高喊“陈君万岁”,呼吁湖南联省自治。
 的确,谁年轻时没点纯洁而臭屁的小理想?谁会一开始就想做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但是,当怀揣理想的润之同学无限憧憬地奔赴北京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个陌生而稚嫩的湖南后生,并未如预想的般受到北大新文化运动大佬们热情地待见。理想轰然倒塌,可以想象毛泽东的失望之情。“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迷茫的毛泽东抑郁南归,像只没头苍蝇到处乱撞。但毛泽东不是个容易犯拧巴的人,当他在家乡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草莽造反、江湖暴动,这是曾国藩日记之外《水浒传》里的东西,貌似很有前途!此时毛泽东终于豁然开朗,把自己拧了回来,从湘江畔的励精图治拧到了梁山上的聚众造反!李劼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挑战。
的确,谁年轻时没点纯洁而臭屁的小理想?谁会一开始就想做个杀人如麻的暴君?但是,当怀揣理想的润之同学无限憧憬地奔赴北京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个陌生而稚嫩的湖南后生,并未如预想的般受到北大新文化运动大佬们热情地待见。理想轰然倒塌,可以想象毛泽东的失望之情。“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迷茫的毛泽东抑郁南归,像只没头苍蝇到处乱撞。但毛泽东不是个容易犯拧巴的人,当他在家乡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草莽造反、江湖暴动,这是曾国藩日记之外《水浒传》里的东西,貌似很有前途!此时毛泽东终于豁然开朗,把自己拧了回来,从湘江畔的励精图治拧到了梁山上的聚众造反!李劼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其说是向陈独秀式的革命领袖的进言,不如说是向胡适那样的士绅和知识分子的挑战。
曾经的理想青年毛泽东就这样很识时务地变坏了。李劼评述,虽然毛泽东从曾国藩立场转向洪秀全立场是轻而易举且顺理成章的,但要让整个历史环境从当年曾国藩平定洪秀全暴乱之后的改良格局,重新转化为适合于洪秀全式的人物江湖作乱的以暴易暴环境,却不是当时的毛泽东力所能及的,这样的历史转折是作为“先行者”的孙中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给后来的毛泽东提供的。李劼矛头所指并非1911年的那场革命,而是革命后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身上所时时流露出的帝王情结。为了实现自己潜意识里一统天下、中央集权的帝王梦,孙中山联合苏联人乱搞,疏远试图营建现代议会的宋教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与倡导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反目。孙中山与后来的毛泽东是一路货,但他却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宏观视野和话语能力,只能把中国越搞越糟,使当时的历史环境彻底陷入暴力循环当中,间接成全了毛泽东的横空出世,而进一步推波助澜的是蒋介石。孙中山的北伐,仅仅给毛泽东创造了走向暴力革命的历史条件,蒋介石的大屠杀才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进一步带来了历史合理性。蒋介石大屠杀的愚昧在于,本来手中就没有多少文化资源,结果还要以血洗陈独秀的“五四”式中国共产党来清算由孙中山勾结苏联暴动专家所犯下的历史罪孽。蒋介石的大屠杀在把历史合理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源奉送的毛泽东这样的暴力革命者的同时,也把陈独秀那样的文化领袖逼出了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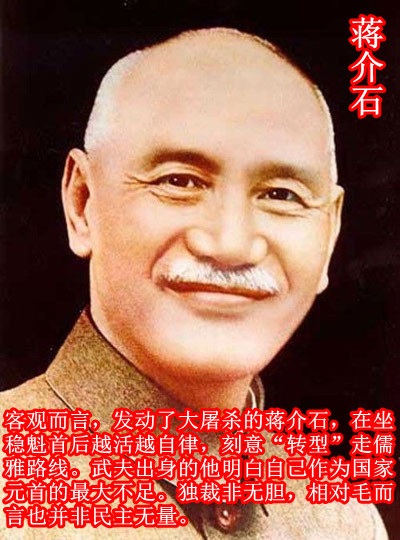 让我们回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臭脾气但一直反对暴力武装的陈独秀,最终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黯然退场;而已落草多年的毛泽东,在人生追求上早已完成了从曾国藩向洪秀全的转向;在陈独秀退场后暂时处于中共高层核心地位的周恩来则惟苏联是从,眼看要把这个团伙断送掉。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是明确意识到还只是潜意识里的感觉,跟着那个既能玩转敌人也能玩转自己人还能玩转国际友人的老毛干,大约已成为党内多数头脑还算清醒的革命同志们的共识。于是,历史那看似偶然的转折早已顺理成章、顺水推舟,毛泽东也就顺手牵了羊,成为团伙老大,中共最终从陈独秀式的“五四”党彻底转变为了毛氏“山党”。毛泽东这一身混世的本事,也使这个人精在成为党魁后最终修炼成了毛太祖。
让我们回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臭脾气但一直反对暴力武装的陈独秀,最终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黯然退场;而已落草多年的毛泽东,在人生追求上早已完成了从曾国藩向洪秀全的转向;在陈独秀退场后暂时处于中共高层核心地位的周恩来则惟苏联是从,眼看要把这个团伙断送掉。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是明确意识到还只是潜意识里的感觉,跟着那个既能玩转敌人也能玩转自己人还能玩转国际友人的老毛干,大约已成为党内多数头脑还算清醒的革命同志们的共识。于是,历史那看似偶然的转折早已顺理成章、顺水推舟,毛泽东也就顺手牵了羊,成为团伙老大,中共最终从陈独秀式的“五四”党彻底转变为了毛氏“山党”。毛泽东这一身混世的本事,也使这个人精在成为党魁后最终修炼成了毛太祖。
李劼说,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国人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里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从演义小说里流露出的阴暗心理以及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上的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毛泽东的白话文演变成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语文化,也即所谓毛泽东思想。
鲁迅和毛泽东都发现这种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中国是如此的有市场,这可谓是作为一场社会启蒙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失败之处,它未能在全社会培育起宪政民主的话语体系。寻不到切实的出路,鲁迅只能一个都不饶恕,毛泽东则既然搞不过就加入其中,与其同流合污,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在历史舞台上兴风作浪了一把。不知做成毛太祖后的晚年毛泽东,在其乐融融地与人斗并逐渐成为孤家寡人之余,是否还会想起他年轻时的理想?我觉得他是会想起的,这个一辈子都在反传统的人恰恰是最传统的那种中国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用类似于毛语的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未尝不也是一种悲剧。
我曾在毛泽东死去三十周年时写下一首短诗:
三十载并未朽掉你的面容
许多人又在对你浓妆艳抹
浸淫在老树新花的妖艳中
虚幻的面容离了你的肉身
一些人固执地拿来照妖镜
镜像却模糊在尘埃纷飞中
三十载朽不掉你的面容
却可掩埋几代人的苦难
你的肉身终该订棺入土
你的面容也将瞬间朽烂
随同你的王朝灰飞烟灭
朝阳升起在尘埃落定中
“你的肉身终该订棺入土”句,在草稿中本是“你的肉身终该入土为安”,旋即感觉对毛泽东用“入土为安”这个词实在太客气,遂很不客气地改作“你的肉身终该水淹土埋”,后又觉得对一具尸体这么说显得不地道,最终改成描述性的“订棺入土”。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我忍不住慨叹,天安门广场上的那具僵尸最好还是入土为安了吧,我想这也是他自己所奢望的。死了的都明明白白地“安”了,活着的也能和和谐谐地安稳下来,这大约是最好的结局与开始。应当朽烂与湮灭的不止是毛泽东和他的王朝,更应当包括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一个毛泽东和这个已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民族专制大王朝。“朝阳升起在尘埃落定中”,错失了一次次机遇、经历了无尽的苦难后,但愿如此。
2010年4月23日
原载《议报周刊》
《吾诗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