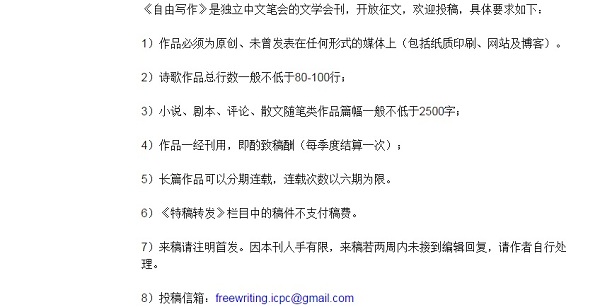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地处高寒的肃北县天气已经十分严寒,朔风呼啸,草木枯零。但是县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深挖五一六运动”。各单位天天开会,不是检查交代,就是揭发批判。十月三十一日,我们开了一上午会,下午清查小组成员和骨干分子开碰头会,我们则奉命写检查。我写了两行,不爱写了,便上杨才铭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找报纸看。
推门而入,却见老杨坐在床沿上发怔。他脸色苍白,我便问:“你不舒服么?”他转过头直勾勾地瞪我一眼,随即起身奔过去把门关死,慌慌张张地劈头问我:“出大事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了!你听说了么?”我莫名其妙,见他那紧张的样子,我不禁也紧张起来,连忙问:“啥事?啥大事?”他俩眼直僵僵地盯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身后很远的地方,如同梦呓似的幽幽地说:“事情太可怕了!太严重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不敢给你说,不敢说……”我好生奇怪,一再追问,他却死也不肯再吐一个字,只是眼睛发直,喃喃自语:“太可怕了……”见他如此卖关子,我心急火燎,恨不得扳开他的嘴把那重大事情掏出来;同时我脑子里飞旋:能发生什么事情让老杨如此大惊小怪?
(全文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