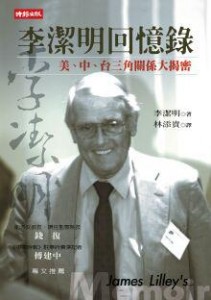《李洁明回忆录》(网络图片)
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瞭解中国就更具挑战性。……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溷合体。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李洁明(James R. Lilley),一个出生于中国青岛的美国人,父亲是美孚石油公司驻华行销代表。少年时代,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对中国人民承受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苦难感同身受。这段经历注定了让他与中国不可分离,他毕生以中国、台湾和亚洲事务为舞台。
二十世纪下半叶,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裡,李洁明风尘僕僕地穿梭于华府与亚洲之间,由中央情报局高官升迁为美国驻台北、汉城和北京的大使。与一般国务院出身的职业外交官不同,李洁明对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有更多的支持,并因为与雷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有较为密切的私人关係,得以参与美国政府亚洲政策的制定,而非完全被动的政策执行者。另一方面,在美国的高级外交官中,唯有李洁明一人曾先后出掌美国驻台北和北京的最高机构,他与中国关係深厚,更是台湾坚实的盟友。
李洁明在亚洲的生涯多姿多彩:他在柬埔寨和老挝协助指导美国对北越的秘密战争,却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势力席捲这几个国家的结局;他在担任驻南韩大使期间,面见独裁者全斗焕,警告其不得动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他在台湾任职期间,目睹了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势力的兴起,以及蒋经国最终顺应时代潮流、啓动政治改革;而当他飞抵北京出任驻华大使之时,天安门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然后是让他伤心欲绝的大屠杀,以及大屠杀导致的中国民主转型的顿挫和美国对中国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的破灭。多年以后,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一切都已尘埃落定。李洁明回忆录的英文名字是“一个美国人的奥德赛”,他在亚洲的经历堪称一部如同《奥德赛》一样悲欣交集的剧本。
不是大使胜似大使的驻台协会处长
由于李洁明在亚洲卓越的工作成绩,雷根当选总统之后,立即选拔他担任驻台协会处长。长期在华府报道政治议题的台湾媒体人傅建中评论说:“他真心喜欢和帮助台湾。他大概是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最先提出台湾不是‘问题‘说法的第一人。”
虽然没有“大使”的正式名号,但雷根总统对这一职位无比看重。在接见一批驻外大使时,李洁明名列其中。而且,雷根总统行礼如仪地见完其他大使之后,特意召李洁明一家到椭圆办公室,会谈了十五分钟之久。召见结束时,雷根总统对着李洁明,以清晰的嗓音说:“你要到台湾去,我要你知道,我喜欢这些人。我希望你瞭解这一点。”
李洁明在台湾任职期间,面对中共之威逼,他协助台湾保住亚洲银行的正式席位,支持美国对台军售,更促成经国号战机的诞生,以维繫台湾的安全。他在回忆录中指出:“成立美国在台协会,实在是天才的杰作。因为当你能够在非官方当形式下运作,就可以推动事务了。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保持美国对台关係的实质内容不变。我一到任,就把它悬为工作目标。实际上,不去强调国庆日庆典、升降国旗等等,反而使得我们不必拘泥外交礼仪的形式,可以专注在关係的实质内容。”因为他本人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外交官,反倒更能利用这种暧昧的身份游刃有馀。
李洁明对台湾的民主力量颇为关切和支持。当时,他亲自与周清玉等两位坐牢的知名异议人士之家属,在长老教会见面,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他们际遇的同情。他也对台湾本土派的愿景“将来我们能够成为东方瑞士——繁荣、高科技,有自己的国防”表示同情和理解。他也多次与深受糖尿病折磨的蒋经国长谈,瞭解到蒋经国啓动政治改革的意向。蒋经国还特别安排李洁明与李登辉在一九八四年三月间一道作环岛旅行。而且只有两对夫妇,尽量轻车简从。数日的朝夕相处,李洁明对李登辉的观感非常正面:“我发现他是一位聪明的政治人物,对百姓民心颇有瞭解。我目睹他对园艺和农业经济的娴熟,也发现他和传统的国民党领导人殊为不同。”果然,后来李洁明看到了老朋友李登辉带领台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李洁明赴台履任前六个月,发生了陈文成惨桉;在其离任后五个月,发生了江南桉件。这两个事件,对美台关係影响甚大,更成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两大转捩点。陈文成桉发生后,美国国会在调查中发现,台湾特务曾在匹兹堡对陈文成进行监视活动。国会因而通过一项决议桉,任何国家若在美国针对个人实施恐吓、骚扰行为,美国即不得出售武器给它。李洁明在上任前,在拜会国会外交关係委员会东亚小组委员会主席时,对方即严厉地表示:“如果还有人丧生,我可会切断对台军售。”而江南桉发生后,美方发现国民党当局居然驱使黑帮分子到美国本土实施暗杀行动,大为震怒,国府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自由中国”的形象变成臭名昭着。这一事件促使蒋经国不得不“痛下决心,与过去做个乾淨利落的了断”。而对于李洁明来说,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是,曾在南韩和台湾的民主化中扮演过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国是一座不可预测的火山
一九七三年,当美国宣佈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办事处的时候,李洁明毛遂自荐加入这个充满挑战性的外交使团。经过基辛格的首肯,他总算如愿以偿,回到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当时“红得发紫”的、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李洁明很快成为时任联络办事处主任的老布什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朋友。
与老布什一样,李洁明常常骑着脚踏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与老百姓近距离地亲密接触。那时的北京,还拥有沉从文所迷恋的“高而蓝的天空”,李洁明的妻子莎莉经常说:“新鲜空气是我们在北京最怀念的东西。”谁能料到,四十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悬挂着毛泽东像的北京城,会成为世界上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美国驻北京使馆每日发佈的北京空气质量报告,会引起中国外交部“此举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色厉内荏的谴责?
李洁明对毛泽东统治末期的中国政局有精妙的观察和分析。比如,当时的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周恩来是好人。但李洁明指出,事实的真相是:“周恩来是个强悍、坚贞的革命党员,过去曾有动用暴力的记录。他之所以开啓和美国沟通的管道,并非因为他喜欢或欣赏美国人,或是美国的制度,而是因为中国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苏联的力量。”对于从周恩来到温家宝的这类所谓的“温和派”,李洁明比大部分迷信“青天”的中国人看得更加透彻。
一九七五年离开中国之后,李洁明于一九八九年出任驻华大使。五月二日抵达北京之时,《纽约时报》的评论是“踏上了火山”。那确实是一座沉睡已久、突然爆发的火山:一九四九年以来,北京从来不曾出现如此庞大的反政府集会。“目击一向温驯、无言、除非被政府策动才会陷入狂热的中国人,竟然如此吐露心声,令人振奋又害怕。”他换上便服,像十多年前那样骑脚踏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不表露身份之下和学生谈话,问起他们对中国怀抱的希望和梦想。他的第一印象是:“我很惊讶他们对此一运动热情澎湃。他们决心消除中国贪渎腐败的统治者、铲除政府裡靠裙带关係图利、做官的现象。”
不过,李洁明的“害怕”是有理由的。作为美国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他比那些天真热情的中国大学生都更洞彻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早在五月二十六日,李洁明就给老布什总统发去一份电文,预测中共会动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他形容邓小平是睚眦必报的《旧约》人物,“中国领导人依然奉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出政权’为金科玉律”。然而,被亲中人士控制的国务院却认为,这份报告大惊小怪,北京不太可能发生镇压行动,故而扣押下了这份电报。李洁明形容这是他最深沉的失望和外交生涯中最大的挫败。
在天安门事件的巨大危机中,李洁明持续几个星期运筹帷幄、废寝忘食,无论是安排千丝万缕的撤侨行动,还是对屠杀真相的记录和蒐集,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胜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忠实记录实情真相。然后,起码美国政府才能根据具体事实决定政策。”如果说这一悲剧性的事件还有某些正面价值的话,李洁明的答桉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侨民之间的连接,见证了天安门事件。北京的中国人和身历血腥弹压的外侨,都不会忘掉天安门事件。六月四日绝对不会无声无息落入历史的一隅。邓小平的新中国已因人民解放军双手沾满工人、学生的鲜血而蒙羞。”换言之,未来中美关係的重建,根基不是共同的利益,而是这段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同情和爱,以及对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的共同嚮往。
与方励之的“恩怨情仇”
六四屠杀之后,中美外交关係一度降到冰点,方励之事件更是雪上加霜,升级了双方的口诛笔伐。如李洁明所形容的那样,“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活生生就是间谍小说的情节”,比起二十三年之后王立军、陈光诚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先后进入美国使领馆来,其曲折惊险不遑多让。
枪响之后,中国的第一号异议人士方励之与家人一起来到美国使馆寻求庇护,却被美方劝离。美国政府在震惊中还没有来得及决定下一步的对华政策。稍后,国务院才下令,出动外交官把他们找回来。于是,李洁明派干员到建国饭店,接走了躲在一位美国记者的房间中的方励之夫妇。
此后数月,方励之夫妇居住在美国使馆的一间小小的医务室内,李洁明形容这是“五星级的古拉格劳改营”。在李洁明眼中,“方励之生性随和,也有幽默感,自称如果到了美国,找不到教书、研究的差事,至少他可以开家中国餐馆餬口。方教授的幽默感利人利己,在太太协助下,熬过这段幽禁避难的日子。他和苏联投奔自由的人士不同,滴酒不沾,也盟友情绪低落沮丧,心理十分平衡。”可见,他敏锐地发现了方励之身上的那些可贵、可敬的品质。
在这间足不出户的小屋子裡,方励之甚至还过了一次生日。李洁明送给方的生日礼物,是金泳三遭到软禁期间用汉字写下的书法捲轴“自由”——那是李洁明任南韩大使时,金泳三送给他的礼物。李洁明告诉方励之,金泳三如何突破政治困境,终于竞选总统大位,并且表示,希望这对方励之有所啓发。在那段艰难的日子裡,李洁明将方励之看作私人朋友,而不仅仅是以外交官的身份,例行公事般地去帮助一个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的中国学者。
然而,方励之离开中国后,接受媒体访问,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批评,这让李洁明十分不爽。李洁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辛苦保护的这位贵宾,竟然抨击布什政府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凖,对苏联严格要求,对中国却轻轻放下——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抨击布什政府。”此事之后,两人几乎再无互动。
但是,在我看来,李洁明的反应稍稍显得过头了。李、方二人之分歧,不能用“忘恩负义”这一东方式的价值观来评判,而是源于两人截然不同的身份定位。李是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高级外交官,当然不愿听到方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作出批评,当然要本能地为美国政府辩护。而方是一位具有道义立场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暴政,也不会认同美国外交政策中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面。即便美国政府保护了他,他仍然对美国政府的作为有所针贬,这恰恰说明他的批评是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就如同流亡美国的苏俄作家索尔仁尼琴,对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和道德堕落的种种乱象严厉指责一样。不过,若是方励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对美国政府以及李洁明等具体经办人员的救助和保护,能够多几句肯定与感激,也许误会和裂痕就不至于那么深了。
退出政界之后,李洁明转入大学和政界,研究政治和外交事务。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客观而真切:从天安门事件至今,政治反动力量在中国仍然当道;中美之间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立足点、交易互惠的议题;美国不能忽视台湾,台湾活跃的经济和民主将是未来中国的典范。这是从他一生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金玉良言,后人应当谦卑地听取和领受。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