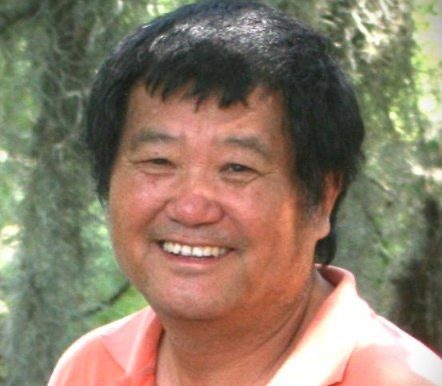布鲁耐克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是同行,谈得多,也了解的多。我喜欢他,因为在他的身上,我可以看到自己,以至中国人的许多弱点。应该说布鲁耐克是我赞赏的一种性格和人生。有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的生活态度,实是幸运。如果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这将是一个健康而有希望的社会。如此,人和人类还是有光明有意义的。
布鲁耐克不是一个特殊的人,而他好也好在他的普通。人类也好,社会也好,还是普通人的,他们是人类生活的主体。、健康的普通的人生是人类的意义所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世纪。思想、行径、生活。人都被挤到极端。人除了发疯找不到别的道路。中国一向是中庸的民族,而这一世纪也被逼到极端的尽头。真是上帝死了,各样的人便赶出来充当上帝。向前、向前、再向前。而我想,人退后一步或许更好——退到人正常的生活。这或不是真理,却是常识。
布鲁耐克的父亲是立陶宛人——波兰的几个重要诗人,密茨凯维支、米洛什都来自立陶宛,因此他算是波兰的少数民族。但布鲁耐克把自己当作波兰人,站在波兰的立场谈论世界、历史。只有当他隔于生活的具体事物时,他才划分和波兰的限线。比如他要到外交部去工作,他就不愿意去立陶宛,因为立陶宛人会把他当作波兰人,而波兰人亦把他当作立陶宛人,两边都不信任。他说我可以到驻立陶宛大使馆工作,但晋升不了大使,因为我是立陶宛人。他说这些事时,有些怅憾。我理解。我见他和立陶宛语教师用立陶宛语谈论的时候,更亲切些,像兄弟,但在平时,看不出他和波兰人的区别。
布鲁耐克不是民族主义者,电视台报导在德国一家土耳其人被杀,他非常气愤,“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杀人,还有孩子?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吗?”
我问他这样的事在波兰会发生吗?他说:“不会”。我相信,如果有,他也一定同样气愤,他不喜欢英国和德国,说他们是欧洲的的两个流氓,他认为英国没什么文化,但他始终不理解德国,“德国是很有文化的国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
当然,布鲁耐克亦反感俄国,他不能原谅俄国对波兰、立陶宛及其它斯拉夫民族的伤害。苏联的解体,他很高兴。但他亦很同情俄国人现在的生活,“怎么办,他们怎么生活?什么都没有。”
布鲁耐克反对社会主义,讨厌共产党,他说:“这是不好的制度,不给人们自由。它最坏的地方就是培养坏人,只有那些坏人可以作官生活得好。”他的话有些绝对,但大体如此。
布鲁耐克喜欢当警察,他说:“警察可以帮助人们做好事,惩治坏人。”他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公安部定期向全国公布的疑难刑事案,通过电视请求民众提供线索,每有这样的节目,他便停下谈话“对不起,我必须看这个节目”,他说:“我可以做一个好警察,可惜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好人不能做警察,现在我老了,什么都完了。”我想他说的是真的,他是行为的人,他的性格适于那一工作。无论是作军人还是做警察,他都会有作为,他有行为,正直,热爱公正的天份。
他毕业于华沙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可以找一份有实益的工作,像外交部,或报社、电台,但他不愿为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工作,于是他去了博物馆,管理东方文物。那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清冷、寂寞,没有实际的好处,他的性格去外交部、报社、电台更合适。他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傻?我的同学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于是他去了报社,以后他又退了,现在他长驻中国,写中国方面的文章,是中国问题专家(算是飞黄腾达了)。”“我没和他们合作,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他不是投机的人,自然捞不到需要投机的好处。
前年他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作汉语翻译,那里的风景很美,语言也很好听,但他很悲哀,他不能接受那个社会,“有钱的太有钱,住的像宫殿。但是没钱的太多,到处是住在街上的穷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食物,靠乞讨生活。”他每上街,即换一大袋零钱,挨个发放。他不满意这样的社会,我告诉他:“中国如果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功,就是固为中国的穷人太多,他们完全没法生活。”
我们都很悲哀,我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他说是“北欧”,实际上他还是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不能接受大多数人的贫穷和不幸,去年立陶宛大选举,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他很不满意,那时他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兼职——波兰一家电台对立陶宛的广播,他说他要利用他的工作来影响立陶宛,我最终不知道他对立陶宛说了什么。
布鲁耐克是热情的人,喜欢社会生活,他住在华沙,却是我的大学校委会的教师代表。系里有事,他总是帮着张罗,例如选择系主任,他会自动地帮助组织,发选票。这样的事在知识分子中,少有人愿意干,那日他跟我借了一件短半截袖子的西服,打着领带,穿着牛仔裤到大学生参加大学校长竟选投票,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赢了。为此事他和所长商议了多次,如果他们支持的人当选,那对我们部门大有好处,大学的教师生活很糟。
我问他:“学院为什么不做一点事情,赚些钱帮助教师”。他认真想想,说“可以”我说:“如果你是领导,你有办法改善教师的待遇吗?”他说:“有”,他确适合做领导,有公务热心,有能力,又为大家欢迎。人们有事愿意找他,将他做为朋友,他有原则,有性格,但通情达理——这像中国人。更主要的是他公正,但他没有当领导的欲望。他更热爱个人的自由,我在波兹南,有事即找他,办成办不成,我都愉快,他真心帮助你,替你设想,为你奔跑,这里没有所求,亦无对你的的怜悯施舍之感,他天生的热情,与人平等。
布鲁耐克精晓立陶宛语、波兰语、俄语。前两种均是他的母语,他的德语说得跟德国人一样好,他亦通英语,法语他能阅读。而中文是他的专业,他告诉我在他会的几门语言中,汉语是最差的。他说:“汉语真的太难,要学好得用一生的时间。”进大学,教师问学生为什么选择汉语专业,学生们做了回答,教师说:“可惜,没有一个人因为汉语是最难的语言而选择它“。
布鲁耐克告诉我,他选择学汉语真的是因为它最难,只是当时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学了十多年的汉语,到中国呆了一年,他从博物馆调到大学,即是因为可以去中国。布鲁耐克的汉语可讲、可读,一般应用没有问题,但难为汉语学者,他不像搞了十多年汉语专业,每提至此,他都有愧意。他不是学者类型的人,那个时代——中国于封闭中,汉语是一门死学问——远在欧洲研究汉语,确是难为他。我想他当初的选择是个错误,但当时,波兰也是“社会主义”,他又不愿同流合污,他能选择什么呢?选择汉语或许是个体面的逃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大多逃避于文化之中,谁曾想到以后的变化呢?如果是现在,他未必这样选择,这个问题布鲁耐克也许还没反省过。
像波兰大多数知识分子,布鲁耐克喜欢拉丁文化,在欧洲也就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化。谈起时总是充满赞叹,对之他有些自卑,他以为波兰文化不如它们,这也是波兰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他瞧不上英国文化,认为他们没有个人文化传统,他们也只是在政治上强悍,英语英语没有美感又生硬、又单调。德国有文化,但他不喜欢它的极端性。俄国,他只承认其文学,从普希金到二十世纪初,他大体把俄国作为一个非文明的野蛮国家。布鲁耐克尤其看不上美国文化,“那也是文化吗,他们完全没文化。”但他喜欢美国的黑人音乐,尤其喜欢他们的爵士乐,有时他来便带一盘爵士乐磁带,边听边摇晃,神采飞扬,他赞叹黑人,“他们真的有音乐天才”。
对现代文化,他大体是保守的,他不喜欢足球狂热,不喜欢成千上万人狂呼乱喊的流行音乐,还有各种的披头士、雅皮士、崩克……。他理解不了女权主义,同性恋“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这是谁发明出来的?”他反对妇女堕胎“为了自己五分钟的快乐,就把另一个生命杀死,为什么?只是五分钟的快乐。”我的爱人和他争辩,说:“美国现在也在修改法律,允许堕胎。”“那是美国,我不应该管他们,受他们的影响。”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堕胎是社会的一大问题,议会为之反复辨论,先是准许了,以后又推翻了,那一阵整个波兰为之争论纷纷。
布鲁耐克尊崇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世界第一名”。他翘起大姆指,他赞赏中国古代对文化的敬重及给予的崇高地位,古代中国是他理想文化圣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是他理想的文化楷模。但是对中国当代他甚是失望,他不满意中国的权力和社会,他说:“中国的文化在古代,而中国当代没有文化,也许台湾有,但我没有去过。”他在中国一年,大是失望,其最大的收获是进修了武术,他练了十多年的八卦、行意拳,到中国算是拜了真佛。他说:“中国的青年现在学习拳击,不学武术,真可惜。拳击怎么能跟武术比?”中国的开放使他最高兴的就是武术直接到了波兰,过去在波兰中国的武术只有日本、朝鲜或越南人教,另一个波兰汉语教师从中国带来了崔健的磁带,想在波兰介绍崔健。他听了带子对我说:“我要告诉你实话,他的歌真是不行,向西方学的,太简单,太低等,像中学生。波兰人不会有兴趣。”反之,他对中国古典音乐却很有兴致,我从中国带来了十盘中国古典和民间音乐,他均翻录了,他说:“很了不起,完全是东方的。那么安静,是另一个世界,欧洲没有这样的音乐和文化。”布鲁耐克颇有音乐天份,他的母系是一个音乐家庭,音乐是他的第一爱好,他遗憾他没有学音乐。
布鲁耐克很羡慕我认识繁体字,可以阅读旧书,“我退休之后再好好学汉语吧,也许八十岁我可以阅读古文。”他说:“中国当代最不好的就是改革了汉字,为什么要改,改了就没有中国文化了。”这是太复杂的问题,我无法应答。“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繁体字,你们一定要恢复”。他有时教学生写繁体字,但我知道他实际不认识多少。文字简化方便了现在,但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个看法倒是对的。
布鲁耐克不是文化专家,许多问题他未必深入想过,他的许多看法亦有偏颇,但他身上自然地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这就是对传统和文化的崇尚和尊重。他只有32岁,在西方这大概还是一个造反的年龄,波兰和西方不同大约即在这里,波兰在欧洲是受欺凌的弱民族,近两百年受制于异族。波兰在强凌之下能顽强地存在下来,唯依传统和文化,没这两点,波兰早即消亡了。文化属于弱者,人由于在自然界中的脆弱而创造了文化,文化是居所,是生命的秩序。
布鲁耐克尊崇文化,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清高不食烟火,他不要求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权,亦没有不谙世事的呆气,他是立于现实生活的人,不赞赏那种闭门不出隔绝于世的学问生活。他对当博士、教授没兴趣,虽然这对他不是困难的事,只需要时间,他的博士论文拖了六年,仍没写。“为什么要写?就为了一个学位吗?要真正地研究治学,需要一生的时间,什么也不做,而我不能这样。”他尊重真正的学者——例如我的邻居耶热,但他瞧下上图慕虚名,现代社会博士、教授往往转为虚名之事,他清楚真正的学者需要贡献一生,而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自谋生计的人,其不能要求社会特权,亦不能要求社会供养,他首先是一个于现实中自食其力的谋生者,在这上他不以为他和普通的工人有什么区别。他活得真实朴素,波兰变革,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都受到影响,许多知识分子对之抱怨,牢骚满腹,像是受害者。布鲁耐克对之不以为然,“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可以离开大学,为什么不?他们有别的工作,有办法赚钱。”
布鲁耐克对家庭,他是男人,是家长,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这是他做人的首要责任。他可以为之放弃知识学问,大学的工作,以至他的兴趣和爱好,但他不能为后者放弃前者,为了生活他去打零工作翻译,译文稿,他不断地找工作,有一阵他甚至准备离开大学,他为没有时间研究专业遗憾,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和不能,他首先是承负生存责任的人。去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且让他满意的兼职工作——华沙电台立陶宛语广播,二份工作,每月三百多美金,不是很多,但是够了。他说:“我不爱钱,但痛恨贫穷,贫穷使人丧失一切,但是一生只为钱,没意思,几百万,几千万……有什么用?”布鲁耐克没有汽车,亦不准备有,妻子——银行职员,两个孩子,还有岳母,五口人挤于一居室的住房,他的生活不是很好。
家庭是布鲁耐克生活的核心。32岁,两个孩子,有岳母,还有老父,他活得不轻松,他比他的年龄显得成熟,也显得苍老,他的妻子不漂亮,胖得异常,文化也不高。我去他家,他为之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夫妇,责任多于情感——或许这就是情感更深入更稳定之处,他们是尽责的夫妻、父母。他的岳母,一位善良的老人,虔诚的教徒,操管家务,家庭的中心是两个孩子,女儿7岁,儿子3岁。孩子是布鲁耐克的寄托和希望,他生活的主要意义。他每次到波兹南都要给孩子带回去礼物,节日或孩子的生日更是如此,他的生活不富裕,但孩子们的所需什么都不能缺少,他每日抽出时间陪伴孩子,或游戏,或教育。我去他家,他亦不耽搁,“对不起,现在我要陪女儿去滑冰”。谈到孩子,他便有些愉快、宽慰,他一直注意女儿的音乐教育,他觉得她有这个天份,今年她的女儿考入了华沙音乐小学——在波兰很不容易,他非常高兴,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为此事做了许多努力。明年他有机会到中国进修,但他不准备去了,因为他要辅导女儿音乐。他过去也曾有可能去新加坡、立陶宛,都是很好、待遇很高的工作,但他没有努力,他不能离开他的家庭,他不理解中国的两地分居,“这怎么可以?政府怎么可以这样?这还是家庭吗?”他瞧不起不负家庭责任的男人。“他们不负责任,为什么要结婚?要有家庭?”
布鲁耐克一米八十还要高一点,强筋强骨,大步地走来,大步地走去。他不卑不亢,说话沉稳,握手有力,两撇斯拉夫人的胡子使他显得老练。他热爱中国武术,每天练习,几乎可以算一个武术家,他批评波兰人不喜欢锻炼。布鲁耐克是天主教徒,但不虔诚,他有时去教堂,有时亦不去。他尊重上帝,但不把教会的事全当真。他喜欢和男人一起喝酒,开玩笑,谈政治,谈女人。喝多的时候,话多也兴奋,那时便显得年轻,大约这是解脱了家庭的束缚与责任,他能不断地开玩笑,使人们捧腹大笑,眼泪不止,他自己亦然。他最擅长的玩笑是关于家庭、婚姻、岳母的。想是他大有苦衷,以之消解,布鲁耐克喜欢女人,他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大学?大学总是有女孩子,她们围着你……啊……啊,你也可以……啊,……啊……”“我喜欢夏天,姑娘们穿的很少……”,我们大笑。布鲁耐克喜欢维夏——我们的年青同行,见了她就高兴得说不出话,走不动路。“啊,维夏……维夏……。”他们过去在复旦一起进修。我想,他们曾经可能是情人,我和他开玩笑:“干脆离婚,娶维夏吧,她还没男朋友。”“哼,结一次婚已经够傻的了,要维夏就更傻。”这不是心里话,但也是现实的人。他不拘小节,丢三拉四,亦不注意穿着。像许多波兰人一样,他办事没谱,说好的事情象是没有,约好我们一起和秘书谈话,我等了他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他的影子。下次我问他:“噢,我是坏人,我是不好的人,我完全忘记了。”他不断拍打自己的胞袋。我托他给华沙大学送去三篇论文,但他只给我带回来两篇,而且也拖了大半年,那一篇是没了,我两个月的工作。有时他下课忘时间,上课亦忘时间,待他想起赶去,学生早已走光了,“走吧,我们去喝酒吧,没有了学生。”一家公司请他去一趟印尼做贸易翻译,这是好事,他可以观光,亦可挣一笔钱,但他却在那里丢了他的相机和钱袋。他不断地告诉我:“啊,我要有新的工作了”,国防部、外交部、某大公司,某报社……,他说得兴奋,神秘,但终无踪影,唯到电台兼倒是实事。布鲁耐克是现实的人,但这些事又让人觉得他是孩子,人的确还是年青人。布鲁耐克是可爱的人,他身上的种种弱点都可以原谅,那是他的生动光亮之处。和他在一起你会真实,年轻,快活,健康。真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他有两点可贵的,一点是对中国人的,一点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不欠缺中庸和家庭责任感,但是中国人太老于世故,失去了人性的天真爽直热情,亦缺社会的正义与正直,是国家太大,还是我们的历史太老?中国的百姓向来是小民,没有社会权利,亦不能参预,连自身的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任其自生自更,社会对之没有公正,其自然也没有正义感。而中国的社会没有公正的原则,法律,社会生活也即异常残酷,人不极心竭力即不能存活,这即发展了中国人自私与世故——人与人斗,我不能谴责中国的历史的人,事物都有局限,但到了近代现代各种矛盾交激,人就变得越发猥琐,活不好了。倒了皇帝是好事,但一盘散沙即变成了一潭烂泥。中国人自得于老于世故,一人一条龙,但整个社会都不堪救要了,杀来砍去,小至阿Q革命,大致军阀混战。于是来了“救星”——共产主义宗教,志于世故无用了,玩世不恭也没用了,几亿人都被押上了祭坛,自私变成了献身,世故转为大脑白痴。真是大颠大倒,“大乱达于大治”,像是命定的轮回惩罚。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民众的自觉公义,那么就靠强暴维持,其程度恰成比例。我们谴责毛泽东,但其源正是中国社会的腐朽,中国人世故得已结不成社会。固此没有一般民众的正直与正义,即不能有稳定良好的社会,而不给民众权利不对负责,其社会公正感也无从建立,一个社会没有公正的法律、道义,那即谁也活不好——大多数人活不好,人群如同兽群,其结果不是暴乱就是暴政。我看欧洲各国,对他国他民不说,就其自身,一般民众是有一般的社会公正、正直、道义感的,没有暴徒当众抢劫强奸女教师,而人们观而不管(中国报纸报道)的事情。社会到了那一步,大体应该解散了——或自行崩溃。我观在外华人,志于世故,奸狡溜滑在国内如鱼戏水,到外便成了缩头缩脑,鬼鬼祟祟,对手不是依靠算计便能对付的了,其也只能欺负华人。反之那些简单些而有专长的人,如医生、科技人员活得倒好些,舒展些,也踏实。世故生产不出大米,做不了手术,世界的创造多出乎几分天真,李鸿章可谓志道,权谋纵横,左右逢源,以夷制夷,但其挡不住坚船利舰。世故是对社会的依附和利用,但人最终要靠自身的独立和能力。人大概没有了能力,不能自立便要算计了,但现代社会不买这份帐,否则西方社会便不会有志年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的权力结合相一,读书入仕,士是官僚的后备队伍。故此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权力,也渴望权力,这是传统,我没有道德与价值上的肯定与否定。近代中国巨变,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力的人格与精神却未培养起来。“五四”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人格唯新,形成一支传统,但有了抗战,新中国到五七年便一网打尽。之后便是知识分子全盘尽忠,这里虽有权力的强暴,但也确有自愿之成份。扬绛的小说《洗澡》,那些知识分子确没有持异见的,这里有人格的懦弱——不敢,由不敢而回避,也有文化变革中的盲目,也有缺少独立精神——个人人生观、社会观、哲学观,也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愚忠。比如那个想去卖花生米的教授,看到其工作生活有保障,且有地位,也就转而拥护了。现在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有各种控诉,但缺少严格的自我反省。由知识分子而言,其大约有两个欠缺,一是人生的独立,二是精神的独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至今没有学会自谋生存,也不能把自己降为一个善通的自食其力的谋生者。当然这有前题,就是社会允许,比如在奥斯维辛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中国有这个可能了,这要看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份能力和勇气,精神的独立就有个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哲学观,对事对物有个人之见解,不屈服不放弃,不为潮流、权力、政治、团体、他人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