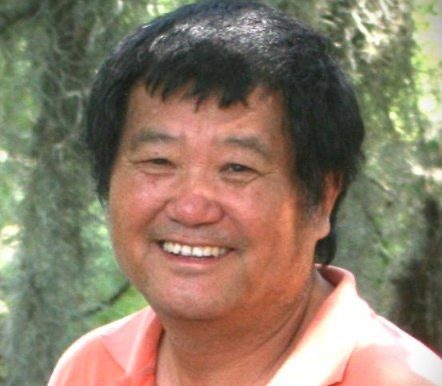我在华沙没有朋友,进入不了它的生活,而仅仅作观光,华沙确无太大的意思。老华沙已在二战中毁掉,新华沙是二战后的结果,据说是按照老华沙建造的。但连片的厂区,蜂拥叠起的居民住宅楼,并不是老华沙的景致。现在的华沙即没有西方现代都市的新奇变幻,也没有古都的肃穆庄重,那是一片五、六十年代的景象。初到华沙之感,类似我七十年代初头次到沈阳,混乱,嘈杂,烟雾腾腾。人们说波兰的文化不在华沙,如果仅就城市建筑,我以为然。与之相较,克拉克夫更像波兰的首都,教堂林立,古迹连连,确有国都之气。但是一座城市的构成,不仅由其建筑,亦包括其于民族的功能,人员的成分和生活。由后者看,华沙自然是波兰的中心,政治不必言,波兰重要的文化机构,优秀的艺术家,学者,作家,科学家多聚于华沙,因而华沙仍是波兰最重要的城市。但是我对于华沙的观感仅仅是它的街区与建筑(这就是旅游的坏处)。我不很喜欢这座城市。华沙让我怀念的一角是老城,背倚残缺的朱红色的城堡,眺望维斯瓦河,黄混的河水浩浩荡荡,对岸绿荫葱葱,圣•依奥拉娜教堂铜绿色的双塔刻入蓝空。而身旁的丁香树花团簇簇,潮湿的石阶凹凸不平,古墙的影子一直投在脚下。这里你看到了时间的韧带,它由古久之往昔伸向未来,像浩大的维斯瓦河,来于遥远驶于无限,横贯大地与晴空。
“过去”是一个向度,是对现实的平衡。在现实的纷纭变幻中,“过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它代表人的某些永恒的价值,而平衡现实对人的纷扰。人是需要一定的稳定的,即象人需要居所。在人类文化中,最高的荣誉总是留给时间过去——我说是时间的荣誉,这是人的明智。我并不相信过去比现在更好。一百年前,华沙的贫民窟比现在的水泥楼更好吗?前者的可怕近于地狱。当我们提及华沙古都时,并没有包括它们。但时间的过去正在于此,它不是历史,它只代表着人类于过去有价值有意义的部分——人的肯定经验。人做过,曾经做过。它是由现实淘洗的纯金,代表人永恒的原则和意义。如果说这是虚构,这则有经历的背景和根据。因此那“过去”是一种精神的光辉,它生于历史中人跋涉的足迹。由于人的缺陷和不幸,我们必须宽容地看待历史,尤其是珍重其可贵之处,那是人竭尽全力才做到的。以奉神的虔诚尊重那古老的文化,那意义是在承认我们的局限,而竭力奉守“人”的那点价值和意义。
华沙于二战中的焚毁,它的残酷是毁坏了波兰文化的过去,波兰民族的一个骄傲,一个古老的文化的象征消失了。华沙——波兰之都——切断了和它过去的联系,它没有了归宿。战后的华沙虽然是按战前的规模候复的,但是拷贝和真品毕竟不同。我站在华沙时感到脚下是废墟的沙漠。老华沙毁灭了,就象波兰国徽上的那只鹰鹫掉落了王冠。华沙保留了一些战争的残址,这是一片空白中的一角记忆,它延伸到战争,战前,华沙的往昔,维斯瓦河畔的华斯和夏娃(传说华斯和夏娃建造了华沙)尤其是四四年英勇的华沙起义,二十万人遭受屠杀。也许真正的华沙在这里——波兰的不幸和英勇,正义的失败和蛮横的胜利。也许于此才能真正理解华沙的意义。
我不愿意去华沙,一出车站就感到压抑和难过,每每感到一种文化被摧残和强占的野蛮。华沙车站在地下,它的头上是美国马瑞奥特(Marriott)旅馆水银大厦,三几十层,习习烁烁。出车站,斜对面又是华沙文化宫——战后苏联送予波兰的礼物,典型的俄国建筑,巨大无比,这是华沙,也是全波兰两座最大的建筑。其象征两个时代,战后苏联的强权和新到来的西方现代经济。我的朋友布鲁耐克说:“我真不喜欢它们,希望把它们送回去。”我理解他。对华沙来说,这是两个心理压迫,它蛮横地占有其文化心理。文化宫修得那么庞大,水银大厦那么闪烁,其意义在此。我有时替华沙人感到尴尬,在电视或像片中,有华沙,它们如果有过去,它们不会这么傲慢。在时间中没有事物可以胜利,最高的荣誉属于往昔。如果有一天波兰的首都迁至克拉科夫,我不会奇怪。是的,真得庆贺的是波兰还有克拉科夫——那才是波兰文化的象征。
朋友来信说,北京在变为沙漠。那情景我可以想象。北京文化上的荒废不是由现在开始的。其它不说,六十年代北京男女被动员去拆城墙,古城拆了,结果有了前三门大街的水泥住宅。当时那似乎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创举,人们弹冠相庆,五千年被压迫的人民有了骄傲。但没过二十年这即成了讽刺,而拆毁的古城却不能恢复了。中国人丢失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我们想过吗?华沙毁于异族的战火,但北京呢?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参加过中国文化的破坏,我们感到耻辱和忏悔了吗?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就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时间的向度。中国传统的时间一直是向后的,这是中国文化得以四千年延续的奥秘。这个奥秘的中心就是在每一个瞬间,它提供对自身的肯定,而抗拒外界的瓦解和风化。而这个世纪之后,中国的时间向度转向了未来,其结果是对未来的虚幻,及对自身的不断破坏——否定。中国也就是由此丧失了自己。从“五四”到新中国,到文革,这不奇怪,这仅仅是一个极端化的过程。丧失“过去”,陷于未来的盲目,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不单单是个人或其团体的道德之事。严格的说是没有“现在”的,在流动的时间中,永远也不能标刻下“现在”。“现在”是过去和未来的衔连的模糊的运动。在人指向未来——未知,人生命自然的向度——的时候,其必须以“过去”为相应的平衡。只有“过去”是人可以认定的存在,提供人以可靠的肯定和经验。“现在”——现实是赌博,未来是未知,既然这两点是人生存所无可避免的,那么人即须有一个“过去”和向度以之平衡,这是时间中人可能的理性和秩序。无此,人即被打散,受制于盲目的本能和混乱。这是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教训。中国不存在却罢。如果其存在,我看不到其除了恢复传统文化之外的选择可能。
华沙文化宫远比华沙维拉诺夫王宫和克拉科夫瓦威尔王宫辉煌。剔去时间的因素,华沙文化宫可能是波兰最雄伟的建筑。但是其不能成为波兰人文化的根据。苏联赠送这一庞大昂贵的礼物时,就包括对波兰文化征服与占有。因此,波兰民族的文化根据——由建筑而言,只能是郴斯道豪瓦(波兰宗教圣地),克拉科夫玛丽教堂,会此他们便丧失自身。这就象我在外越久,就越感到我是中国人。欧洲的文化有许多可贵之处,令我赞赏惊慕,但我终于明白其中有些即便我愿意也是无法学至的。这就是文化的命运。文化过于复杂,和人血肉相关,地理、气候、历史、语言、人种、体质及至饮食……都转化为文化。成为文化构成的潜在基因。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技术及至社会行为方式……。但是那最根本之处——与潜意识同在的——是学不到的,就像学不到人们的血液和发色。中国人在欧洲就是到了第三代也成不了欧洲人。于是我感到轻松,知道了我的位置和命运。我必须放弃那些愚蠢的企图,清清楚楚地划定脚下的界限。各种文化需要彼此理解、尊重、交流、吸收,但是不能取代。属于某一文化命运的,只能在此命运之中。它的命运就是你的命运,无从选择。一个人能接受这一命运,而珍重它,那就是荣誉。我踏实多了。
在中国,我们这一代在文化上大约是最糟的,彻底断了传统。我是中国人,但我的根在哪里?我亦感到我需要回过身来,我回我们那丧失的时间——“过去”,在现代世界尤其需要这一向度。那末“过去”及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魂灵就在屈子的行吟,杜工部的沉诵,曹雪芹的“虚幻”中,这是巴赫、毕加索、卢浮宫所不能取代的。在我的未来——我的后半生,我要做的,就是找回那毁坏丧失的“过去”。我的未来如果有一向源远的“过去”,那么我将完整——不论它多么微弱而陈旧。当然这也可能弄巧成拙,那就像现在的华沙,它是它“过去”勉强的拷贝。但人要遵从命运,命运如此,我无能逃避。
94年3月10~14日于波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