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成文宪法。由于美国在独立之前是一片特殊的“蛮荒之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北美的原住民没有发展出任何形式的现代政治体制,所以摆在美国建国初期这些天才政治家面前的是一张任由他们挥洒灵感的白纸,而非一幅只能修修补补的古老画作。换句话说,与许多国家不同,以美国宪法为基石的美国政治体系是“设计”而成而非“进化”而成的。在通过“进化”形成的宪政体系中,往往存在许多无法用理性加以解释的偶然事件,或是掌权者一时冲动下的命令;但在美国式的“设计”而成的宪政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由一群政治家组成的一个机构,及在此机构的框架中进行的理性的思考、辩论和投票却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宪法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反联邦党人为美国宪法作出的贡献是我们理解政治制度中反对者作用的一扇窗口。
二、反联邦党人及其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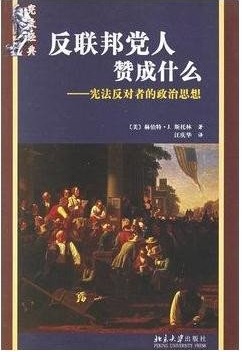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大陆会议在1777年通过了《邦联条例》。但在《邦联条例》生效之后,松散的邦联制度导致了很多问题,于是在1787年2月,国会通过《召开联邦制宪会议书》,认为“美国现行联邦条例有其缺点”,决定召开制宪会议修改《邦联条例》 。在制宪会议前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充满智慧的论战在会场内外都进行得无比激烈。长期以来,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更为人所关注。他们的论敌——反联邦党人的观点却长期被忽视,《反联邦党人文集》也在1981年才首次被出版。这本《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就是《反联邦党人文集》的编撰者——芝加哥大学的斯托林教授为《反联邦党人文集》所著的导论。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讨论了反联邦党人的宪政主张、联邦党人的回应以及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贡献。
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大陆会议在1777年通过了《邦联条例》。但在《邦联条例》生效之后,松散的邦联制度导致了很多问题,于是在1787年2月,国会通过《召开联邦制宪会议书》,认为“美国现行联邦条例有其缺点”,决定召开制宪会议修改《邦联条例》 。在制宪会议前后,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充满智慧的论战在会场内外都进行得无比激烈。长期以来,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以及他们的作品都更为人所关注。他们的论敌——反联邦党人的观点却长期被忽视,《反联邦党人文集》也在1981年才首次被出版。这本《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就是《反联邦党人文集》的编撰者——芝加哥大学的斯托林教授为《反联邦党人文集》所著的导论。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讨论了反联邦党人的宪政主张、联邦党人的回应以及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贡献。
《邦联条例》是“联邦主义”的产物。简而言之,“联邦主义意味着州权优先,各州平等,州拥有主要的政治权力。”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美国不是一个建立在公民个人权利让渡这一基础之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各州之上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联邦主义”这一美国立国初期的基本原则中,“联邦”一词的含义绝不同于“联邦政府”中的“联邦”。尽管反联邦党人的观点之间差异很大,但总结起来,反联邦党人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都坚持联邦主义,认为新的宪法不符合州权优先的原则,而基于新宪法建立的过分强大的联邦政府会潜在地损害公民权利和自由。有人认为,反联邦党人实际上更应当被称为“联邦主义党人”,而联邦党人才应当被冠以“反联邦主义党人”的头衔。而联邦党人狡黠地混淆了“联邦主义”和“联邦政府”这两个“联邦”的用法,在当时的论战中将对方置于了反对者的位置,或许也是一种论辩中高明的政治伎俩。
虽然在这场政治角力中被摆在了反对者的位置上,但反联邦党人对美国宪法起到的作用绝不能用“破坏”与“拖延”来概括。反联邦党人仍然通过他们的思考和辩论为美国宪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促成了被称为“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尽管“权利法案”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反联邦党人们的失败,但这些法案的巨大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反联邦党人在无奈地接受新宪法的同时,强调“共和政府中权利法案的作用就是作为对多数人派系的一种制约” 。这一观点最终击败了联邦党人的坚持。而历史也证明了反联邦党人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使放弃他们最基本的“联邦主义”观点,转而支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也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无论这些方式是否看似不必要——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苏力教授对反联邦党人的贡献总结道,尽管他们的很多观点“并没有最后落实到美国宪法文件中,但其思想实际上已经进入美国宪法制度和实践,因此是了解美国宪法制度不能缺少的部分” 。
三、反对者的意义
反联邦党人的历史说明了反对者存在的意义。在任何一次目的高尚的政治论争和政治决策里,对于尊重历史、光明磊落的战胜者而言,反对者不是简单的“对立面”,而应当是与自己一道为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战友”。
一方面,从人类理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即使是再有智慧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很美,但却不值得期待,也不可能被发现。所以,无论是谁,在一场论争之中都无法做到使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十全十美。而反对者的攻击恰恰可以使得己方观点中的漏洞被发现、被填补,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观点的不断完善。而假如己方的某个论点本已十分完善,反对者的批评也有利于凸显观点的正确之处,并得到更多人的关注。总之,善意的批判(而非攻讦)只会使观点越趋完善,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真理越辩越明”。
另一方面,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各方的观点冲突往往是由于各方的利益不同。如果掌握权力的一方不断地封杀反对的观点,就等于断绝了不同的利益进入决策的路径。而社会从来都是利益多元的,当多元的社会利益诉求被一元的政治决策体制所压制而无法得到实现时,社会只能通过打破这种体制来寻求利益的释放。所以,允许反对者对政治问题进行讨论、批评,并让更多的意见代表进入决策之中,是一个体制长期生存的条件。事实上,反联邦党人对宪法的反对迫使宪法的推动者们看到了地方利益的诉求,从而修正得到一个能够满足尽可能多样的利益群体的体制,而“权利法案”也对每一个个体的权利作出了更大的保障。美国的宪政体制能够一直健康地运行到今天,反对者也可谓功不可没。
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反对者在政治决策之中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防错纠偏,避免极端。在美国制宪的过程中,反联邦党人的作用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四、正视反对者
尽管反对者能够作出伟大的贡献,但反对者却极少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在人们惯常的思维中,尤其是在中国长期以来“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哲学里,反对者意味着“敌人、反动、威胁”等等。而当一方在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之后,其反对者要么被从历史中抹去,以便营造出“高度一致”的太平气氛;要么遭到诋毁,而将功劳全归于胜者,从而更能反衬出胜者的伟大。这就是对反对者的习惯性的忽视或敌视。
无论是忽视还是敌视,一致的地方就是反对者的贡献极少得到承认,甚至他们的曾经的存在都会成为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中国,作为反对者往往没有什么好结果。古代政治中的反对者——以“谏官”为典型,即使“反对”不过是他们的本职而已——动辄“触犯龙威”而遭不测,似乎能够流芳百世的不过一个魏征而已;现代政治中的“异见者”也往往被封口、被驱逐,不能享有任何的话语权,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就举一个常见的例子:看看新闻报道,哪级权力机关不是孜孜不倦地在追求“一致通过”,似乎真能有哪项立法、哪次任命或者哪个决定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一般?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55年没有投过反对票”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人民代表最为自豪的事情 。而相反,任何人,就算没有遭到什么实质性的打压,但仅仅被贴上“反对者”的标签似乎就足够成为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对于一个政治体制而言,这是一种病态。正视反对者才是更好的选择。
正视反对者首先要正视反对者的存在。粉饰太平、强求一致是不可取的。忽视或者敌视反对者,将反对者的声音从整个话语体系和决策体制中剔除,对于一个期望自身能够健康长期发展的政权来说,既不可欲也不可行。不可欲是由于反对者能为这样一个政治体制提供自我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忽视或者敌视反对者不是帮助一个政权延年益寿,而只能是饮鸩止渴;不可行是由于社会利益越趋多元,表达渠道也日趋多样,权力对话语进行控制的能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所以,再假装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之时就已经表示要以民主作为“跳出历史的周期律”的关键,但民主最基本的要求——容许各种声音的存在——却一直未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内达到。这也是一个遗憾的地方。
正视反对者还要正视反对者的作用。习惯性的忽视或敌视植根于“斗争哲学”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现代社会更多地是一个“合作”式的格局,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往往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的可合作性就是放弃这种忽视或敌视最好的理由。反对者和赞成者处于一种“合作”的关系——也即,反对者所做的不是简单的“破坏”而已,他们能够作出伟大的贡献。要促进政治制度的发展,就必须给予反对者足够的空间和尊重,让反对的声音得到表达的渠道。当反对者得到应有的地位,不再处于被忽视和敌视的处境,当反对者的贡献得到正视甚至重视的时候,他们的作用才真正能够发挥出来。对于赞成者,或曰当权者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正视反对者、认识到反对者所能作出的贡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在学术自由度相当高的美国,反联邦党人的观点也长期受到冷落。但对具有非常政治智慧的人而言,能与反对者共存并正视他们的贡献,是高尚人格和宽广胸襟的最好体现;而能够勇敢地站到“伟人”、“强人”的对立面,以自己的反对观点为历史作出贡献,更是需要无比的勇气。两百多年前,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些,所以他们——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反对者——都在历史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代表们能够做到呢?
(SYSU法学院报 201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