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2018-3-05 10:56 | 作者: 食指/翟寒乐
食指/口述 翟寒乐/整理
摘要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聊布往怀,不胜感慨。诗歌在我心中是神圣的,我写诗时心是虔诚的。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我尝试过多种诗体,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到了晚年,尤其注重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韵味。我活着,就不改初衷,不停止思索,不停止追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停下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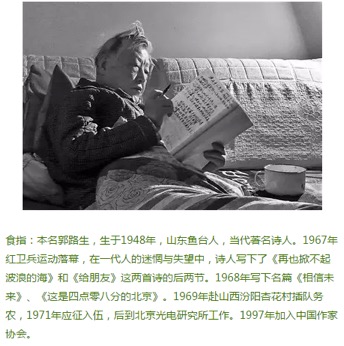
小时母亲诵读古诗 至今清楚记得两首
我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王庙乡程庄寨村。1948年11月21日出生在行军路上。
五六岁时母亲给我诵读古诗,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其中两首。一首是:
欲寄君衣君不还,
不寄君衣君又寒。
寄与不寄间,
妾身千万难。
就那么几个寄与不寄的字,把心中纠结缠绵的感觉说了个清清楚楚。我当时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还有一首是:
打起黄莺儿(ni),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可能是这两首诗特别耐读,读来语音缭绕,意味隽永,所以直到现在都记得。
上小学开始喜欢诗歌,买了好多儿童诗集看。对我影响大的是柯岩的儿童诗,如《两个将军》、《帽子的秘密》等,让我印象很深。受其影响,大概在四年级时写了: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
初中又读到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他们写的诗是新诗),都找到了小时听母亲诵读古诗的感觉。印象深的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乡村大道》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就那么几个句子稍加改动,读着绕来绕去余音绵绵不尽,和小时妈妈读的“欲寄君衣君不还”如出一脉。还有冰心的《繁星集》,里面的每一首诗都很短,就像元曲的小令一样,都有那种味道。
这样的诗作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朦胧中我感悟到诗歌的魅力——诗应该是这样的。这些可能是引导我走向诗歌道路的起点,我开始对诗歌着迷。
得罪老师继而挨整想自杀被马铃声唤醒
初中时,对知识的渴求让我放学后就在家关着门看书,经常是饭好了叫我才出来。为此母亲很担心:“这孩子别是病了吧?”父亲说:“没事,他是读书读进去了。”语文课开始接触诗词,到书店买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看,知道了诗词的常识,但没下工夫。
初二下学期的清明节前后,由于家庭的教育,写了首纪念二大爷郭耕夫、三大爷郭宗斌烈士的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得很英勇,很惨烈,让我深受震撼。记得几句:无数的花圈和挽联,萦绕在烈士墓边,花圈上那迎风抖动的鲜花,像是一簇簇跳跃的火焰。
初三因成绩优秀被评为北京市优良生。中考发挥失常,同年进北京函授学校西城分校补习,准备1965年再考高中。
在一年的函授学习中(主要在家自己温习),由于功课底子较好,就有了许多自己支配的时间,便比较系统地按照外国文学史认真读了些外国文学经典,并进行了分析。还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词、散文),以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优秀作品。此时和牟敦白有来往,他接触外国现代文学艺术较早、较多。我和他交往后,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作品和现代派艺术。
函授学校搞“反修防修”的反“自来红”教育,老师让我做典型发言,批我爱看外国小说,我对此事反感,不干,由此得罪了老师。老师联合团委书记整我。挨整很厉害,激烈的冲突使我有了退团的行动(上高一时父母找西城区团委讲明情况,才恢复了团籍)。
1964年底或1965年初,曾在一天夜里走到复兴桥上,想投护城河自杀。前思后想,在桥上徘徊将至黎明时,农村进城拉粪的马车经过,马铃声将我从黑暗中唤回。之后的一天早上迎着阳光骑车出行,心情和阳光一样灿烂,想了四句:喜逢朝阳送,清风款款从。飘然辞嚣市,田园育乡童。
“把材料塞进他的档案,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记得“文革”初期,当时整我的同班对立派的人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说:“把材料塞进他的档案,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些塞进我的档案的“黑材料”,在“文革”初和“文革”后期的下乡、交友、参军的经历中都产生了极大、极坏的影响。开始下乡都没有资格,等着运动后期处理。
在函授学校挨整的“黑材料”被装进档案,成为“问题学生”的佐证,更成为入北京五十六中高中后以及“文革”中挨整的基础材料。“文革”中五十六中的左派组织继续整我的“黑材料”,并将一些不实的“黑材料”塞进我的档案。如我在和同学议论读过的书时说“法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整成“黑材料”进了我的档案则成了我说“法国社会制度好”。当时有本很红、很风靡的小说,我看后说:这像中学生作文,里面有的抒情是模仿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也成了“黑材料”放进我的档案。
从1964年在函授学校开始挨整,到1968年我写出《相信未来》后,下乡前参加学校组织的秋收劳动时还在继续受到批判。我这个“问题学生”的问题是:看外国文艺作品,写诗。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在杏花村时,大队选我参加县里的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后资格被取消,我问是怎么回事,大队长只说了一句:“公社说档案到了”。
档案如影相随,从北京五十六中到山西汾阳杏花村公社,又经山东鱼台王庙公社至济宁市人武部辗转跟到部队。
我清楚地记得,在部队我已当了文书后,连里一位党支部委员当着很多人和我开玩笑说:文书还是个粉红色诗人。临离开部队前,我们营和驻地海军基地通讯营举行篮球比赛,一直观看比赛的营政委(我所在的独立营是政委编制)动情地和我说:“回去吧。把你的档案写好点。”这是肯定了我在部队的锻炼成长。
串联留在上花庄
1966年8月外出串联,9月下旬回京。在这期间,不知哪个学校的几个学生跑到我们家,说我们家有封资修的书,让处理。父母很害怕,处理了家里除马、恩、列、斯、毛以外的所有书,只有一套放在床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得以幸存。我回家得知此事,气得打碎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一片黑暗。
1966年11月,中央决定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串联。我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商定去延安。行至山西代县阳明堡公社,经当地挽留,我与同学王建平决定留下帮助社队搞“文化革命”(延安我曾去过)。之后我应该公社上花庄(大队)之请去上花庄帮助搞运动,其实也就是“四清”的扫尾工作。1967年初因宣布“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深感震撼。我佩戴的红卫兵袖章虽然是“十六纵队”的普通袖章,但怕引起群众猜疑,因此返回北京。
在上花庄,大队安排一个中年单身饲养员(时间久记不清名字了)和我同住。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整理汇集群众上报的材料。和我同住的饲养员话不多,我每天晚上回来他和我打个招呼,给我搁几支烟就自己休息去了。烟是大队买的,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吸烟。吃饭是大队派,在老乡家吃一天饭自己交四毛或三毛钱(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一斤粮票,钱和粮票都是从家带的。
何其芳专门给我讲授“新格律体”诗歌
在剧团认识了何其芳的孩子何京颉、何辛卯,于初夏认识了何其芳。自此之后,才对诗的韵味和形式及语言的知识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并开始了有意识的自觉追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
“文革”前在学校阅览室读到过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那些作为批判“靶子”的外国诗歌,虽多是零散片段,但美国的象征主义诗篇和苏联年轻女诗人阿赫玛杜琳娜的诗令我惊叹,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何其芳之后读他的诗集《预言》,发现有一种空灵感。如《月下》中的诗句:“但眉眉,你那里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即有,怕也结成玲珑的冰了。/梦纵如一只顺风的船,/能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以及《预言》等诗篇都是能把人心中的神性召唤出来的作品。
和何其芳的交往是我在诗歌写作道路上的最大幸事,对我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使我终生受惠。尤其是何其芳关于新格律体及诗与歌的关系的教导,使我懂得了中外诗体由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
何其芳专门给我讲授“新格律体”诗歌,讲得非常细,非常耐心。记得他先给我讲新诗的“形式”,他说:新诗是应该有形式的。诗体的变化从来是从没有形式到有形式,之后再打破旧形式,形成新的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跟社会和语言的变化有关,跟时代有关。在新诗的形式上,他主张“新格律诗体”,基本上和闻一多提倡的差不多。但在为什么要提倡写新格律诗上,何其芳老师更多地强调新诗应该有音乐感和韵味,有了音乐感和韵味才受老百姓欢迎。
那时我们特别喜欢唱歌,经常一起在何其芳老师家唱苏联歌和其他外国歌。何其芳老师曾对我说:你们喜欢唱歌,歌词配上曲子,好听好记。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的谱子是由几个乐句组成的,而乐句是由若干小节组成的,小节又是由音节组成的。要知道歌谱里的乐句就像一行一行的诗一样,一首歌里乐句里的小节数量是一样的,同样每个小节里面音节的长度也是一样的,这样唱起来非常和谐,感觉余音绵绵不断。新格律诗体,像歌的曲子一样,一首诗几段组成,每段中的诗句和曲子里的乐句一样,句数基本相同,每句中的顿数也叫音步,也应和乐句中的音节一样,大致相同,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二、四或二、四)押尾韵,就会产生和歌一样的效果。
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民歌也非常有音乐感,配上小调也很有韵味,民歌体是否也应该提倡?记得老师说:在反映现代这个博大深沉的社会时,新格律诗体比民歌体要好一些。
我听得认真,牢记在心。这等于是说,写新格律诗体的诗人就和音乐家作曲和谱曲一样,有节拍、有句式、有章法了。再加上押尾韵和略微注意点平仄,诗就有了乐感。一首好诗会和受欢迎的歌和乐曲一样好听、好记。如果你了解新格律诗体和懂得音乐简谱,就知道何其芳的联想多么神奇,把歌、曲的体式与新诗形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必然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何其芳的思考与实践是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我把当时写的诗稿拿给何其芳,何伯伯不但看得认真,还写上自己的意见,再耐心地和我谈,一点没有名家大诗人的口气和做派。谈完了,还嘱咐我:“要记得”。
还有一点要提及:从小我一直觉得诗的抑扬顿挫特别好听,像声音的回廊,觉得新诗里也应该强调一下。1967或1968年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新诗中平仄的问题。何其芳老师说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问过语言所一位好像是姓陈的所长,他是这么说的:“现代口语亲和力强,仄声字多,新诗中这个平仄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写诗时,一句诗中仄声字多的时候,就适当地换几个意思一样的平声字的词,使诗句朗朗上口。
1967年、1968年陆续写出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诗作,这与何其芳伯伯对我的教导密不可分。
这件事让我心中一惊 因为我是准备一辈子写诗的
1968年的夏秋之交写出《相信未来》。王东白说,张郎郎(编者注:美术家张仃之子)逃往外地之前在他的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正合我当时不好的心情。原来还想写“用孩子的笔体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后觉得字太多了,不合节拍。
刚写出《相信未来》就有一次与谷牧伯伯的巧遇,谈到了文学创作和诗。其间谷伯伯诵读杜甫的诗《旅夜书怀》,他那略显浓重的胶东口音,沉郁苍凉中带着些无奈,把我惊呆了。杜甫的诗我读过,可谷伯伯的声音、语调,把我这个刚写完《相信未来》的小青年震住了。这才是诗啊!我写的那叫什么?回到家,马上找出杜甫的诗选来看。让我极其失望的是,一个个铅字呆板地排列在书上,再怎么读,也找不到听谷伯伯读诗时的那种震撼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还有件事也必须提一下,因为对我的影响很大。谷伯伯在听我说了为什么喜欢文艺后,喝下一杯白酒,沉思了一会儿说:“年轻时都写诗,成仿吾在创造社时常写东西,可到苏区就不写了,做其他工作了。”成仿吾的事当时只略知一点,他是创造社的成员。到苏区之后的事我一点不知道,不敢说什么。
这件事让我心中一惊,因为我是准备一辈子写诗的。谷伯伯说这些时,是边考虑边说的,语调很有些沉重。之后再联想到小时候读到的鲁迅答《北斗》杂志提问,我就一直在考虑,怎样生存?如何给自己创造一个温饱的环境?在单位的传达室工作后,才找到了有饭吃、又宽松、还能学习(传达室报纸、文艺期刊多)、写诗的地方。1985年1月初开始长期住院,这个问题就搁置了,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反复推敲、诵读、删改的诗作
《相信未来》原创第三段“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最后删去了,为此有的朋友一直觉得可惜。这是我多次朗诵后,经过认真考虑删去的。“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这心境是非常凄凉的。“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情绪开始高昂,“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情绪更高了。这种在高昂情绪的逼迫下一步步递进的不适当的高昂,不符合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压抑。删去了这一段,心中的情绪自然转成了低沉的“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很大气、很深情,用孩子的笔体则是充满向往,但却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这才符合当时的情况。
1968年写出《相信未来》后,经曲磊磊引见去贺敬之家谈诗,认识了贺敬之和从小喜欢的儿童诗作者柯岩。柯岩在厨房做饭时我和她就写诗的问题交谈了一会儿。柯岩去世我写了篇怀念的文章。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原创第三段的后两句——“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正式发表改为“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蓝天里,只留下鸽铃那袅袅的余音”。有朋友觉得“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是神来之笔,删了可惜,可我特别喜欢鸽群飞时的铃声,听着心里舒服。
《鱼儿三部曲》我写得最下工夫,也是我最满意的诗作之一,不料竟无意言中了自己的命运。“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这是《鱼儿三部曲》“三”的开始两句。形容冬天快结束时,雪没那么大了,雪白的单衣是残雪。在1974或1975年修改时为了整个诗的内容忍痛割舍。当年诗写好也被大家传抄,我听说一位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什么人看到此诗时说“这才叫诗”,吓坏了我,想收也收不回来了。后来在《今天》发表时,我的原稿已丢,用的是北岛保存的抄稿。

送别人下乡和自己离开北京感受太不一样
1968年12月18日乘下午四点零八分的知青专列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在车上秦晓鹰说,“给你找个空点的车厢写诗去吧”,随后找到一节人较少且有暖气的车厢,是夜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第一稿。19日抵达杏花村,20日完成定稿。初稿的第六段是:“……然后对她粗声粗气地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当时车站特别乱,只能这样大声喊着说话,三个小短句也符合节拍。原稿的第三段“人们都用手捂住了眼睛/放下你们的手吧/让我再看看你们/那两颗闪烁着温情的明星”在定稿时删去。
小时候,衣服扣子掉了,母亲给我缀扣子时,我穿着衣服站在母亲面前,母亲把扣子缀好了,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这是印在我脑子里非常深的印象。临走的那天,母亲又给我钉了扣子,是将扣子加固。母亲没有去车站,只有妹妹丽娜一人去送我们。以后才知道,那天父亲也去了火车站,只站在远处望着。我们走的那天,全家没吃晚饭,连灯也没开。
这之前写过送别人下乡的《送北大荒战友》。送别人下乡和自己真要离开北京感受太不一样了,尤其火车开之前“咣!”的那一声,一下让心里一震。“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改成过“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雄伟”和周围的环境符合,但内心仍感觉是尖厉的声音,后又改了回来。这首诗曾在多个场合朗诵,有时会随心情脱口朗诵成“一声心碎的汽笛长鸣”。
临下乡之前,何其芳、贺敬之都不约而同地和我谈到向民歌学习的问题。贺敬之还专门谈到我的诗语言有些晦涩,应该学习民歌语言的简洁明快。何其芳给我找出一些民歌诗集让我带到农村学习。除此外我还带了《老人与海》,另有甘恢理送的《永别了武器》、《马雅可夫斯基诗集?长诗卷》,马雅送的《汉魏六朝诗选》、《辛稼轩词鉴》,梅天、梅津送的《鲍参军诗注》。
插队杏花村,写作组诗《红旗渠》
杏花村很大,是一个公社,分西堡和东堡,西堡和东堡分别是大队,我们在西堡。这里远离运动,尊重文化。在大田干活的时候还能听到老乡们唱上辈人传下的民歌,比如《走西口》、《送情郎》等小调。
除了劳动,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零碎时间读书。逢雨天不出工时,更是我读书的整块时间,别人在隔壁聊天我根本听不到。
由于摆脱了城市和“文革”中挨整的处境,心中阴云散尽。
1969年回北京,一次朋友相聚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彭宁说到红旗渠,说那是农民修建的,了不起,应该写写。那时正在农村插队,对农民和农民生活有所了解,彭宁谈到农民的这一创举,对我又是一个震撼,决心写出红旗渠。
1970年的9、10月份,在山东老家因给生产队办事,去泰安市水利局。在办公室看到介绍红旗渠的两本不同的小册子,非常高兴,向人家索要。要来后一直带在身边,仔细阅读,准备写红旗渠,阅读中把想出的句子随手记在小册子上。
1973年3月初,我决定亲自去红旗渠看看,看看农民创造的奇迹,希望能写出歌颂农民的诗。记得很清楚,我是穿着棉袄、绒衣、绒裤,背了一个装满馒头军用的挎包,带着部队发的搪瓷茶缸出发的。先坐火车到安阳,再打听着去红旗渠,沿着红旗渠走到拦河大坝,看到了漳河。一路饥了啃干馒头,渴了舀红旗渠的水喝,晚上住两毛钱一夜的大车店。后来钱花完了,把身上的绒衣脱下卖了五元钱,买了张到邢台的火车票。我的一位本家大爷在邢台,去了他家,让他给我买了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回京后我把诗串了起来,原先写在小册子上的闪光句子都用上了。小册子就是介绍一段段水渠,我把它全部想象成人物的形象写出来,这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和当时的样板戏(立人物)的影响。像青年洞,我把它写成青年小伙的形象。宣传册子上有一句介绍“土专家”,我把他的形象发挥了:“捡根树枝地上画,画山画水画远景,画出山水甲天下。”这样我写出了《红旗渠组诗》的《序诗》和第二首《英雄汉》,第三首《好后生》,还写出了《壮志篇》。
入伍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两年
1970年12月在入伍年龄的最后一年(在还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怀着能写出军旅诗的心情决心去部队好好锻炼。从济宁应征入伍,去了浙江舟山定海的舟嵊要塞司令部直属通讯营三连(永备架设连)。1973年1月退伍。
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两年。
紧张的施工,严格的训练,刻苦的读书,两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生活、劳动、读书的思考等,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体验,思想和身体得到很大的锻炼,有了坚强的意志和结实的身体,扛住了以后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和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军旅诗。
刚入伍在新兵连写出《新兵》一诗,分到连队后在班里挤时间写出了《刺刀篇》、《架设兵之歌》。
1971年接徐庆东来信,信中讲到舟山有个诗人陈山诗写得很好。在我认识了军宣传处干事叶文艺后,和陈山认识。后来借到陈山的诗集《擂鼓集》,读着很惊叹,真好!还抄了很多。“夜半三更/一片红旗天上走/万点白帆开绣球/潮迎人面起/喝彩看飞舟/刺刀如水向东流。”这样的诗句我看两遍就记住了。受其诗作影响,我写出《刺刀篇》、《壮志篇》、《红旗渠组歌》、《海礁赋》等。
1971年当战士期间,我挤时间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别人施工回来都忙着洗涮,我一回来就到我们班的学习室看书。“文革”前我读完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1971年提倡读原著,我是带着读《矛盾论》、《实践论》中的问题借来《自然辩证法》读的。
训练中我很认真,能吃苦,曾背着备复线从山坡上直接往下跳,把班长吓坏了,告诉我若跳到老乡砍的竹子茬上能把脚扎穿,让我买很厚的帆布鞋垫垫在鞋里。部队的生活紧张又充实,每周只有半天的自由时间处理个人杂事(洗衣服、写信、请假上街买东西等),写的诗不多。
1971年底我被任命为连里的文书,工作比在班里更加繁忙。文书室在北边的一栋房子,是一个单独的房间,保管的有档案、手榴弹、子弹、连排长的手枪。前任文书交班时提醒我:吸烟注意点,离弹药箱远一些。除了分管的工作(每周要制定出各班、排每天的施工、训练任务以及学习的具体时间表,协助指导员讲国内外形势,准备各种材料,按时出时事和思想板报、每周定期擦拭保养一次手枪),以外,还有上级安排的临时任务,几乎没有个人读书、思考的时间。因配合给战士讲国际形势写出《澜沧江湄公河》。
1973年1月正式退伍,先被安排在北京市第二光学仪器厂(通县)的技校任辅导员,后因去河南林县红旗渠写诗离职。离职前曾给通县县委写信,希望能安排到通县农村教学,我心里觉得这样可以利于写诗。
1979年,正式使用“食指”笔名
1973年的夏天很热,时常休息不好。在我刚过了二十五周岁生日三天后的11月25日,被送北医三院精神科。在有理想和梦的年龄,被当成疯子,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这样反而使我更豁达地面对人生了。沉静是内在生活的力量,我提笔面对命运,诗就这么一路写了下来。
出院后的1974、1975年写出《灵魂之二》,完成《红旗渠组歌》。在我整理以前写的诗时(《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我还能记得,第二部第三部已经遗失),《鱼儿三部曲》第一部中有“……又怎能在现实中迈出坚实的步履”的句子,我想鱼儿怎么能迈步走呢?为了这一句我把整段都删了。而删掉“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这样的句子也是为了回避当时的痛苦。“经过人世时,我脚步放得很轻”,我从不敢大喊大叫的。
1978年12月下旬,北岛、芒克、江河、黄锐等带着刚刚油印出来的第一期《今天》来家里找我,约我投稿。此后一段,和他们来往甚密。
1979年在《今天》发表诗,正式使用“食指”笔名。食指的意思就是“时之子”,时是母亲的姓,又和老师的“师”谐音,别无他意。
1980年柯岩几次来信要诗,在母亲的催促下,给了诗刊社《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两首诗。刊登在1981年1月号《诗刊》上。
不想回北京,在汲县火车站,落下右腿伤病
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由于自己是个“疯子”,做不了什么事。近年底时,想去农村教书,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还能有时间写诗。10月底和母亲打了招呼,拿着刊有我的诗的《诗刊》,去了母亲的老家山东单县。1974—1984年我基本是上半(天)班。1974年刚出院不久,有天下班的母亲把我叫进屋里,过了会儿才心情沉重地和我说:“以后吸烟回屋里吸,刚才有路过的人指着你对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疯子’。”母亲说了后我不敢再去前院,就去后院站着吸烟,思考修改以前写的诗,然后回家整理、修改诗稿。虽然心情不好,诗写得很苦,但到80年代后还是注意了锻炼身体,坚持洗冷水澡,能连续做三十多个俯卧撑。
记得去单县还不好买车票,买到的是一张退票。未果。不想回北京。从单县回鱼台老家,在四大爷家住了一段时间,帮着卖完公粮。
还是不想回北京。从鱼台乘长途汽车到砀山,然后转乘火车到郑州。去河南是想到兰考看看,写焦裕禄。记得那年冬天在郑州时雪下得很大,天很冷。在火车站挎包被偷,一本《诗刊》和钱全没了。到郑州一家医院找我的一个姨,没找到。在火车站滞留了几天。
仍然不想回北京。把戴的一块钟山牌手表卖了五元钱,除去吃喝,盲目地买了张去河南汲县的火车票。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汲县下车是半夜,只能在车站等天亮。躺在水泥地上休息竟然睡着了,早上醒来整个右腿麻木,掐着没有一点感觉。我用左腿撑着身子站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拖着无知觉的右腿沿铁路往回走到新乡,我的一位堂哥在新乡。在新乡住了一天,次日堂哥汉章陪我回到北京。母亲告诉我,她梦到我的一条腿被截肢,拄着拐回家的。还好,我的腿慢慢恢复得以保住,只是落下伤病。
在安定医院,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写诗
1985年1月初住安定医院,一直到1989年春节。在安定医院住的那几年,对我的管理比较宽松。比如别的病人须家里人来接才能回家小住,而我却可以每周六自己回家,周日再自己返回医院。
在安定医院写出了《真想再见你一面》、《黎明的海洋》、《我不知道》、《秋意》、《受伤的心灵》等诗篇。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和《秋意》两首诗是在冬天写的。睡觉时病房里一片漆黑,我只好借着过道的照明灯光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写诗(因腿有伤蹲不下,即使能蹲下手也够不着地)。我把纸铺在地上,全身趴地上,硌得膝盖真疼。想好一句趴地上写在纸上,赶快爬起来活动活动。再想一句,再趴下写,胳膊肘都硌得疼。“随意踱步能使人浮想联翩/冬夜里内心中跳跃着诗意的火苗/喧嚣不安的白天得不到的东西/我要在冰冷的月波下细细寻找……直到灵感化为动人的诗句/才感到已是寒气逼人的拂晓”。
安定医院我所住三病区的臧护士一直让我心存感激:有次他值夜班时,我夜里起来写诗,想休息一下,他扔给我一盒火柴,使我得以吸支烟,缓解身心的疲惫。还有三病区的任护士、杨护士、王护士等也对我倍加照顾。
2000年写《青春逝去不复返》这首诗写得特别苦,因为条件改变,又回到病区,一想到自己十多年身处绝境的无助心态,决心写好这首诗。白天在乱哄哄的大房间,大房间是在病区走廊的尽头,所谓病人活动室。除了睡觉在病房,吃饭在饭厅,其余时间全病区四五十病人必须在活动室坐着或站着。活动室有一台电视,有几条旧的老式长条候诊椅,病人可以看电视,可以聊天,不能走动,有一位护工坐在门口看着,病人去厕所需向护工打招呼。医生每天的查房也是到活动室看看自己管的病人。想起一个词或一句诗,有时是改动的一个字,找护士借笔写在手背上,洗碗还怕洗掉。有时还是不小心会洗掉,以后就写在胳膊上。病房的门只有中午和晚上睡觉时才开,一开门赶紧进去记在纸上。
我活着,就不改初衷
在精神病福利院十二年,我从小被诗歌培育的心始终没有变。清夜无尘,月色如云照无眠。漫长的冬夜,追求与思考从来也没有停止。一次次提笔抒写心中的伤痛,诗伴随我等待着春天。
2002年3月21日,寒乐接我走出福利院。这一天恰巧是世界诗歌日。出院后不久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2005年5月1日迁居海淀区上庄,开始了真正的晚年生活。粗茶淡饭,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2006年2月9日,我和翟寒乐办理了结婚手续。
从小妈妈教我读古诗,抑扬顿挫的声音,我听着像声音的回廊。这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就是吸引我,直到55岁时才从介绍钱钟书韵论的文章中知道,这种感觉是宋代范温论韵味时以听钟比喻点明的。范温在《潜溪诗眼》谈到韵味时说:“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
我以为“韵味”按范温的话说,用听钟声的心神愉悦来比喻是再合适不过的。回荡的钟声会令人们各有所想,直至陶醉了不能自已。诗歌是如此地讲出了人们心中深处的东西,叫我着迷。这些就是我和传统割不断的联系;我觉得这是中国诗的根,是中国诗歌血脉的延续。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聊布往怀,不胜感慨。诗歌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我写诗时心是虔诚的。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我尝试过多种诗体,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到了晚年,尤其注重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韵味。我活着,就不改初衷,不停止思索,不停止追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停下笔来。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
责任编辑:实群
文章来源: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