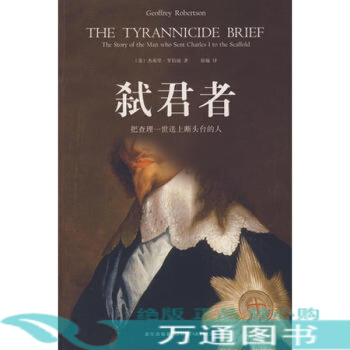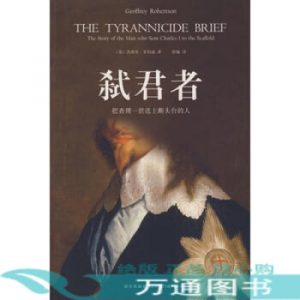 人类的历史写作仿佛是一种竞争——挖掘者与那种掩盖史实的力量之间的竞赛。太多的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死后迅速被忘却,或者因为事功肤浅,声名虚张,或者因为某种党派立场或集体心理,成为心照不宣的禁忌者。如果说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打破禁忌、挖掘真相便是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的历史写作仿佛是一种竞争——挖掘者与那种掩盖史实的力量之间的竞赛。太多的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死后迅速被忘却,或者因为事功肤浅,声名虚张,或者因为某种党派立场或集体心理,成为心照不宣的禁忌者。如果说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那么打破禁忌、挖掘真相便是历史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罗伯逊先生的这本巨著正是这样的正本清源之作传。对于英国历史有所涉猎的读者都会知道,发生在距今300多年前的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起意义重大的事件,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慷慨赴死的一幕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大场面之一。但是,正如罗伯逊所言,人们对于这场审判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起草了起诉书并且在法庭上对查理一世进行指控的副总检察长约翰·库克却很少关注,例如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手边的是英文第15版)居然没有收入他的词条。某些历史书里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标签化甚至妖魔化。这种情况引起了作者的忧虑,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对于某个人的评价,而且关乎重大史实的真实面目以及对于宪政和法治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一.国王走上被告席
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篇章,也是英国近代宪政体制得以形成的关键时刻。国内各种实力风起云涌,最终导致内战烽火燃烧,不可一世的查理一世沦为胜利者的阶下囚。库克出身贫贱,不过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法律界的显要人物,各种不同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终于成就了一个法律人难以梦想的一份大事业——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次著名的审判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说法看出,据说那些法官们在判决书上签完名字后很快就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惊呆了。
当一般历史学家从政治的角度解释这场审判的起因、过程以及后果的时候,罗伯逊用他那极其细密的笔触对整个事件给出了法律角度的描述和分析。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经追问何以没有人写出英国法律史,他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做出分析,法学教育与历史学教育的差异使得两者思维方式出现了某种对立:法律家所需求者乃是权威,于是最新最好;历史学家需求者乃证据,于是越旧越好。由于过分关注历史与眼下案件之间的关联,于是法律人所呈现的历史就会发生扭曲,但是历史学家由于缺乏法律的训练,所揭示的事实又失去了法律的意义。所幸的是,作为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的人权法和国际法专家,罗伯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细节化的事实,而且对于那些细节中所蕴含的法律含义做出了深入的解读。这是我们阅读其他历史书所难以获得的收益。
不妨举一些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强烈的例子。从这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出,早在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发生之前,一些法律人一直在寻求对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论证,这种论证的指向明显地朝向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罗伯逊迫溯了17世纪初爱德华·柯克爵士对于法律高于王权的论证以及身体力行的抗争。不过,柯克与詹姆斯一世之争涉及的是国王是否有足够的合法性审判臣民的案件,而库克与查理一世之争却是国王是否可以在他的王国里成为一个适格的刑事被告。换句话说,当君主本人的行为涉嫌违法甚至实施暴政,人们是否可以把他送上法庭审判,从而走出或者忍受奴役或者揭竿起义的恶性循环。审判的前前后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虽然坐在被告席上,但是,查理·斯图亚特仍然是国王,那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们也如此称呼他。国王本人在法庭上更是公然对于法庭的管辖权提出质疑:
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是法定的国王。仔细想想,你们企图审判国王,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记住上帝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审判官,我说你们在犯下更大的罪之前真该仔细想想……况且,我的权力是上帝所托付的,这是古老的合法的世袭权力。我绝不会违背这项托付的。我也不会为了答复一硕新的非法权力而违背我的托付。所以你们要先告诉我你们权力的来源,否则我无可奉告。
实际上,依据下议院1649年1月6日所通过法律而设置的法庭是否有权审判国王的法理基础有着显而易见的软肋。这项立法在被上议院推迟之后,由经过清洗之后的下议院变换策略将“Ordinance”变为“Act”而绕着弯通过。此种做法当然受到了一些质疑,以至于克伦威尔及其拥护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为这样的立法程序寻找依据。代议制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揭示,那就是由于下议院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因而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议院的立法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的同意或协助。如罗伯逊所说,这一宣告乃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构明确提出的民主原则。
在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上,库克以及布兰德肖法官在本案中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学说。例如,布兰德肖在法庭上向查理一世宣示:
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是为保证好好履约。同时,先生,这一约定当然是相互的,你是他们忠实的君主,他们也是你忠实的国民……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带的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先生,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
二.孟子难题
以上这一段论述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要义,布兰德肖法官提出这一学说比洛克和卢梭提早好几十年。阅读本书,我不免想起我们的历史上的种种限制君主权力的努力,不妨话分两头,略作讨论。孟子在跟齐宣王聊天时涉及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孟子的这种说法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是相当激进的理论。他的逻辑的关键在于将“君主”与“一夫”(或后世更常说的“独夫”、“独夫民贼”)作出区分:当一个君主贼仁残义,沦为暴君,就已经自我放弃了君主的身份,对其征讨诛杀就是正义的行动者。这样的学说是否也有某种社会契约论的色彩呢?
不过,困难依旧存在。孟子学说在后来的一个回声是司马迁在《史记》里记录的辕固生与黄生之间的对话。辕固生,齐人也,是研究《诗经》的专家,更是一个惯持异见的人。那一天他和黄生一起跟汉景帝聊天,话题扯到了汤放桀、武伐纣的事情者。黄生义正词严地驳斥那种认为汤武所为是受于天命之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马上反驳:
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同样不以为然,他用比喻说事,曰:
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这样的比喻真的难以把道理说通。拿帽子和鞋来比喻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表面看来有点类比的可能,例如常态之下的分工和地位高下。但是,除非“文革”其间红卫兵小将们制作的那种以羞辱人为乐事的帽子,平常的帽子都是保护人的,又如何反过来残害人身?还有,他回避的一个可能性是,如果臣下按照“正常程序”正言匡过,但是天子我行我素,暴虐依旧,为臣者又该怎样?遗憾的是,辕固生既没有如钱钟书先生希望的那样,引已位居正统的《孟子》张目,显示“当时陋儒老生之专固”,更没有抓住黄生叙事话语中的破绽,进行更细致的追问,反而拿本朝开国皇帝来堵对方的口:
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可以想见辕固生的这种“归谬法”论证一定让黄生张口结舌,无法回应。但是,拿这样的敏感事例说事势必让景帝感到为难,于是他也以比喻对比喻就把这场辩论给草草“和谐”了:“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司马迁如此感叹。
不过,即便后世可以讨论,也还是无法走出这种一方面是君为臣纲,另一方面是可诛暴君之间的两难者。即便是按照孟子的理论往前走,还是有一个难题:怎样判断君主已经沦为独夫?这里包括以怎样的标准判断和由谁来判断两个方面。暴政或者暴君显然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否则孟子不会用“贼仁”、“贼义”这样极具贬义的词汇来形容。智力的平庯、性格的懦弱、施政的举措失当都算不上。暴政一定是在对内或对外的行为上残酷、虐乱达到极其严重程度才构成。但是这里的界限还是含混不清。历史上固然有些定评为“暴君”者除了夏桀殷纣之外,秦始皇、秦二世、隋炀帝都是大名鼎鼎的暴君。根据一位作者的说法,中国历史上500多位皇帝里,暴君的比例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这些暴君的称号也大多是在后世才获得定评的,而且还经常在评价上有所反复。实际上,细读历史,即使是在那些明君圣主之下,某种程度的暴政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在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的治下,甚至有“康乾盛世”之誉,但是,“文字狱”频发,动辄株连九族,将大量无辜者流放尚阳堡、宁古塔等烟瘴之地,流放者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或被饥饿难忍的当地人分而食之的事情不绝于书。
至于暴君或暴政的构成由何人、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判断,也是没有解决的难题。孟子曾就是否杀某人提出了某种具有民主色彩的判断方式:“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日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盂子·梁惠王下》)这样的说法曾在近代被沈家本用来论证引进陪审团制度的古老依据。但是所谓“国人皆日可杀”也要有个检测手段,今天某些国家采取的全民公决可以说是检测公民态度的有效手段,以大陪审团来确定是否提起公诉,也是一种更具操作性的途径者。孟子的问题在于,他只是如此主张,但如何操作却不置一词。后世中国思想中的某种只高扬宏大价值而忽视技术层面的制度建设的特色,跟先秦儒家的这种内在缺陷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
把这样的困境单纯归因于儒家学说也许是不公平的。我们从孔子、孟子、《淮南子》一直读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以看到人们一直在歌颂尧舜那样的明君圣主,在谴责后来的“茶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独夫民贼,在严苛的政治现实面前,这种规劝或谴责终究不过是以石击天或与虎谋皮,令人徒唤奈何。理论很难超越其所产生的环境,古典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权力的架构乃是形成这种一方面呼唤诛杀暴君,另一方面却在暴君治下无奈叹息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以造反相威胁甚至索性推翻王朝的事例也是不绝于书的。但是,悲剧在于,新建立的王朝专制如旧,历史不过是在不断地循环。甚至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也无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哪里是出路?
从西方历史观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能够引出起诉一个暴君,在一个法庭上对之审判的结果,有比抽象理论和法律条文更重要的因素,举起荦荦大端。第一,社会结构中是否存在着足以跟君主抗衡的其他社会阶级。第二,是否存在着一种为君主与国民所共同信奉的宗教信仰形成相当的制约,这种信仰首先要有某种内在的自由指向,其次它不仅是一种观念的存在,还形成了组织化的力量从而迫使君主就范。第三,与君主共同治理国家的官僚集团是否能够在与王权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约束力量,从而让君权循规蹈矩,严格地在事先设定的程序和实体规范中行使。用韦伯的术语,这就是权力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或者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也就是真正的宪政的发轫。最后,也许是一个偏向法学专业角度一个因素,那就是是否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法律职业集团,其成员发展出了一种专业化的知识,并成为官僚集团的一部分从而分享和塑造国家权力,为权力的限制提供坚实的知识基础,这正是理性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层面。
回过头来,我们看在起诉查理一世之前英国已经积累的基础。显而易见,从进入17世纪开始,从苏格兰来即位的詹姆斯一世就面对着议会以及国内士绅贵族的巨大压力。跟从前占主导地位的辉格派历史学家不同——其实这本书也是努力摆脱辉格派历史观的一次重要努力——晚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不再认同那种黑白分明的历史观,好像17世纪的政治史就是一边是代表宪政主义的议会党人,一边是固守专制暴政的王权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史,其他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国王与议会尚具有不可忽视的合作的一面。但是,从16世纪起在英国出现了愈演愈烈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尤其是新兴的地方士绅与王权之间的斗争,这一历史事实还是得到了广泛公认的,在罗伯逊的书中也有较多的叙述。这种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乃是议会。
三.库克的法律论证
库克在论证君主与人民之间关系时强调了普通法对于受托统治国家的君主所施加的限制。如果可以在法律上确认君主侵害了国民的权利,常设议会就成为提供救济的正当途径。不仅如此,库克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对于政体模式的选择权力即便是在君主没有侵犯国民权利的情况下,人民也可以选择摆脱君主制,因为那样的政府既缺乏理性,也不为上帝所乐见。
除了管辖权以及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外,法庭面对着的另一个难题是,假如被告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因而在审判过程中对控诉本身不作任何有罪或无罪的有效答辩,就像查理一世在法庭中所表现的那样,法庭是否可以依照“本国众所周知的法律规则……视其为‘如同承认’”。在审判中,国王没有聘请律师——本来如果国王承认法庭合法并希望作无罪答辨,杰出的法学家、律师马修·黑尔是准备出庭为国王辩护的,同时国王本人也没有作出有效答辩,致使一场也许会精彩纷呈的法律论辩没有发生。最终法庭不得不直接作出了有罪判决并宜布“应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为了说服公众,库克将他原计划在法庭上发表的公诉意见以书的形式出版,当然,这个小册子也成为王政复辟后判决库克死刑的一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给查理一世确定怎样的罪名也是当年颇费周章的法律事项。我们知道,最后法庭判决所确定的是“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库克如何论证君主的独裁行为与暴政之间的关联,对国内以及国际战争中所发生的杀戮行为君主是否应当承担作为指挥官的责任,是否构成“暴政”的罪名?如果对于叛国罪的定义是背叛国王,那么国王本人又如何可以自己背叛自己,成为叛国罪的主体?库克旁征博引,援用上帝律法、普通法、自然法以及国际公法等进行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即便在今天还是具有重大的启迪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在这次审判以及1660年对于库克等人的审判中,还有一些富于法律意义的事项和观点值得点出。在审判查理一世之前,国王的法律宠臣布里奇曼曾经以《大宪章》中“同侪审判”的规则要求组成一个不可能有的陪审团进行审判,被库克以鲜明的态度拒绝。刑事被告的诉讼权利逐渐得到关注,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刑事程序中开始出现。审判过程中对公开原则的恪守也令人感慨,即便审判的是国王,也要公开地进行。库克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阐述,诸如律师不应以商人的方式招徕顾客,律师、医生以及神职人员不宜过分富有,律师应为因自己过错而导致客户之损失承担责任,律师要劝导委托人慎待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应当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某些受法庭宠爱的律师,律师应当给贫穷者提供法律援助,不得以律师为“坏人”辩护而将其与被告混为一谈,律师也不应为法庭的判决结果负责(这是库克在受到审判时为自已提出的重要的抗辩理由,也许是后来著名的“计程车规则”的滥觞),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法律职业意识在17世纪的逐渐形成,也在后世获得了响亮的回声。
通读全书,作者所体现出的公正无私的立场和在字里行间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把握和专业精神都令人印象深刻。著名历史学家巴拉科夫在评价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时说:“在这个历史学家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做研究的时代,本书实为巨著。”不过,望远镜也不能取代显微镜;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把两者交替使用。罗伯逊先生显然更多地用显微镜观察历史,尤其是法律的显微镜,这使得该书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此,我们要向作者致敬,也要向年轻的译者表达谢意,这不是一部容易翻译的著作。
最后,容我对书名的翻译提点看法者。原书名中的“Tyrannicide”,也许是从“Regicide”衍生而来秦。Regicide传统上翻译为弑君或弑君者,但是当表示国王的词根变成 tyranni-,指的却是杀死暴君(tyrant)的人或这种行为。麻烦的是,正像我们前面引用的孟子与齐宜王对话所显示的那样,汉语里的“弑”字有着鲜明的情感色彩,包含着对于杀人者的贬低,所以孟子明确地说武王伐纣不能算是弑君,只是诛杀纣这个独夫而已译。所以,本书书名译为“诛暴君者”或许更适当些者。质之徐璇君,不知以为然否?
本文选自《私法》,第9辑第1卷(总第17卷),是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一书中文版所写序言的扩大稿(序言扩展为读书笔记)。
来源:书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