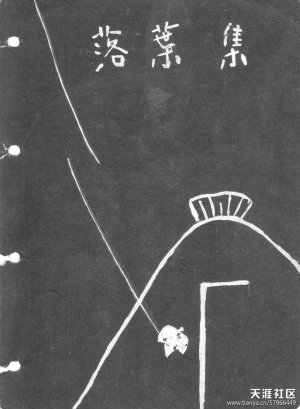六、“想当初、枇杷楼下,好诗齐发”
没有理由认为,《落叶集》系文革中写的。其中找不到,文革的时代印记。
不论现在的人,对文革怎么评价,起码就事实来说,迄今所知“三年文革”大起大落的剧情,跟《落叶集》所展示“这是一个完全喑寂的世界”、“这儿本就是一座大墓”……不吻合。《学生》一诗中,“小数点左移/黑色沦为负数”,及《未及》一诗中,“在户口簿上的消息/如重重迭迭的咒语”,在在表明“森严壁垒”,而非打破秩序的“史无前例”。
收入《灯花集》,标明写于1965年2月,也就是文革之前的《门》写:
阶与阶之间/有无数森严壁垒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门/它既是原始的自然的火与水/也是四大金刚们的法器/以及他们怒睁的警惕的/眼睛
历史地讲,“阶与阶之间森严壁垒”,防范意识深入人心,是文革爆发之前的常态。文革爆发初,也就是“刘邓路线”时更是,似乎变本加厉,但也有所不同。至于1966年底“群众发动起来”后,“阶级斗争”为“路线斗争”所取代,就大分裂、大改组、大动荡甚至大内战了……诗集《落叶集》中内容,基本与这些无涉。
当然可以,多说一点。据刘国凯讲,“文革前和文革初,那出身等级歧视和政治等级歧视是何等沉重地压在我们这类青少年的肉体和心灵上。没有在那段岁月里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红色恐怖运动”中,“黑五类”鸡鸭一样被打死,甚至鸡鸭不如——
……1966年12月是一个群情激奋的日子。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这样扬眉吐气过。那情景是以前做梦都不可能梦到的。党的书记们从来都神圣无比。他们总是绝对正确、满脸严肃。群众总是匍伏在他们面前,听从他们的教诲、指挥。现在一切都难以想象地颠倒过来了。他们被党中央宣布做错了事,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之至,他们无可奈何地对群众认错,接受群众的批判。看到这些情况,我深为惊讶,也从中体会到原来群众心中隐藏有这么多的不满情绪。
(刘国凯:《基层文革泥泞路》)
据武宜三回忆,没有广大群众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积怨,文革一定搞不起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武宜三《我与文化大革命》)
当然“大乱”不到三年。随后“清阶”、“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甚至大张旗鼓“备战”……那是后话了。关于文革起来后的回忆,邓垦、陈墨的记忆跟上述一致。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云:1966年8月,“文革”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打、砸、抢、烧“破四旧”……到了12月中旬,各地“造反大军”纷纷出笼,扭转了前期专整群众的局面,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成了批斗对象,一般平民百姓从人人自危中找到扬眉吐气的机会。陈墨“文革经验”亦是。当我这篇文章初稿写毕,浏览2018年1月13日“陈墨之博”时,邂逅《我的“文革”经验》一文:
我的经验是:文革初期,打人、斗人、整人的都是红卫兵(髙干子女红二代即北京“联动”及各地“土联动”),待到造反派革命组织纷纷成立,斗争方向指向了“资产阶级当权派”后,被压抑十多年的仇恨如火山爆发,易帜以来唯一 一次民打官、民斗官、民整官“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暴力复仇运动就在全国漫延起来。但时间很短,死人也不多。
……一句话,毛指引的“革命形势”既然己由“阶级斗争”转为“路线斗争”后,正是地、富、反、坏、右们在夹缝中天赐了喘息之机。
……所以,我觉得“文革”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当权派”从上到下全部垮台时,作为一个黑五类狗崽的我,好像每天都活得很幻想,很机会主义,甚至很逍遥很亢奋。
——这是一个“文革余孽”幻想“失去的天堂”么?显然不是。从哪个方面,都说不到那儿去。有意思的是,高尔泰《寻找家园》中有篇《牛棚志异》,也说到类似“有趣的事儿”,“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如海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日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
不管“宏观叙事”,怎样翻云覆雨。可个人经验和心理,包含着更真实的信息。仅从这个角度,我想也可以得出,“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的结论。再看陈墨在1992年时,所写《关于“工于谋人,拙于卫己”》一文的叙说:
我有一朋友,是孤儿,在民政局下属之孤儿院长大。初中毕业后,在民政局下属之“假肢厂”当学工。未及半年,竟被其厂长以“现行反革命罪”送去劳教七年。此事纯系冤案。……文革初,他约了我们几个朋友帮他回假肢厂“造反”,闯入厂长家,从床上将其提起,本欲一番“暴打”,以解七年牢狱之仇,无奈全家老小七八口跪于我们面前,言说:“前几天已被本厂造反派将另一好腿打断,若再打,必死无疑矣”(假肢厂领导全系残废军人)。我们只有作罢。站在朋友角度,此人烂用职权,草菅人命,实属可恨,该打;但他本是残废之躯(少一腿),而今非但手无寸铁,且卧病在床,可怜得很,下手打他,于心何忍!于是,文革初造反派“灭絶人性”的斗“走资派”行为,既有它的符合伦理的正当性(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也有它“无法无天”“群盲群氓”的反动性(反人性、反文明、反法制、反理性)。只不过这行为是假“保卫毛革命路线”而生,毛之号召,即为授权。故一夜之间,原有“权力”,全数瘫痪,红卫兵和造反派才可能“说斗那个,就斗那个;说整死谁,就整死谁”。
九九《魂断台北》一书,也讲述了一则“阶级报复”的花絮:
办事处主任长期对我的歧视,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早已不满,于是……在批斗大会上,我和生产组几个小伙子把几个头头揪了出来,趁机在那主任的背上狠狠地挥了几拳,出口恶气,心中默念:给老子欺压百姓,整人害人!不安排老子的工作!
殊不知这幼稚真切的露面和几个拳头,让我失掉了工作:咋“四类分子”的娃娃都造反了,是不是阶级报复?!台下群众七嘴八舌,谣言四起。……
《魂断台北》一书中,更是津津有味地讲述“跟着陈墨偷书”的趣事。不仅偷书,还要贩书,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找书的好机会”。陈墨《书话——偶然得之》陶然写:
到了“武斗”期间,造反派们只顾“消灭对方”,对文化的革命稍松。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黑书市”如同野草般自然滋生出来了。先头还只是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诡诡秘秘,像黑市买卖票证;到后来干脆摆起了地摊,把所有“封资修”禁书都冠冕堂皇地摆将出来,且公然高声讨价还价。全盛时整整一条百多米长的街道被书摊人流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场面壮观闹热。……当然,也有过几次被强拉回现实的时候:造反兵团猛地开来两车“武装”,街两头一堵,逐个搜身,将缴获之各种书籍在街心堆一座小山,放火一烧,完事。只有个别不甘于损失且“不依礼不依教”,不识时务的家伙,被“武装”们的皮带抽得满街乱滚。
然而,纵然如此,“黑书市”断断续续还是维持了两年之久,直到 “清阶”运动,当局大量抓人,风声鹤唳,到处弥漫着恐怖气氛,这明目张胆“不革命”的文化现象,才告销声匿迹。
无疑,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的“黑书市”成为成都文革史中一道与其时代色彩反差极强的风景。而且据我所知,在全国大城市中,这“风景”绝无而仅有。
——“对文化的革命稍松”,就是陈墨们的“黄金时代”。邓垦《〈空山诗选〉始末》一文,更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述那时候的逍遥自在:
1967年5月,……我像难民一样背包打伞回到了成都,躲在号称“解放区”的东郊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即现电子科技大学),同父母住在一起。7月的一天,陈墨匆匆从“国统区”的城南穿过一号桥“封锁线”溜到我家,说想在东郊租一间住房。
……更使我眼前一亮的是,成捆成捆的书籍往几个书架上一放,整个房间顿时大放异彩!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卧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现实。我和陈墨梦寐以求的卧榻之旁书相拥竟成现实。陈墨一脸得意,说:“上头抢权,下头抢书,各革各的命!”好一个嗜书如命的陈墨!我无“贼”胆,“傍”上这样的“富家”,何愁无书可读?
……1966年5月我在名山县参加单位技术“培训”,休息时在一家小书铺淘得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王瑶着《中国新文学史稿》,竟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眼下陈墨“暴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怎不令人欣喜若狂?红卫兵们忙着“玩命”,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成了李金发笔下的“弃妇”,也成了陈墨们翻墙撬窗窃取的目标;而在春熙路“黑书市”上,陈墨独具慧眼,专挑有关中国新诗的史料用其他小说交换。这一大堆被长期封杀的民国时期的诗选、诗集、诗刊等,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开拓了我们的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诗艺。于是,每天,在高音喇叭“踏平东郊”的吼声和呼啸而过的枪弹声中,我们躲在松柏村的农舍里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便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读诗、品诗、论诗、抄诗、选诗、写诗”……的确“时空大错位”。难怪后来诗人罗鹤,以“野草桃源”概括。据说当时,“梦兄周围诗歌爱好者越聚越多”:
当时,“发配”到会东的徐坯,“发配”到攀枝花(当时称渡口)的何归,“发配”到云南开远的明辉,“发配”到喜德的张基,“发配”到宜宾的罗鹤,“发配”到乐山的九九,“发配”到甘孜的白水,“发配”到资阳的蔡楚、谢庄等,都已先后“逃”回了成都,加之稳坐成都的吴鸿、杨枫、冯里、万一、樵夫、兰成、乐加等人,一张被“诗”牵着的网撒在了成都的各个角落,相互之间抄诗、写诗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时,为了混淆视听,大家还乱七八糟地取了各种笔名。 (邓垦《〈空山诗选〉始末》)
真是好日子,“吃着火锅唱着歌”。有陈墨《满江红•诗友》为证:
夜竹秋风,薛涛井、蛙声互答。
想当初、枇杷楼下,好诗齐发。
隔叶川鸣香草梦,调轸弦待伯牙匣。
理素笺、字字有玄机,情难察。
——看他们兴高采烈,作为读史的人,“好像时空大错位……以为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文革”。不过定神想:有什么不可思议?宏大叙事是一回事,个人生活是另一回事。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人与“主旋律”不一致,何况“主旋律”也时常变的。
看着他们“蛙声互答”、“好诗齐发”,让我想到戈蒂埃《珐琅与玉雕》序诗所写:
不管那狂风暴雨敲打我禁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与雕玉。
我的看法是,作为“哀苦之辞”的《落叶集》,不会是这时候写的。
当然还要,做更细辨认。当然还要,把陈墨的写作拉通来考察。拉通考察的话,《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中,有标明为文革期间写的。如1966年底《草堂独游》,1967年《山寺》、《自宫》、《简约》,1968年《零碎的爱》、《薛涛井畔》、《人迹板桥霜》。还有深受邓垦推重的《独白•我要把忧愁忘掉》——“我以为是陈墨迄今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诗,却有着小说的份量,优美反复的吟咏中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如再扩大范围,还有1969年初《超声波》、《无人在听》,1971年3月《记住而已》、《也许不难》……
上述作品时间跨度大,风格也不尽相同。不过即便如此,也还是跟他写于文革之前,可以叫“前期的前期”的作品,有着可辨的不同——既跟时代有关,也跟自身有关。
如《人迹板桥霜》(68年12月)结尾:
我只是这白夜的黑烟?/飘荡就干脆消亡罢/这世上太多并不认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认真的机关
——“并不认真的死”,或与文革武斗有关?当然我的解读,只是一种可能。去掉“武斗”的背景读此诗,我以为也是完全可以的。本来么,“这世上太多并不认真的死/和死前太多认真的机关”,人们本来很容易把更重大的事置之脑后。今年元月,王怡发来一首《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第一段写:
献给成都,一座失败的欲望之城
人们随随便便地去火葬场
不讲究,不化妆。随随便便地
就把亲人的身体倒掉
——讲述的也是,漫不经心的死。所以“诗史互证”,只是一种路径。
再看收入《灯花集》的《超声波》(1969.1):
因为你叫蝠/黄色的热望/便以丑为美/并登堂入室/在皇王的卧榻之侧/放心入睡
工具交媾/夕阳宣称永远不落/蝠在烈焰中/涅盘为美丽的/向日葵/超音速地繁殖/只有一瞬/山河顿时变色
还有收入《灯花集》的《无人在听》(1969.2),“诗、史”纠缠形成“复调”:
烈日孵化出/阶级的家谱/小红书燃尽/硝烟成灰/这一页翻不动/撕不下 只好/就地掩埋/杂乱无章/露胳膊露腿的/埋与被埋者/都不敢呻吟
白天比夜更泥泞/子时 华西坝/老协和大学的钟楼/仍旧准时敲了/十二下/但无人在听
外部世界是一回事,个人生命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地讲,陈墨写于“文革”中的作品,颇有一些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我爱”的意志强烈。如《草堂独游》(1966.11):“我爱寂寞,寂寞的黄昏/蜻蜓的翅儿带着透明的水声”;《山寺》(1967.4):“我爱山寺的黄昏和清晨/我爱林下是泪様的苔痕”;《零碎的爱》(1968.10):“我爱——/顺着采珠女圆滑的胸脯/流淌着的那甜的/不,分明是咸的海水/我更爱——……”;《独白》:“我爱我宁静的伤悲/在雨中看菊花悄然地憔悴”。此外,还有《在你家门外》(1968.5)、《她要远去》(1968.10)、《潇湘馆》(1969.10)、《惠的风》(1969.12),《黛玉》(1970.9)、《无法拒绝》(1970.12)、《难免无奈》(1971.1)……
好不好说这些“情诗”,构成一个“有情世界”:
是天邉有颗小星向着我蒙眬的笑/这苦涩的日子才有甜蜜的心跳
用不着细看,跟《落叶集》不同。据刘国凯描述:“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基层文革泥泞路》)考虑到“史”的情况,对照陈墨此时的“诗”,诸如《独白》之二“我爱我宁静的伤悲”,之四“我终于惨然地微笑”,之六“我唤来的只是个凄然的春天?”之五“我要在我的秋天裏沉默”……会发现跟《落叶集》,还是很不一样。借用臧克家早期的诗句,则《落叶集》完全是“深闺无眠的心,将把这/做成诗意的幽韵?/不,这是生命的叫喊,/一声一口血,喊碎了这夜心。”(1934年《生命的叫喊》)《落叶集》是“生命的叫喊”。
那么六、七十年之交陈墨的诗呢?且看写于1971年3月的《记住而已》:
记得一朶小白花从墙头探出/记得荒凉的髙坡上有间破茅屋/当生命只是而已的时候,请记住/精卫鸟永远都在中途
记得一片冰心最宜装在玉壶/记得雪中的芭蕉长得特别緑/当存在的风想穿过而已时,请记住/阴阳鱼永远都在相互追逐
记得沙漠中不会有飞瀑/记得槐树下总少不了蚍蜉/当而已的尘埃拂去又来时,请记住/秦时月永远都填不满希望的空谷
记得荣国府的石狮子总是在哭/记得美梦邉的黄粱总也煮不熟/当智慧企图超越而已时,请记住/饮江鼠永远都不过仅仅满腹
再看同一时间的《也许不难》:
月光清淡,似水流年/青铜器把该坚守的守坚/夕阳盲鼓,故事飘散/唤不醒无处赊酒的诗僊
还未赊到的酒在诗中飘散/白云苍狗,斧柯已烂/散不开的故事已长满緑斑/松下残局,鏖战正酣
十年一觉,芦苇折断/禅房中的腊梅开得空幻/篆香燃尽,轮回懒转/海风吹涨等待的云帆
还在海上的筏原地打转/万刼如雨,百梦千幻/金刚经的苦涩悬在眉间/一念死寂,也许不难
这些诗很落寞。如“白云苍狗,斧柯已烂”、“十年一觉,芦苇折断”、“一念死寂,也许不难”……但再落寞再消沉,跟《落叶集》都还不一样。“当生命只是而已的时候,请记住/精卫鸟永远都在中途”,你可以说跟《落叶集》中“而海上的精卫/来去无痕”(《骨灰》)形成互文,也就是呼应。或者在重复吧,不过我觉得,《记住而已》更有底气。“记得雪中的芭蕉长得特别緑”一句,已经把来龙去脉都说清了。
——结论是:《落叶集》的写作,不会与之同时,不会在“文革”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