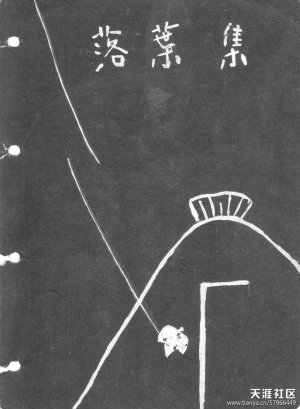九、“如这锦江,锦已走、江并未走”
叶子被风吹落/又被风卷走了 (《残萤集》)
不必担心/太阳已走/不必担心/岁月已走/暮鼓已走 晨钟已走/都不要紧 蚕马/蜕去第一层皮/飞翔的梦并未走/如这锦江/锦已走/江并未走 (《已走》)
钟嵘《诗品•序》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对于弃儿陈墨而言,“诗歌拯救诗人”。现在的他,像极了曼德施塔姆:“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沃罗涅日笔记本第一册》中有这样的诗句:“你们剥夺不了我蠕动的双唇”,“是的,我会躺在地下蠕动双唇”。理解他的布罗茨基解释:“要知道所有的创作实质上就是自己的祈祷。所有的创作都指向全能的耳朵。艺术的实质本身就在这一点上,这是无条件的。诗歌如果不是祈祷,也是用与祷词同样的机制来运行的。”没有谁能阻挡,人向上帝说话。哪怕你绝望:
图腾/比耶稣早一步/复活/人类在回头路上/纷纷举起了屠刀/血流成河
(《一步之遥》,1965年6月)
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程一身译)进一步写:“身在古拉格集中营的曼德尔施塔姆疯狂地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这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事实,他注定要沉沦被消灭。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切斯拉夫•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上海文化》2011年05期)我想说,一辈子都“是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从来没有上场的资格”的陈墨,似乎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又像1945年,从集中营回来的诺曼•马内阿,有人给他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诺曼•马内阿:《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3月,第3页)
对于陈墨来说,文字亦是奇迹。现在看他1966年10月所写《趁着》一诗:
我必须把我从文字中唤醒/趁着因果的微雨洒透了清明节
收入《灯花集》,写于1965年6月的《奔乱的脚步》:
为了美/传输带不会停下/但人心可能暂停/空谷脚音般地/玩味自己的心跳/——如果山垭那邉/还没有及时吹来/裹挟着雨雪的/寒风
《残萤集》中许多小诗,令人爱不释手:
爱之天性/如轻燕吻波时之敏捷
我该庆幸:/在任何牢笼裏/总会有新鲜空气吹来
当社会变得愈来愈无趣/有趣的文字可以拯救灵魂
诗句飞翔时固美/但当它跌落最终竟能/死裏逃生一飞冲天时/更美
雨冲击着荒原上的一棵小树/我理解/这是上帝对它的爱
芳心之培育/有待春风吹进心坎/一轮月、一枝柳/或一声洞箫/虽寒而不酸/那是苍凉/不是苦力/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衫
用笔/刳木为舟/用舟/横渡苍海/遍泛五湖
诗的故乡的涛声/在眼花缭乱中/渐渐清晰起来
窝里稻草暖身/梦中文字暖心
《落叶集》有些诗,本身透露“怀念与诗思”:
怀念毋须孵化/石碓起起落落……像我的诗思/潜入春夜/我与你的杯中不空/惆怅渐浓
(《得》)
于是有了《落叶集》。于是有了《我早期的六个诗集》。于是有了陈墨的半个世纪。
以后发生的故事,很像1940年的阿赫玛托娃:“你没了,对这哀痛和崇高的生命,/四周鸦雀无声,/唯有我的声音,像一支短笛,/在你寂静的追思会上响起。”一种“迷了路,该怎么办?”的自问,却又自答:“你还没有死,你并不孤单”。以后发生的故事,很像1910年时,才十九岁的曼德尔施塔姆:
从凶险和泥泞的沼泽中
我悄悄长大,像芦苇般沙沙有声,
既迷恋,懒散,又温情地
呼吸着被禁止的生命。
我叶片低垂,谁也不会发现,
暂时栖身在冰冷和泥泞里,
只有短促的秋天
用低声的问候向我致意。
以后发生的故事,用陈墨的自我书写,则——“暮宿苍梧,朝游蓬岛,朗吟飞过洞庭邉/循规蹈矩,战战竞竞,泡菜捞出艳阳天……出入无踪,往来不定,半是疯狂半是癫/白天苦力,晚又失眠,荒漠甘泉早已干”。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同样写:
我们大多数人既非诗人也非史家,但我们仍会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亲近叙述这项活动,因为人有回忆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叙述中,这些事件把我们自身同他人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经常迸发“诗意”。从最宽泛的词义上讲,“诗意”是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可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它喷涌而出。……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
此后的半个世纪,陈墨以其《落叶集》和不同时间对“叶子老师”的不断书写,使“叶子老师”在叙述的世界中活得比肉体凡胎更长久:“上帝不会让落叶返枝 正如美才能让 在污浊的急流中的灵魂 上岸”。与此同时,他又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人生艺术化”:“叶子告诉我:/把人生凝练成一句诗/够我一辈子努力”。
一个唯美主义者,语言的炼金术士。我们时代的“炼石补天”者:
……我差不多是把汉语语言的纯洁当作“天”,而把“封建传统文化”、“极权统治的霸语话权”以及“后现代的文化现象”等视为“天的破洞”。虽然,这“破洞”仍以熵速在迅速扩大着。
我的文学,就是我的“炼石补天”。
(《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一 补天》)
一个穷处陋巷,“想用这块石头,砸开混沌的存在之域”的亡命之徒:
……《红楼梦》结尾,寳玉离家出走,不知其终。后人瞎猜,有说进了佛门,有说随了道士。我说,他哪也没去,穷处陋巷,箪食瓢饮,写他的《石头记》。想用这块石头,砸开混沌的存在之域。
(《关于“身心”》)
说到底,一个追梦人:“若不幸与我同时,当了黑五类的待业青年/跟我一样,一定把那坠落的黄叶梦绕魂牵!”(《叶子老师教我象征主义诗歌》)一个“有文死更香, 无文生亦腥”(孟郊)的信守者。说到底是,一个毕生的“美学青年”。像古人说“自然成啸傲,不是学沉潜”(陆龟蒙),也像纪德称:“我倾向于相信自己有一种使命,一种神秘的生命。”
的确有一种,“时日曷丧”的劲头。其《导师-禁书-文学险途》一文写:
……他无情地打碎了我的一个梦 (作家梦),却精心构筑起我的另一个梦:这个梦让我义无返顾地爱上文学,爱上诗歌;这个梦让我终身对平庸的泥沼怀着深刻的敌意与戒心;这个梦让我奋斗向上,刻苦学习,却与生存无关,甚而相悖;这个梦让我的人生得以充实,却教我痛苦不已,因为它既无彼岸,又让我看到太多人世间的残酷与肮脏;而且还让我别无选择,不愿从这个梦中醒来。
与《落叶集》同一主题,大概略晚的古体诗词《雨淋铃•怀叶师》云:
云遮明月。
望羌笛处,隠隐落叶。
清光染上残柳,渔舟唱晚,声声乌鹊。
也许从来无果,隐士总碧血。
想过去,陶潜辞官,也把躬耕写髙节。
而今我仍笼中鳖。
孤零零、扎扎争争辙。
白天苦力挥汗,青灯下、与前贤约。
遍泛江湖,寻觅终身自由不缺。
直到那石烂海枯,誓如恩师洁。
九九《魂断台北》一书中,讲述了一则他“犯上”的故事:
陈墨,是我的师友,他和我一样,都出身“黑五类”。
1965年,我初中毕业。在一次街道办事处主任对全体社青(待业青年)训话的大会上,陈墨君大胆的表现,令我印象颇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街道办事处,是管理你们的地方,到办事处不要老是伸手要工作,要知道,你们中间各种人都有,要接受监督,改造思想,只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我们才可能安排、考虑他的工作,有些人调皮捣蛋,不参加政治学习,对现实不满,简直是害群之马……”刘主任说着话眼光死劲地盯向陈墨,几十上百个待业社青中,不少眼光也一齐投向他,只见他哗地一声站起来大声道:“我们不是牛马!”说罢转身而去。敢公开地顶撞办事处主任,等于是提前摔掉自己的饭碗。全体社青,无不惊愕。
这句当时属完全“犯上”的话,使我对他肃然起敬,这句话出口也使得他好多年没有被分配过工作。
罗清和《方脑壳传奇》第十七回“报旧仇痛打水二娃 递情书又成假老练”云:
正在这时,过来一位全身着黑,二十多岁的书生,招呼老九道:“九九,这个水二娃是我邻居的侄娃子,他虽是毛贼,却有点义气,现已改过自新,你就放他一马好了。”接着他又回头对水二娃道:“今天的事情对你算是教训,常言道,一个鸡蛋吃不饱,贼名却要背到老。你今后要走正路,勿再作奸犯科。”水二娃见来人替他讲情,慌忙拱手称谢,拖头鼠窜而去。
来者姓邱名墨砚,也出生在锦江河畔。为人刚直,好文,素有锦江才子之称,十几岁便同毛月梦诗文唱和,的确才高学厚,为人景仰。……水二娃走后,老九指着邱墨砚同大家相互作了介绍。罗汉见他全身着黑,联想毛月梦经常提到的绰号“黑乌鸦”的诗人,听说他便是邱墨砚,连忙点头称道久仰。
《方脑壳传奇》(续集)第一回“孙九路锦江惊旧事 陈罗汉恬淡忆往昔”交代:
孙九路同陈罗汉在锦江河畔背着手走了一段路,突然问陈罗汉知不知道,丘墨砚为什么全身着黑的原因?问完见陈罗汉没有回答,主动解释说:“墨砚兄之所以全身着黑,是在无声抗议,抗议这个社会没有光明。墨砚兄说,旧社会,成都有个叫刘诗亮的才子,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走,别人问他这是干啥?刘才子说没光明,看不见,墨砚兄就是在学那人。”接下来,孙九路情不自禁轻声唱道:
“星星月亮那样暗淡,江涛仿佛为我吟叹,我凝望呀凝望着天边,几时才有晨曦的光烂……”孙九路唱完,解释说:“这歌词也是墨砚兄写的,内容表达了他对光明的向往。”
——书中“孙九路”,就是九九。化名的“邱墨砚”,正是陈墨。
王尔德精辟讲:“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传奇。你永远不该摧毁传奇。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对一个人的真实相貌略有了解。”毫无疑问,不该摧毁传奇。而叙述在宇宙时空中,也有它自己的位置。
话该说清了,又猛然想到——为什么是陈墨,一个“引车卖浆者”?
一方面是人们抱怨:“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学术与思想,恐怕称不上一部真正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时而虚假繁荣,一哄而起,时而万马齐喑,遍野寒蝉,由此造成士人内心之畸型残破,大概只有起龚自珍于地下,重写一篇《病梅馆记》,方能描述。”(朱学勤:《我们连“愧对顾准”都不敢说》)这是确凿无疑的。可在另一方面,“黑衣人走过板桥”……
看来陈墨想过很多次。一次是1998年,读孙静轩长诗《告别二十世纪》后写:
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粗话”,即“粗人”常挂在嘴边的那种“日妈倒娘”的脏话或流活。不过现在时代进步了,“粗人”概念有了质变:过去引车卖浆所谓干“粗活”下体力的最底层人民,近五十年却充塞了不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被历次运动清洗出共产党的“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大量的右派和整整一代知识青年。而坐轿子的则多系泥巴脚杆,斗大的字认不到一筐。所以,以社会地位之上下来划分人群文明程度、文化水准的“粗细”,显然不再准确,也行之不通。
(《粗话——孙静轩长诗〈告别二十世纪〉读后》)
一次是1987年笔记,2015年初改《关于八僊——道家标榜的理想的八种生存状态》一文中,专门有“成都散僊”一节:
六十年代初,人民挨饿,国家困难,很多冒进的国营企业纷纷“下马”(倒闭),大量人员堆积在底层“待业”(找活路)。于是有了一个新名词,曰“社闲”(“社会闲散劳动力”之简称,其实就是“失业者”)。叶子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其他社闲尚属“主人翁”,而他是“专政对象”(黑五类),虽同样卖苦力,肩挑背磨,政治地位却有天壤之别。然而,向来并不把“主流”当回事的成都苦力们,却不买官方的帐,而将自己这个“浑身解数,用以刨食”的群落,自称为“散眼子”或“散僊”。散者,散漫无归之谓也。
“散僊”们的活法与审美,天然地接近道家,而对主流的“冠冕堂皇”,嗤之以鼻。——这种底层文化,也许由来已久(几千年),也许天府之国生存不难,依赖君国社稷较少,独立本能,得以天造地设水到而渠成。
我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的。
再一次是2006年6月,回顾自己的“胡适阅读史”时写:自己读胡适,同绝大多数国人不同步。记得文革到了武斗时期,全民已疯狂,有些地区毁村灭城,人成千成万地死。“而我则在枪炮声中直接进入二、三十年代,象当时的读者一样,读着胡适”:
……因我是社会最低层靠卖气力营生的“闲民”(官方叫“社闲”或“社青”,即那种做建筑工地担抬挖气力活临时普工而无正式单位者),所以可以游离于整个社会风尚、运动、政治之外,充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不读那全民必读的烂书和社论,而去读胡适。
我是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从来没有上场的资格,命中注定人生苍白、终身庸碌。是胡适他们的五•四新文化改变了我,重铸了我,让我和另外一个我分裂开来。
(陈墨《我读胡适——为冉云飞网上“我读胡适”征文而作》)
此段文字,可圈可点。“这个制度的贱民与弃儿”,“可以游离于整个社会风尚、运动、政治之外,充当一个置身事外的观众”,可以从从容容地去不读那全民必读的烂书和社论,而去读自己想读的……一系列“可以”什么意思?老实说,需要细想一下。就像高尔泰《寻找家园》中有篇《面壁记》,“身份自觉”地写:“这些洞窟壁画,以前都曾看过。但是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待罪之身,手持箕扫,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
——面对“待罪之身”,需要细想一下。不同的身份,怎么一样呢?就像文革“造反”大潮中,造反派与保守派(保皇派)怎么能一样呢?哪怕同为造反派,代表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底层群体利益的“红造总”,与那些国营企业尤其是军工大厂的“工人阶级”又怎么一样呢?……当然这是,社会史的眼光。很高兴地看到,在文革研究领域,有了“社会史视野下‘文化大革命’研究”(如董国强)。还有已故的杨小凯先生,早已注意到文革造反中“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网上浏览中,注意到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识背景》一文,也发人所未发。他说参加过文革的大知识分子,很难看到深刻的思想;“那时许多异端—先行者,往往属于边缘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单枪匹马”:
在文革前的主流话语系统中,视市民阶层为异己力量,用“社会闲散人员”、“社会渣滓”等含糊的贬意词来称呼。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不含辛茹苦地挣扎求生。……除去反抗歧视,争取现实利益以外,市民的另一特征就是他们基本上游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以外。政治运动都在单位内进行,市民阶层就是没受过或很少受过传统的政治教育的那部分人,他们习惯以常人的立场观察文化大革命。这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时,常常站在被压迫被损害的一方面。
一位原中央文革的记者说:“在干部队伍中,往往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反而较早地接受了‘左’的思想。”(张云勋:《贵州夺权前后–一个记者三到贵州所了解的片断情况》,搜狐博客,2010)这也是当然的,因为“左”的思想,尽管很“左”,但终归是思想。有思想和无思想是很不一样的。
他把自己的思考,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这不是偶然的现象。站在无组织、散漫、被人所轻视的市民背后的是多元化的社会;而其面对的则是党和国家,是僵硬的斯大林体制,是国家对社会的吞噬。所以这一对立,实际上是社会PK国家。”——看到这样的论断,我又一次“如受电然”。无独有偶的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有类似发现:“在那段严酷时期,工人家庭里的谈话要比知识分子们的谈话开诚布公得多。”无独有偶的是,讨论“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时,北岛有类似眼光。其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讲:
《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我的确想到:表面上看铁板一块的“大一统”社会,或许在“国家”之外仍有“社会”的空间?由于他们肉身和头脑未被“单位化”、“组织化”,由于“他们基本上游离于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以外”,而使“礼失求诸野”的古话在今天有了新的意义?虽然从传播角度讲,肯定处于占位的不利……的确想到这个方面,想到“大地和尘世因素”。就研究路径讲,是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争之实是,近年来研究范式发生转换,革命的“合法性”与新文学的“先进性”受到挑战,“对‘多元共生格局’的强调意味着已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整全的历史叙述框架来替代过去革命史衍生出来的现代论述。”(程凯:《“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针对性》,《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
我要强调的是,“地下文学”的研究中,尤需此种眼光或自觉。若用陈墨的话,即是“成都散僊PK单位体制”……细思之,此种社会史的视角,与理论上“深处的美学”是重叠的。王尔德《自深深处》云:悲怆中自有圣洁之境。“不止于此,关于悲怆,还有一个严酷的、非同一般的现实。我说过我曾是我这个时代艺术与文化的象征。而同我一起呆在这不幸的地方的每一个不幸的人,无不象征着生活的真谛。因为生活的真谛即是受苦。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就是这个。”他的话,我们中国人容易听懂。自古以来发愤著述(司马迁)、“文穷益工”(韩愈)、“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等等……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是我想到,对“中国当代地下文学”的开掘来说,它或者具有更特殊的指导意义?
汉娜•阿伦特如是讲:“通常,一个时代在那些最少受它影响,距离它最远,也因此遭受最多不幸的人身上打下它最清晰的烙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如是写:
思考吧!从你的苦难中做出结论吧。
……监狱是思考的好地方,劳改营也不坏。主要是因为没有集会。十年之内你摆脱了任何集会!这岂不等于呼吸山间的空气?……头脑的自由 ——这难道不是群岛生活的优越性吗?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