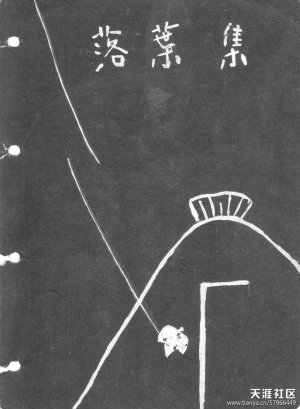尾声·魂兮可以归来
“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蚯蚓》)
——目前难说。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墨表达“独白的无奈和无奈的独白”:
……几十年来,我为了创造“奇特的自由”,吐“思”作茧,自我放逐自我封闭。这无疑是一种变态,——孤独的虫对“自由”的创造性变态。或许,这也正是庄子“蝴蝶梦”的全部内涵。每当我的心中生出对人类“可悯”悲情的时候,我知道,我正用我美丽的翅膀飞向苍穹。--也许,我根本飞不出这“城堡”,也许,我会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夜悄然死去。但我毕竟飞过了。我自信我已超越了屈原,超越了东坡和张岱,超越了余光中和张爱玲,超越了所有失语的人和把艺术用于 “功利”目的的人。
然而,我的眼中仍有一滴清泪,因为我仍然孤独,而且我清楚自己并非真正的旁观者。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所表述的,还是一个文化政治或传播学的道理。
2012年11月20日“陈墨之博”,在《桃花扇》、《暗香》、《解语花》题下按语:
所谓“集”,又不能见天,不过抄在活页记事本上,满足心理上一种虚无飘渺的虚荣罢了。然而,我们这伙热爱诗歌的“黑五类狗仔子”,却全靠这点虚荣,才活了出来,最终也才稍微活出了个人样。
但是怎么说呢?“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这一问很重要。
2000年8月,陈墨《茶铺派文学“理论”现编之三 理水》一文揭发:一方面,当代政治“以人民的名义”用文字狱、吃掉了一大批文人;另一方面,这政治的紧箍咒如此这般地就异化掉所有不再敢发任何杂音的苟活文人。于是,在“红海洋”、“红歌潮”的背后,是万马齐喑与噤若寒蝉:
……如此,我的文学也许才算得上是纯粹我个人的:蚂蚁告诉大象,你可以踩死我,但我不服!纵然十三亿蚂蚁都服了,我!也!不!服!
因此,我也许在纯“不服”的写作中,才能找到点点自由和小小乐趣;才能证明自己有血有肉的存在。而不是他们十三亿中的那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既可忽略不记,又可随便代表。
“犹有野夫肝胆在,空山相对暗吞声”——这一点很重要。用汉娜•阿伦特的话: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作者序”,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
经过半个世纪的蛰伏,决心从洞中爬出来——没人多少人围观、打量?不要紧!
已经是一项奇迹,一项了不起的胜利。了不起的苏俄女性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讲:“文章有很多种丢失的可能,比得到保护的可能性更多。……得到保存的所有东西,都是奇迹显现的结果。”“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保住了这些诗。如今诗不会再丢了,应该把这视为一种成功。”针对一时的不被认可,她不在意地讲:“谈论一位诗人不被其同代人所承认,这样的话题是天真的。为诗人感到高兴的人和因诗人而发疯的人,都能立马辨认出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诗人能让许多人生气和发疯。”(《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264页)
诗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在我们过去的时代,曾有“但是洛阳城里客, 家传一本杏殇诗”的传奇。可更多的,是“前辈有谁同此恨,雪庵和尚读《离骚》”(方文)的默默接受。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出现“……这也算现代中国诗歌史上的怪事一桩”,说怪也不怪。它本身印证着《河满子 •双十节》(在博客上注销时,改题《河满子•国庆》)之真实不虚:
吟断求索之句,未见启明之星。……五柳难隔风雨,孤心今夜苔生。
只有尽其在我、安之若素。美学家高尔泰讲:“如果一个人面对古代的东西,比如原始洞窟岩画、埃及法老陵墓或者希腊神庙,只能看到它们的考古价值,看不到那些个里面至今活着的审美精神,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人文。如果一个人读了释迦牟尼、柏拉图、老子、庄子、李白、杜甫,说是‘至今已觉不新鲜’,那么这个人不足以与谈历史。”(高尔泰《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写:“对科学和学术来说,时间的流逝是废弃旧物的缘由……艺术和文学作品则不然。如果它们在自己的时代就不算上乘作品,那么它们就会湮没,在大多数情况下,永远不为人知。但也有例外,有些作品一开始被任命错误地评判,任其湮没,后来却被重新发掘,成为被人们大量承袭的积存中的一部分。”(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月)生活与写作环境跟我们比较接近的索尔仁尼琴,这位曾经的“深水鱼”在诺奖受奖演说中一再致意:
……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其实中国文学也不曾停止过,哪怕在外界看来似乎是一片荒原……2005年6月,我们的朋友王怡在第71届国际笔会年会上,做题为《我们不是作家,是人质》的发言,提出“在我的国家,所谓作家,不过就是有能力通过文字、通过写作而使自己活得不像狗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从 1979年开始主编一份民间文学刊物《野草》,直到2004年因某期杂志被抄家。他在接受国外文学研究者采访时,拒绝透露刊物同仁们的真实姓名。他谈到一个“以笔名行世”的概念。数十年来,他以笔名和朋友和世人相交。他的真名在肉身的世界中反而不显。他的真名,几乎只留在政府颁发的各种证件、各种隐密的档案中,只留在那些被专制权力辖制的领域。换句话说,当他以真名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人质。他的笔也不是笔,而是一副镣铐。
笔名是什么,笔名就是自我的命名。除了躲避政治危险之外,笔名是卑微者抵抗肉身世界中的屈辱,使自己活在另一个国度的护照。在一个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制度下,笔名是他唯一与灵魂同在的名字。对我来说,写作使我的真实姓名成为另一个名字,一个符号相同但价值迥异的笔名,一个不被我的政府压迫的、属灵的名字。对我这位朋友来说,他选择以另一个名字行在世上,意味着他至少有一部分是高贵的,是未曾屈服在政治权力的压制下的。是不由这个世界统治的。
他指的是陈墨。请看自订《陈墨小传》:
陈墨,字砚冰,成都人。父姓何,母姓陈,故本名有二,乳名阳生,绰名乌鸦,另有笔名秋小叶、一丁、何必、何苦、野放等,一度曾冒名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或问:“一个苦力有这许多笔名,岂非画饼充饥乎?”答曰:“官方文坛多用本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学多用笔名——聊以禳祸耳,时代使然,身不由己。再举例说,写下以上文字,则早被何必、何苦骂得狗血淋头也,则又系时代使然、身不由己也。信否?”
——如此这般,是“隐微写作”上升为“身体写作”,或者说两者合一。用陈墨话讲,当身、心无法统一时,只有“人格分裂”一途。用某高僧的诗,即是“但能触处回光照,莫被尘劳困主公”——“主公者,精神的自我也。因此这禅机等于说——用自强的种种不自由,换来陈墨的点点自由。”(《清言小品》)“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的媚俗观——野性的证明》)
陈墨及其诗友的半个世纪,恰如赫尔岑描述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意识一旦觉醒,人就会带着厌恶的心情看到他周围的丑恶现实”:
要从这阴暗的时代中吸取空气,必须具备另一种气质;必须从小就习惯于这种连续不断的、狂吹猛打的寒风;必须对无法解决的疑问,对苦难重重的现实,对本身的软弱,对每日的屈辱,能安然处之;必须从初离襁褓的岁月起,就具备隐藏一切激情的习惯,不仅能把它埋在心底,不使消失,而且相反,能使潜伏心头的一切在无言的愤怒中日趋成熟。必须善于为了爱而恨,为了人道而憎恶;必须拥有无限的自豪感,能够在脚镣手铐的束缚中,把头高高抬起。
(《赫尔岑论俄国文学》,项星耀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3期)
我花了很多时间,论证《落叶集》写作时间。不是单纯搞考证,不是单为一本诗集,也不是单为陈墨个人。而是想以这种方式,向已逝的叶子老师,向跟他一样的人,“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想以这种方式,为中国的地下文学招魂。想以这种方式,为陈墨和他的诗友,为跟他们一样的写作者,“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写作者寻求理解、帮助和见证”(王怡)。我想尽自己的学者本分,为故国招魂。
2014年8月8日,前年10月去世的民间思想家、文革研究者周伦佐,估计我从德国旅游回来后,发来邮件说:
陈墨当然值得研究和评论。不仅人好,诗作也极其难得。在那个绝对专制主义年代的同龄人中,能够写出这种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思模式和表达方式之作品者,极其罕见。
能够一生与诗相伴是幸运的,无论诗歌是否在名利层面给作者带来成功。
当然而今眼目下,《我早期的六个诗集》就算“见天”了,又能怎么样?包括我花力气写文章,能有什么效果?内心是怀疑的。“野草自緑,不望发现”(《读钱杂记 二十二、关于“隠士”》),这是陈墨自我打气的话。我能东施效颦吗?写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为“解码”,本来就是想“广而告之”……但是的确,无“考古惊天下”的自信。怎么办呢?也只有尽其在我。再说,毕竟研读历史的人,多少有一点历史眼光。尤其是冷静下来,想到阿伦特的提醒——“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时,就忍不住想:还要怎么样?够幸运的了!
你够幸运了:人完好,作品留下来……的确该对照,多少人琴尽亡。像前面提到的曾缄《双雷引》,所“哀”的琴家裴铁侠夫妇……“嵇康毕命尚弹琴,向秀何心听邻笛。询君身后竟何有,绝笔空馀数行墨。”想那了不起的岁月,焚琴煮鹤不稀奇。比如聂绀弩,据说1965年初,有过焚诗的举动。曾经的政法工作者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写: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纪实版2009 年第 2期)
再如高尔泰《天空地白》披露,文革初烧了些“命根子“: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恩害怕,趁她不在,把我那些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
那个年头的故事,真如一位学者感慨:“那个年代, 想写诗而不把自己写成反革命, 恐怕不是容易事。”(赵毅衡:《人生何必为一把葱——〈陈敬容诗文集〉序》,《书城》2008年11期)因此,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儿子回忆:“文字的东西最要不得”,“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领袖和当局垄断一切资源。……这个社会对反对意见不给任何生存空间,要人在如此既诛心又杀身的压力下坚持独立人格,无异逼人去死。所以就连因帮闲而名列第一大无耻的郭沫若,我对他也寄予同情。”(周启博:《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尽管如此,因人而异。如汉娜•阿伦特揭示,“尽管这一时代夺去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生命并决定了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工作,仍然有极少数人几乎不受它的影响和控制。”爱德华•希尔斯则提醒,甚至诗人、作家不同的性情,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
在自由国家中,传统不是统一不变和强制性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并且影响着作家的成功机会,影响着他们选择的模式。在极权社会里,对出版的控制更为集中,“作家协会”或“作家学院”坚持文学的正统性,这就限制了作家在最适宜于他们的传统之中写作的自由。对那些在政治和宗教观点上与协会或学院官员不相一致的作家,这类限制显得最为明显。这些限制在性格强硬的作家身上则失去了效力。协会或学会虽然可以阻止在本国出版这些作家的作品,并且阻止他们以写作为生,但它们却不能完全阻止作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写作。文学创作的传统如此之强大,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如此之广泛,以至伟大作品永远会保持其魅力,并引导具有坚强个性的人去从事文学创作。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1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陈墨值得庆幸。正如其为老友邓垦保存下自己的《琴声》所写按语:
这篇散文写于47年前,那时我19岁。诗友雪梦很喜欢,留住了它。我的早期习作,写作年代皆标为20年代,想以此避祸禳灾耳。然而,纵如此小心,班房虽未坐成,诗稿文稿却因而焚毁遗失了不少!这篇《琴声》,不是雪梦偏爱,早就尸骨无存灰飞烟灭了。既然天不灭它,就让它飘向远方吧!
“言语没有死亡的地方,未来才能得救。”(《牛犊顶橡树》)——这是莉吉娅•楚科夫斯卡娅写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的话。“想到布罗茨基,我想提出他的教育意义。我们还有人像他喜欢俄语那样喜欢我们的语言吗?”这是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中的话。在艰难的岁月中,陈墨一再告诉自己:“我大汉民族的语言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五四新文学的语言”,这语言如水,好像流逝了,不再回来了,但过了一段时期,依旧活活泼泼地流着。那次第,像其古体诗词《沁园春•梦中家》所展示:
杏雨刚定,又起槐烟,陋巷篱笆。得顽云怪虹,菡风谷雨,月肥星瘦,野草闲花。九折羊肠,千盘鸟迹,老树旁邉是我家。溪声改,有汉唐鼓点,两晋鸣蛙。
——也或许只是,个人的幸运?但我觉得,像这锦江,“锦已走,江未走”。
用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序中的话:
……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做梦。
应该如是想,文章甘沦落。无论作为蚁民,还是爱诗的人,想要心灵的呼吸,不算什么“奢求”吧?抱定“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陈寅恪)宗旨,也不算什么“高标”吧?更不用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地下秘密进行着。小丑嘲笑着,用密码和隐喻躲避着,保护着人性。”(马内阿)——本来就是心照不宣、何必拆穿的事。更不用说,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荆天棘地犹青史,誓死鲁连不帝秦”(邵燕祥)的故事,鼓舞着“匹夫不可夺志”的后人负重前行。
拈出“弱德之美”的古诗词鉴赏家叶嘉莹,细读《伯夷列传》时写:
可是有人就说了:一个人死也死了,苦难也受了,不管是《春秋》赞扬他还是《史记》赞扬他,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错,“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不朽之名对本人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或者世界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文化,它们之所以有光明,就是因为有这些为了正义的持守而受苦难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物。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为后人留下了黑暗之中的一线光明。所以,用文字把这些人记录下来,使他们的名字不朽,不仅仅是为了还他们本人一个公平,更重要的是给后人以激励和希望。
(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01期)
在我看来,《落叶集》、《我早期的六个诗集》的意义就在这里。我想提高声音,说它们像四百年前顾炎武《井中心史歌》:“着书一卷称心史,万古此心心此理。千寻幽井置铁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像一百年前梁启超《重印郑所南心史序》:“此书一日在天壤, 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像五、六十年前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惟此是安流。”又像邵燕祥题词《牟宜之诗》:“百年沧海故迟迟,剩有焚馀一卷诗。”
最后,抄一段陈墨谈论“陶潜现象”的话,来结束本文:
现在,时代不同了,陶潜的“志”和“情”已失去现实意义,他的人格力量很难在现代找到共鸣。我们的时代,腐蚀性更强,生活充满着危机,在传统文化的泥石流里、在人格大裂变的运动中,当我们的生活不再“淡泊与宁静”时,我们的人品就再也“清高”不起来了。但我们的挣扎是真实的,我们的求索是真实的,我们反污染的搏击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在“文字狱”的阴影下坚持创作,既不为名为利,也不想赢得唾沫或掌声。这只是我们找回一个真我的形式。只要“真”,我想后人一定会欣赏我们带有疤痕的人品,并享玩我们略带苦涩的文字。
——但愿那时的人们,不再有我们的命运。
(陈墨:《“陶”话——小议“陶潜现象”》)
2018年2月9日星期五 初稿
2018年3月3日星期六 二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3月26日星期一 三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 四稿于凤栖山中
2018年4月12日星期四 定稿于家中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