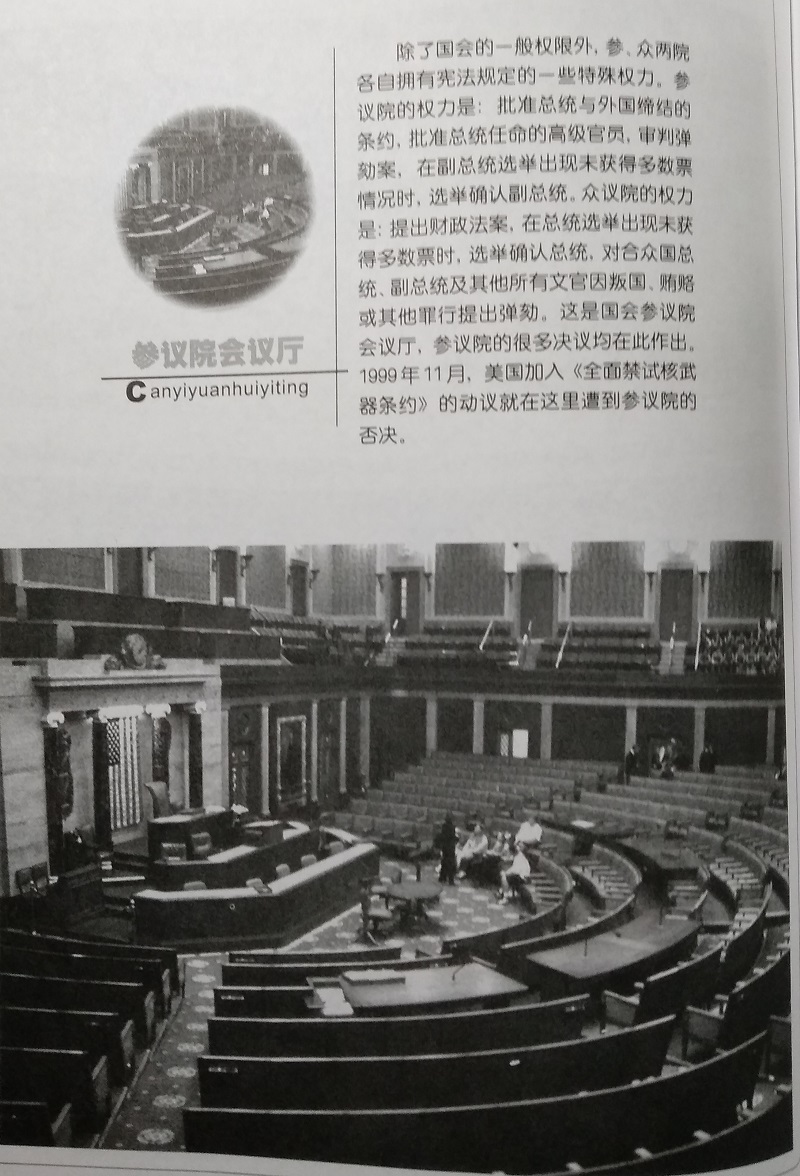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犯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大家也都希望找个办法,使政府少犯错误,或者在错了之后能得到纠正。中国人因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充满信心”(性善论),所以一般选择“让政府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纠正自己”的办法;而西方人则相反,由于对人的基本看法是“缺乏信心”(性恶论),因而选择了“让别人教育政府,让法院去纠正”的办法。
这恐怕就是“政府里边的法院”和“政府旁边的法院”两种不同传统产生的原因。
当年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丑闻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为尼克松的不当行为扼腕叹息,另一方面又深为美国法院公正公平公道的形象深感自豪,更为法院能在旁边“看着”政府而感到放心。
西方人普遍认为,防止以及纠正政府犯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要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人员的“道德自律”了。而这个往往是靠不住的。
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中,讲了一个《家就是一个城堡》的案例,讲述了美国法院是如何纠正美国政府犯错的过程。现在我给大家转叙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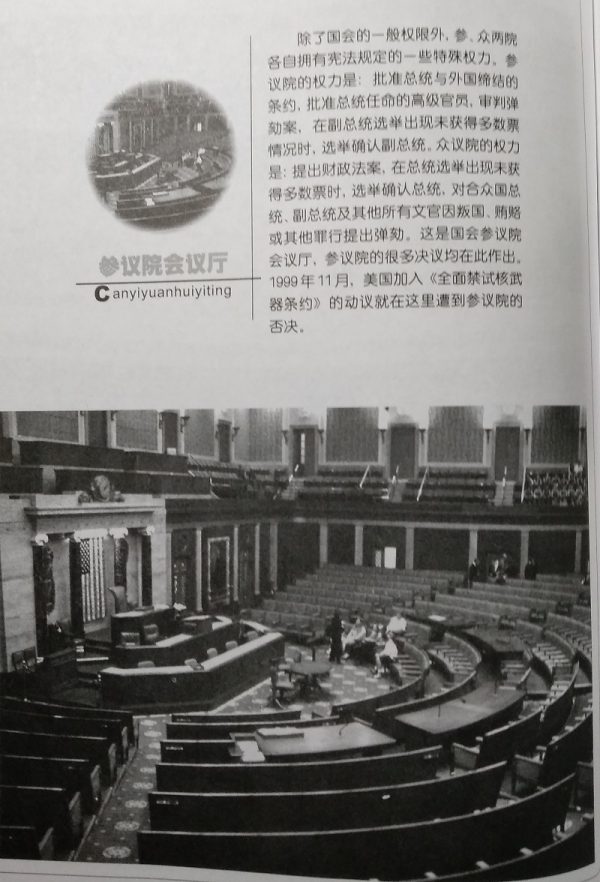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的国家。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查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令”。
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地的国家。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规定:“人人具有保障人身、住所、文件及财物的安全,不受无理的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此项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加上宣誓和誓愿保证,并具体指明必须搜查的地点、必须拘捕的人,或必须扣押的物品,否则一概不得颁发搜捕令”。
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对于这样的宪法条文的执行,是实实在在“令行禁止”的,他们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是绝对的。比如,在美国,当私有住宅领地受到侵犯,作为主人你是有权开枪的。
我的美国朋友塞琳娜,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行为,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就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当时听到塞琳娜的回答,我还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美国,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先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么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在美国,不仅房子是私有的,土地也是绝对私有的。这种私有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房产和土地的出租。一旦签下租约,付了租金,在租约的有效期内,这块地方也就是承租者的私人领地了。房东如果事先没有通知,未得到承租者的许可,也是不能进入的。
美国人的住宅一般没有造围墙的习惯,这该怎么保障安全呢?后来发现,有些林地隔一段距离,树上就有一个小标牌,写着:“警告,这是私人财产,不要进入”。美国人都知道,除了公园,这里都是私人土地,谁也不会随便进去。
塞琳娜生日那天,我们去参加她的生日晚会。她告诉我们,今天有两个行迹可疑的年轻人,在他们对面的一栋家里没人的房子周围转了好几圈。她丈夫打电话报警后,那两个人马上被抓走了。我们奇怪地问,他们又没有破门而入,转两圈算什么,警察凭哪条抓人呢?塞琳娜回答:越界。因为尽管他们没有进入房子,但是他们已经进入了房子周围的私人土地,侵犯了私人财产,犯法了。
在美国历史上,不断发生有人未经许可闯入他人领地而被击毙的案件。现在此类案件基本上都是偷窃之类的犯罪者,开枪者都是依法而被无罪开释。我们来这里之后,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就发生过一个老太太在自己家里开枪打死一个闯入她家里的年轻人而被宣告无罪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渐渐才体会到,塞琳娜的话绝非玩笑。在美国,如果有中国“文革”期间发生过的那种“抄家”行为,绝对会遇到主人持枪反抗。在这里,这早已是天经地义的法律常识。
一个日本留美学生在一天夜里和一位朋友在回家路上迷了路,去一家住宅问路,因语言不通未能听从主人的警告,结果被主人开枪打死。死者家属告到法院,地方法院判决房主无罪。这尽管在美国人的意料之中,可是却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之外。结果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签名活动。克林顿总统接见了死者的父母,再三向他们表示他对这一事件道义上的遗憾。但是,总统是无法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干预司法的,他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总统最顾忌的总是国内的原则和法规,国际影响相对来说是次要的。
此案又经过漫长的上诉,上诉法院最后确认被告的罪名是“使用枪支不当”,这是一个很轻的罪。但这确实是大家都认为是公正的判决。即使这事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但是,美国的权利法案的作者,写下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时候,它的意义不仅是确立土地的私有权和维护平民之间的地界,它还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限制。它的目的不是把外人挡在外面,而是要把警察挡在外面。它的严格执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此,我在下面再向你们介绍一个有关这条法案的著名案例。
大家都听到过那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豪言壮语吧?这件事例充分显示,在法治社会中,个人的财产权是仅次于生存权的自然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侵夺。而说到权利,我们总是认为,权利是法律给我们的,除了法律给予我们的权利之外,我们似乎不大知道还有什么其它权利,更不用说知道法律为什么可以给我们这些权利。但在西方,却存在着法律权利和另一种权利即自然权利的区别。
16世纪,西班牙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叫弗朗西斯·德·维多利亚。那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没多久,西班牙就已经开始盘算怎样统治当地的印地安人了。有一天,国王把维多利亚叫到身边,说他决定用铁腕手段来统治印地安人。他的根据是:土着印地安人没有文化,就文明教养而言,实在无法和西班牙人相比。因此,要在法律上剥夺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不能让他们成为财富的主人。
维多利亚认为不能这样做。他指出,随意对印地安人使用暴力剥夺财产所有权是不应该的。因为,虽然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像西班人一样具有人性和理性。他们的人性和理性决定了他们具有先于法律权利的自然权利;这个权利不是由国家的法律决定的,而是自然存在、与生俱来的。
据说,国王虽然没有接受维多利亚的见解,但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对印地安人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
西班牙人在美洲新大陆的结局虽然不怎么辉煌,但维多利亚的观念却就此传给了后人。英国的洛克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都曾经坚持不懈地反复宣扬自然权利的重要性。从此,许多西方人都坚信,他们的某些权利是天生具有的,不论国家的法律是否承认,这些权利都是永恒的。而且,西方人后来进一步引伸了自然权利的观念:国家法律必须尊重某些基本的自然权利,因为国家制定法律权利的权力本身也是自然权利的授权,而且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那么,依照这种观念,人们只记住法律权利显然是不够的,还要记住其背后的自然权利。
大家记住就好。继续听故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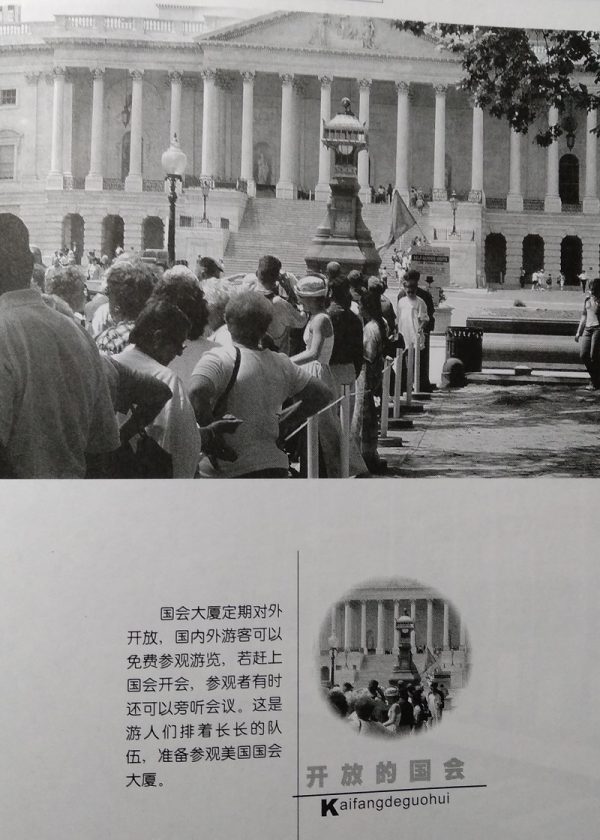 事情发生在1967年。案件一方的主角是一对夫妻,玛格丽特·麦克苏利和阿兰·麦克苏利。他们都是当时被时代所裹挟,对各种思潮都有兴趣,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权运动为职业的年轻人。
事情发生在1967年。案件一方的主角是一对夫妻,玛格丽特·麦克苏利和阿兰·麦克苏利。他们都是当时被时代所裹挟,对各种思潮都有兴趣,有社会主义倾向,并且以民权运动为职业的年轻人。
玛格丽特出生在肯塔基州,大学毕业后嫁了一个军人,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随着丈夫来到了首都华盛顿,不久就离婚了。接着由她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杜尔·皮尔森的专栏作家。此人当时是美国比较出风头的记者之一,有广大的读者。
1962年,玛格丽特成为皮尔森所雇的四个秘书之一,那年她26岁。她很快就成了这个年近70岁的专栏作家的女朋友。她当时被皮尔森的权威所吸引,也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很得意。但是两年以后,她离开了皮尔森去了密西西比州。1966年,玛格丽特又回到华盛顿,就在这时,她认识了阿兰·麦克苏利。阿兰是在华盛顿郊区长大的,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并且离了婚。他对政治一直很有兴趣,他们有共同语言,很快就恋爱了。
此后,他们的工作是安排白人帮助贫穷的黑人,也安排白人去帮助一些贫穷的白人。不久,他们又离开城市,转移到阿巴拉契山脉工作。阿兰在那里找到一个“自愿者组织”里的职位,专门训练帮助山区穷人的义务社会工作者。这个组织准备在肯塔基州的派克郡设立一个办公室,就把阿兰派去了。
1967年4月,阿兰和玛格丽特来到这里,从一个叫杰姆斯·康普顿的当地人那里租了一幢房子。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玛格丽特在南方联合教育基金会里找到了一个工作,这是1938年就成立的一个民权组织。在此期间,他们曾经到音乐城纳许维尔和一些大学去参加民权运动的会议。那里有激进的提倡“黑权”的黑人民权活动,有些大学还发生了骚乱。他们因此很长时间中断了工作。阿兰回来以后不仅教他的学生如何组织农业工人,还对他们大发激进言论,谈论有关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也不知是因为他过于激进,还是由于他的长期离职,一个月后,阿兰就被“自愿者组织”解雇了。
接下来,阿兰就去帮助玛格丽特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言行和这里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他们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却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不但难以被对方接受,甚至有时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因此,当地人对于他们给那里的宁静生活有可能带来的破坏越来越害怕,他们建议房东把阿兰夫妇赶走。于是,房东找了一个借口要求他们搬家。阿兰在搬走之前,要求房东康普顿去查看一下房子,以便确认他们在承租期间没有什么损坏。正是这一看,看出了一场大风波。
房子几乎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和他们工作有关的零碎东西,其中有左倾激进内容的书籍、小册子、照片、光碟、信件等。这些东西都是住在山里的康普顿从未见过的,可以说把他吓了一跳。他马上打电话告诉了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当地老百姓选的四年一期的“地方治安警察”。他在电话里说,这儿有个共产党的老窝,你们该来查一查。
于是,康普顿的“警察”朋友就叫他去地方法院开会,同时还通知了两名地方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地方机构的一名官员。主持会议的是其中一个叫托马斯·雷特利夫的检察官。他在会议上提出要对阿兰夫妇“采取行动”,并要求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帮忙。但是,联邦调查局官员知道这种行动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拒绝了他。于是,雷特利夫只好自己在肯塔基州的法律条例中寻找法律依据。结果,他找到了在1920年该州通过的一个修订法,里面有一条“颠覆(政府)罪”,定罪的话可以判21年徒刑以及一万美元罚款。就根据这个法,他们开出了对阿兰的逮捕令和搜查令。搜查范围写的是:“颠覆材料,或印刷机,或其他印刷和传播颠覆材料的机器。”
这时,阿兰夫妇刚刚搬到新家,满屋子都是没有打开的箱子和盒子,书刊和文件满地都是。1967年8月11日傍晚,一群“地方治安警察”进入他们的家,向他们宣读了搜捕令。检察官托马斯·雷特利夫也来了。此后发生的事情,使这位检察官和阿兰夫妇拴在一起,至少奔波于五个法庭,打了17年官司。
在对阿兰搜身之后,十几个人搜查了这间屋子,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阿兰夫妇被吓得浑身发抖,他们想,只要熬过这个晚上,与外界取得联系,一切都可以过去了。玛格丽特立刻给当地的律师打了一个电话。这时,警察找到一些有关玛格丽特的材料,就给她也开了一张逮捕令。这时,搜查的性质也变了,一开始他们还对书刊进行挑拣,把东西分为两堆;现在,雷特利夫用手一指,两小堆东西被合成一堆全部拿走。里面有他们全部的564本书,其中有毛泽东、切·格瓦拉、马克思、列宁的书。最后,警察从邻居那里借了一台车,把阿兰夫妇的全部东西装车运走。
当晚,阿兰夫妇被关押。要求阿兰的保释金是五千美元,玛格丽特的保释金是二千美元。他们立即和朋友联系以取得保释金。同时,纽约的两个律师,威廉·肯斯特勒和摩顿·斯达维把阿兰夫妇列进了他们的救助名单。他们刚成立了一个宪法权利中心,专门从法律上对这类案子给予帮助,只收很少的费用甚至免费。这两个律师首先寻求的,就是让上级法院宣布肯塔基州的这条法律是违宪的。
阿兰夫妇现在担心的是他们的朋友会被连累,引起麻烦,因为被拿走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是多年来他们参加各种激进活动和组织的情况。玛格丽特被拿走的东西中有以前她和几个男人的私情记录,其中也有那个专栏作家皮尔森的情书。作为习惯于个人隐私权受到尊重的美国人,无法想像这种东西居然会被没收。但是他们偏偏碰到这样一群“土警察”,一时有理讲不清。后来在法庭上,当法官向那些“地方治安警察”问到宪法修正案第四条和有关“搜捕”的法律知识,他们竟然毫无所知。他们只是被当地居民选出来,管管一般的治安纠纷的。这次他们是想给他们讨厌的这两个外地人吃点苦头,却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因此闯入了一个“国家级大案”。
阿兰夫妇在牢里只待了一个星期,就收到了朋友们筹集的保释金而出狱。一个月后,派克郡地方法院开庭,根据肯塔基州的法律,以“颠覆罪”对阿兰夫妇起诉。但是,三天后,美国地区法院的东部法庭就宣布:“很难想像,一个有能力的律师会认为这条州法律是符合宪法的。”地区法院指出:“(该法)违反第一修正案……因为它不恰当地禁止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它无法分辨提倡理念和提倡行动之间的区别……它把牢狱之灾强加在提倡非主流政治信念的人头上。”同时,地区法院下令,永久地禁止肯塔基的州法律以颠覆罪起诉阿兰夫妇或其他任何人。
这时,阿兰夫妇觉得,由于一些乡下“土警察”的自以为是和胡作非为而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可以彻底结束了。接下来,该轮到他们考虑怎么告那些地方官员和警察的问题了。因为在美国,没有政府错了就算了的事情。可是,地区法院却因为肯塔基州政府有可能对“颠覆罪”的合法性提出上诉,因此还不能马上就结案。于是法庭下令,让检察官雷特利夫对所有的材料“安全保存”,“直到上诉或其他法律程序终结”。阿兰夫妇现在发现他们面临的局面有点奇怪:他们重获自由,可是被抄去的财产还被扣在别人手里。他们更未想到,正是这样一个法律程序造成的“暂缓发还”,他们的个人权利和个人隐私被进一步严重侵犯,更糟糕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阿兰夫妇的行为若是放在某些国家,那绝对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美国对言论结社的自由度太宽松,阿兰夫妇才能得以逃脱法网。同样是在1967年,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些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即使老老实实,也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击打;而美国的左倾激进分子阿兰夫妇,公开进行“革命活动”,被警方逮捕,在“人脏俱获”的情况下,居然被地区法院包庇,无罪释放。真不明白,这资产阶级专政机器对阿兰夫妇都不施以专政,哪它应该是专谁的政?难道只专杀人抢人偷人骗人强奸人的政?对“革命造反派”则网开一面,任其发展组织,宣传鼓动,这政治意识未免也太麻木了吧?
(未完待续)
荀路201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