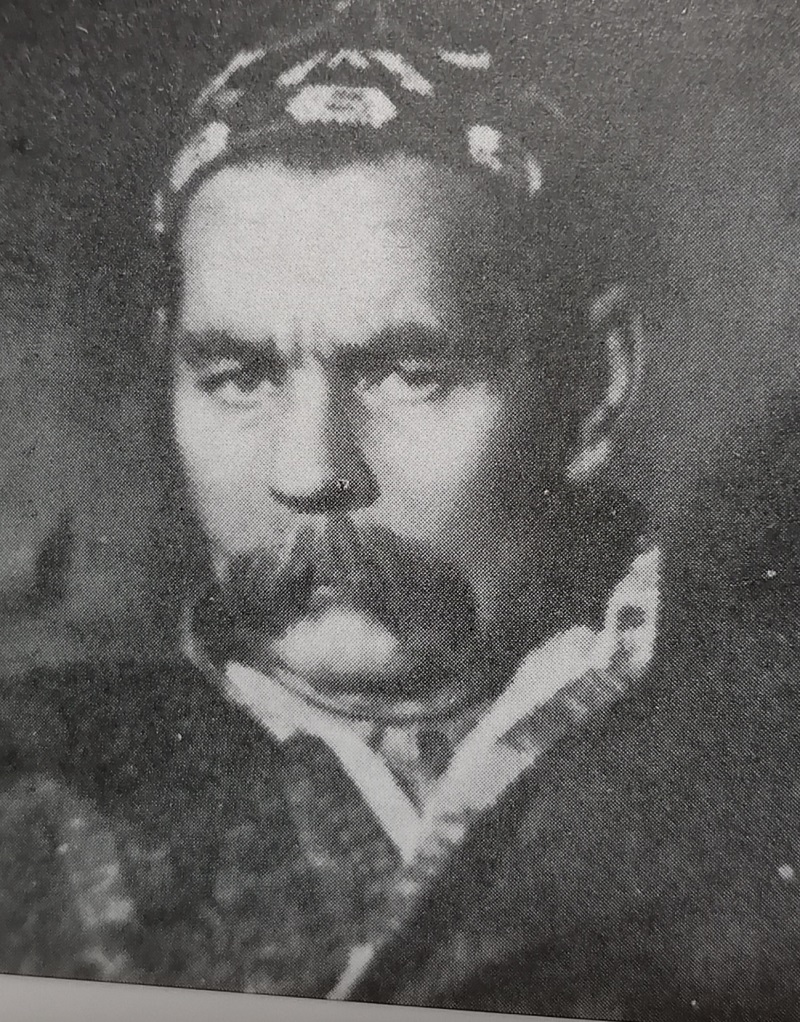“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六)
1918年1月1日,新的一年开始了。高尔基目睹正在 “深入进行” 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俄国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一天,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对时局充滿忧虑和愤懣的文章:
“革命正在深入……
“那些正在 ‘深化革命’ 的人的无所顾忌的蛊惑言论已经结出了果实,很显然,这些果实对于那些最有觉悟和最有文化的工人阶级社会利益的代表来说,是致命的。在工厂里,干粗活的工人对技术专业工人们的充滿恶意的斗争正在逐渐地展开; 干粗活的工人们开始说什么,钳工、车工、铸工等等都是 ‘资产者’。
“革命仍然在深入,为那些用工人阶级活的身体做试验的人们增添着荣耀。
“而那些意识到时局的悲剧性的工人们却对革命的命运怀着巨大的忧虑。
“ ‘我担心’,这些工人中的一位写信告诉我, ‘有朝一日群众将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对最美好的未来永远失望,将永远失去社会主义信念……
“ ‘我想,会这样的,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可能实现蒙昧群众的一切愿望,而且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在这样的群众中的人为了使地球上对社会主义和美好生活的信念不至于破灭,应当怎么办。’
“ ‘文明程度稍高一点的工人在愚昧的群众中的处境变得非常糟糕,好像他成了自己人中的异己分子。’ 另一位工人这样对我说。
“这类抱怨愈来愈频繁,这预示着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大分裂的可能。可是另外一些工人在交谈和来信中却这样对我说: ‘同志,您应当高兴才对,无产阶级战胜了呀!’
“我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无产阶级沒有战胜任何东西,沒有战胜任何人。正像过去,当警察统治牢牢地卡住无产阶级的脖子时,它沒有被战胜一样; 现在,当无产阶级卡住资产阶级的脖子时,资产阶级也还沒有被战胜。思想是无法用肉体上的暴力手段战胜的。胜利者通常是宽宏大量的,也许,这是由于疲劳的缘故; 无产阶级却不是宽宏大量的,这从一些不知何故被投入监狱的人的案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在监狱里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挨饿,是的,数以万计,而且是工人和士兵。
“是的,无产阶级并不宽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应在国内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无产阶级并沒有取得胜利,全国到处都在进行内讧性的屠杀,成千上万的人在互相残杀。……
“如果内讧性的战争仅仅归结于列宁抓住了米留科夫(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小资产阶级的头发,而米留科夫则揪住了列宁那蓬松的假发(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戴假发化装),那么,‘请吧,老爷们,请打斗吧!’
“但是互相打斗的并不是老爷们,而是奴才们。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殴斗会很快结束。当你眼看着国家的健康力量怎样在残杀中灭亡时,你是高兴不起来的。……
“银行被占领了?如果在银行里有可以喂饱孩子们的面包的话,那倒好了。但是银行里没有面包,而孩子们依然在日复一日地挨饿,他们虚弱的人数在增加,死亡率在上升。
“内讧性的大屠杀彻底地破坏了铁路运输,即使农夫们交出了粮食,那也无法很快把它运出来。
“但是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沒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
“……现在,对人的价值估量依然同过去一样低廉。旧的生活习惯并没有消失。‘新的开端’ 依然像过去一样粗俗,只是外表上显得更少教养。在现在的派出所里,又是大喊大叫,又是跺脚,就像以前喊叫的一样。捞起贿赂来还像以前的官吏们一样,还把人们像牲口一样成群地往监狱里赶。一切旧的东西、丑恶的东西暂时都没有消失。
“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说明在俄国只实现了物质力量的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没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长。
“而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中一切卑鄙东西的纠正就在于发展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和能力。
“ ‘现在谈论这些还为时过早,我们首先应该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
“再没有比统治人的权力更卑劣的毒素了,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使得权力不至于毒害我们,把我们变成比那些我们终生反对并与之斗争的人更卑鄙的食人魔王。”
 高尔基显然很看重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一句话: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人道、人性的底线使得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渐行渐远,成了革命的批判者,成为一个 “不合时宜的” 思想家。因此,作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17年11月30日《真理报》刊文说: “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敌人的语言讲话。” 对此,12月2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反驳说: “这不是真的。我要对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的代表们这样说: 狂热分子们和轻浮的幻想家们在工人群众中唤起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和死亡,而无产阶级的毁灭将在俄国引起长期的、黑暗的反动。”
高尔基显然很看重法国大作家雨果的一句话: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人道、人性的底线使得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渐行渐远,成了革命的批判者,成为一个 “不合时宜的” 思想家。因此,作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1917年11月30日《真理报》刊文说: “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敌人的语言讲话。” 对此,12月2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反驳说: “这不是真的。我要对工人阶级的最有觉悟的代表们这样说: 狂热分子们和轻浮的幻想家们在工人群众中唤起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把俄国无产阶级引向毁灭和死亡,而无产阶级的毁灭将在俄国引起长期的、黑暗的反动。”
针对《真理报》文章中 “一切革命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反面现象。这些反面现象不可避免地与旧的千年国家制度的瓦解连在一起” 之说,高尔基不无揶揄地指出:
“我不能认为,像在冬宫、加特契纳宫及其他宫殿里盗窃国家财产的事实是 ‘不可避免的’。 我不明白,毁坏莫斯科小剧院和在我们的著名女演员玛.尼.叶尔莫洛娃的化妆间里进行偷窃同 ‘千年国家制度的瓦解’ 又有什么联系?
“我不想列举众所周知的毫无意义的洗劫和抢掠的行动,我要说的是,对于这种流氓们所干的耻辱之事的责任正落在显然无力消灭自己圈子里的流氓行为的无产阶级身上。
“无产阶级在有1.5亿文盲的乡村人口的俄国中从数量上讲,是一支很弱的力量,它应当明白……
“它还应该明白,它是坐在刺刀尖上的,而大家都知道,这可不是很牢固的宝座。
“总的来说,‘反面现象’ 很多,而正面现象又在哪儿呢?真看不见什么正面现象,如果不算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那些 ‘法令’ 的话……
“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权利。
“而且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一一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
当年的高尔基堪称有责任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革命潮流的深刻理解和对俄国社会的独到剖析,对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到震聋发馈的作用。所谓 “不合时宜” 现在看来是非常合乎时宜的思想。他并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认为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扭曲了社会主义事业。他一再提醒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不要随波逐流,要恪守良知和道德,不能与流氓无产者同流合污。他在1917年12月19日《新生活报》提醒大家:
“未被战争和内讧残杀所消灭的幸存的工人知识分子处在了一群心理异己者的紧密包围之中,这些心理异己者说着无产阶级的语言,但是却不会像无产阶级一样感受事物。他们的情绪、愿望和行为使工人阶级优秀的上层注定承受耻辱,遭到消灭。
“这些愚昧群众的极易受刺激的本能找到了他们动物性无政府主义的表达者。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些造反的小市民的领袖们正在贯彻的是蒲鲁东的贫瘠的思想,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他们发展的是布加乔夫(注:俄国农民起义首领)习气,而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还宣传全面向道德和物质的贫穷看齐。
“说这些话令人感到难过和痛苦,但是又必须说,因为正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将要为由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力量犯下的罪孽负责。
“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已经开始拆卸和盗卖机器的铜部件。许多事实证明,在工人群众中存在着最野蛮的无政府状态。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种性质的现象。比如说,有一家工厂的工人们用自己的工资买了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但是这类事实屈指可数,而与此性质相反的事实却有成百上千个。
“……有聪明而坚定的敌人和自己作对是最为有益的:好的敌人能培养自己的对手,使他变得更聪明、更强大。
“工人知识分子们应该懂得这一点。而且一一我再说一遍一一他们应该记住,现在所干的一切都是以他们的名义干的,历史将对他们、对他们的理智和良心做出自己严厉的审判。不能总是只讲政治,还应当保留少许良心和别的人性的感情。
高尔基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里充斥着的农民习气很是不以为然,他用这样的一个长句指出:“要求重新变成农民的士兵把无产者的理想主义当成他们自己的宗教加以接受并要求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农村中推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幼稚而可笑的。” 这就是说,在当时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强行上马社会主义革命,只会产生非驴非马的畸形儿。他对这种异化变形的产物当然是不能认同的,他期望有健康的力量来承担革命的主导作用。他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阶级利己主义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优秀导师马克思、考茨基等人把将所有的人从社会和经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寄托在无产阶级正直的力量身上。”
高尔基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对现实中出现的不符合革命理想的事实始终持非议和否定的立场。他在《新生活报》1918年1月26日的一篇文章中,苦心婆心地劝诫、提醒俄国无产阶级:
社会理想主义这一所有人都互相和睦相处的伟大理想在推动着全世界的生活。无产阶级在对自己思想上的敌人施加暴力时,是否想到自己正是在实现这一理想呢?社会斗争并不像俄国工人的惊恐的领袖们教导他们的那样是血腥的斗殴。
革命是伟大的、诚实的事业,是我们的复兴所必需的事业,而不是毁坏民族财富的无意义的劫掠。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倾注到革命中去;如果我们不消灭,或者不减少那些使群众忘形并败坏俄国工人革命者的残酷、凶狠,那么革命将会是无力的并将会死亡。
这种劝诫和提醒有用吗?也许能起一点作用,也许不但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会给高尔基带来麻烦。但是高尔基并不在乎,他依然我行我素,仗义执言。1918年5月30日,他又在《新生活报》上写了一篇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人“新瓶装旧酒”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内容:
有一个工人(来信)写道: “我在革命前的功绩不比豌豆街(注:彼得格勒许多国家机关所在地)上那些现在像狗一样向我狂吠的小家伙们小。我从1904年起,而不是从十月革命起就是布尔什维克。我在监狱里蹲了两年零七个月,还过了五年饥饿的流放生活。因为担任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常和农民们一起去找上级。他们朝着我大喊大叫,弄得我羞于直对农民同志们的目光,真怕他们突然会问我:‘这些人怎么咋咋呼呼的,就像沙皇时代一样呀?’请您想办法影响这些人,让他们清醒过来!”
一位工人因为责备一名喝醉酒的赤卫队员粗鲁而被捕了,他被指控有 “反革命情绪”。据他说,审问时 “人家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说:回答!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同志?可他们却说:这样的同志应当掌嘴。请允许我声明一句,掌嘴在旧时代就够多的了,如果现在也这样干,那就不值得费劲(革命)了。”
这种指责听到的越来越多了,而我看不出那些引起如此令人感到耻辱的指责和抱怨的人有什么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东西。……
……他们给生活、给日常饥饿的痛苦生活究竟直接带来了什么新东西,是否带来了许多理智和善良?
高尔基对这种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的行径口诛笔伐,引起了一些赤色分子的不满,他们质问道:
“难道高尔基现在还不同意,他以前说出的 ‘思想’ 中确实有许多是 ‘不合时宜的’ 吗?”
高尔基的回答是:
不,我现在也不同意。我关于野蛮、粗鲁,关于布尔什维克们发展到虐待狂地步的残忍,关于他们的不文明,关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民的心理,关于他们正在拿人民作一场令人厌恶的试验并正在消灭工人阶级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和我关于 “布尔什维主义”所说的许多话至今仍然是完全有效的。”
 高尔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践踏人权,罔顾道德的批判,与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揭示共产极权主义本性的一些言论相得益彰。布热津斯基在《强制性的乌托邦》一章中指出:
高尔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践踏人权,罔顾道德的批判,与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揭示共产极权主义本性的一些言论相得益彰。布热津斯基在《强制性的乌托邦》一章中指出:
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一一通过削弱社会的凝聚力一一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这也可能是一心要保持权力的共产党(以下简称CP)统治者无所顾忌的计谋。然而,很难找出哪怕是一点点的理性解释来说明,曾经被CP统治过的社会为什么会不顾后果地破坏自然环境。……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得不怀疑,CP的精英们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因而对后代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涉及这种大规模犯罪行为的一个矛盾现象是:要想做到全面控制的努力实际上却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它以一定方式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价值和物质环境,以至于在某一点上这个制度必然会垮台。说到底,这个自杀性动力的根本原因是,认为为了乌托邦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这种道德上应受严厉谴责的观念一一结果,甚至连CP统治者都不再有任何能界定政治统治准则和限度的自我道德指导方针。因此,他们对全面控制的追求产生了特别有利于他们自己长存不衰的盲目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范围是无所不包的。CP和纳粹的信条都断言它们具有普遍意义一一尽管它们有很多重大的不同之处。纳粹的蓝图是要使德国居于一个新的全球等级制顶峰,这个等级制结构的基础是认定和排出优秀种族和等而下之顺序的所谓科学基因法则。CP的蓝图则认为,实现CP先锋队的世界革命乃是人类历史性拯救的最终行为,以便把人类推进到社会主义,然后再进入共产主义。
所幸的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两大强制性乌托邦,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 “新秩序” 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无产阶级专政” 都遭到了惨败。高尔基尽管钟情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热衷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在他故后,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始终是水中月,镜中花,没有在人世间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
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拿破仑一起在莫斯科红场观看苏联阅兵仪式。亚历山大目不转睛地望着坦克说: “我要是有这样的战车,也许已经征服全亚洲了。”
凯撒眼馋的是导弹:“凭着这种矛矢,我没准早把世界置于我的统治之下了。”
拿破仑正在读《真理报》,他将目光从报纸上抬起来,大声说: “要是搞上一份跟这差不多的报纸,滑铁卢的事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4月5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