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5
我们在中国梦所看到的,是一个超危险意识形态的胚胎。--斯坦·林根(Stein Ringen)
作为一家跟中国中央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的西方媒体,德国之声由此确立了自己“准五毛”和中共大外宣配合者的身份。即便在中国病毒危害人类,宛如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大屠杀”之际,德国之声仍不断刊登为中共涂脂抹粉的“软性广告”——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对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之专访。如果不看发表的媒体和采访的对象,我还以为是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胡锡进亲笔撰写的社论。
罪恶昭彰的中国难道不能被控有罪吗?
这篇专访的题目是《向中国索赔,可能反而助长中共政权》。当记者问,“近期西方有不少人都提出就新冠疫情损失向中国索赔,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您怎么看待这些诉求?它们合理吗?”

余凯思回答说:“我认为,除非中国政府故意向他国散播病毒、或者在甘愿冒着自身巨大风险的情况下有意让病毒向他国蔓延,否则没法真正向中国索赔。……这种赔偿诉求也是不合理的。提出索赔的人,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真的在法理层面上有什么胜算。”他进而论述说,西方无法从“中国没有恰当、及早地对疫情做出回应”直接推论出“中国的行为尤其地有罪”。
这种貌似客观中立的论述是靠不住的。余凯思所说的“除非”,并不是没有存在的可能,如果你敢于直面中共政权的邪恶,就知道中共作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共军方将领早在二十年前就写出深受高层赞许的《超限战》——与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的情节惊人一致。如果中国没有罪责,为什么至今仍然坚持拒绝外国就病毒源头展开调查呢?
很多西方的汉学家,并不承认“中共邪恶”这一前提。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汉学家,首先是他们对中国抱有如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分子那样的美好幻想,认为那里是神秘、文雅、优美的东方世界,在欧洲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丝绸和瓷器,在那里庶民就能拥有。皇帝是仁慈的父母,百姓是祥顺的子女,一切都在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之下井井有条。但中国真是如此吗?
后来,当这些汉学家以中国研究作为终身的职业乃至饭碗时,他们与这个职业、饭碗产生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攸关性”。他们不愿意批评中国的一切,因为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很容易转换为降低其研究工作的神圣性和荣耀性。在此意义上,他们不由自主地沦为“洋五毛”,还不等中共展开统战,就已膝盖发软下跪了。这也正是他们批判本国政府时显得风骨嶙峋,在谈及中国时则瞠目结舌——他们最喜欢装模作样地反省纳粹罪行,谴责纳粹集中营的屠杀,因为那已是过去的历史;却故意无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进纳粹集中营升级版的“再教育营”的惨剧,一旦他们批评如此“敏感”的事情,其职业生涯就会受损,比如中国政府拒绝发给去中国的签证。
大概自己也觉得以上言论宛如中国的辩护律师,余凯思立即补充说:“我也要指出,在疫情最早期,中国训诫散布消息的医生、试图向本国民众(而非主要向外国)隐瞒疫情的真实规模,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中国处于了一个相当不利的地位。”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批评,并不是对李文亮及被害死的中国人具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而只是为了塑造其“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的观感。余凯思特别将中国政府隐瞒的对象限定在“本国民众”而非“外国”,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护——难道中国政府在隐瞒本国民众的同时,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外国政府通报了真实的情况和数字吗?当然没有,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滚动着越来越大的谎言的雪球。另一方面,余凯思的这一区分无意中暴露出其希特勒式的种族主义思想:德国人(西方人)的生命尊贵,中国人可任其政府宰割,中国政府只要尊重西方人的生命,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和谅解,就可以对本国民众为所欲为。我不禁要反问:德国人真的从人类命运的层面上深刻反省了纳粹的罪恶吗?
避免中国人受辱的方法,难道是无视共产党的暴政?
德国之声记者的问题有明显的倾向性:“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多次输掉战争然后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同意向外国支付赔款的经历。现在,来自欧美的追偿,是否会触发起中国人的历史屈辱感?这种做法是否会有危险性?”
余凯思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左派论述来回应:“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中国人会从现在的追偿联想起受帝国主义列强羞辱的经历。……据我观察,欧洲、美国都没有认识到这一趋势的危险性。这会对中国民众造成非常可怕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波及中国政府。……惩罚措施也会涉及到普通中国民众。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汹涌抬头,此时再来追偿,就会起到不良效果:它不会削弱中国政府,反而会让中国民众去支持中国政府,会掀起一股让中国民众与中国政府团结起来的浪潮。……追偿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可怕手段。”
这是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批评、反击、惩罚中共政权的作恶,会让中国人感到受辱,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以至再次爆发义和团之乱;反之,纵容、默许乃至支持中共政权的作恶,是尊重和同情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对西方有好感,然后东方与西方就能和谐共处、相安无事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可如此推演:当年如果民主世界惩罚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必然刺激全体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让他们更加支持纳粹政权并反对西方;当年如果西方国家因为南非白人政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对其经济制裁,必然刺激南非白人政权的支持者更加同仇敌忾,对黑人展开更残酷的压迫。所以,西方最好的应当方式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一切独裁暴政,自由世界难道应当鸦雀无声吗?
拥有这种奇怪逻辑的西方人,不止余凯思一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大脱钩》(The Great Decoupling)的文章,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川普政府)与中国大脱钩。作者基斯·詹森(Keith Johnson)与罗比·格拉默(Robbie Gramer)在文章开头引用的典故是——美国驻一个亚洲经济强国的大使曾直率地向华盛顿表示:不要切断与他们的联系,给他们一些“经济空间”,否则他们将被迫用自己的武力开创经济帝国。但是,华盛顿受到了经济民族主义者的控制,白宫对一九三五年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大使从东京发出的建议充耳不闻。几年之内,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经济压力,最终实施了贸易和石油禁运。格鲁写信六年后,两国开始了全面战争。从这个历史事件出发,两位作者进入正文,进入反对与中国脱钩的一系列论述:“今天,美国政策制定者正忙于与另一个亚洲重量级国家作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对抗。而且,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样,经济脱钩论调尘嚣甚上。”
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在其“修昔底德论”中也引用同样的典故。但他们对历史事实的认知完全是错置和扭曲的。我建议这些看似饱学却连基本历史事实都未掌握的作者读一读英国历史学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所著的《命运攸关的抉择:一九四零—一九四一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抉择》。书中用夯实而确凿的史实雄辩地指出:美日开战并非美国挑起,并非美国不给日本“经济空间”。恰恰相反,战争源于日本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疯狂扩张,在战争过程中对平民的屠杀。美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和石油禁运,是因为日本在上海和南京的屠杀引起美国民众普遍的愤怒,美国不愿重演在欧洲绥靖主义失败的教训。“日本最后面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开战,这里的原因不在于华盛顿,只能从东京去找。日本的领导层狂热地支持日本急剧的侵略扩张,直到最后发现除了走向灾难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伊恩·克肖所说:在太平洋战争惨遭失败之后,国家经过重建,日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而日本战后繁荣的基础恰恰就是依靠美国,依靠成功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拥抱资本主义竞争和市场经济原则。这是全面失败以后日本从灰烬中重生所遵循的思路,而一九四零年日本的思想方法和战后的新思维天差地别。当时日本的思维方式仅仅看到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威胁日本赖以生存的资源,完全不可能看到除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外,还有其他获取资源和国家繁荣的途径。
在此意义上,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是要像日本那样经历一次惨烈的战争,才愿意与美国同行;还是从日本的历史中获得智慧,不经过战争就放弃对外野蛮扩张、对内独裁暴政,并且主动拥抱民主自由?这是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是西方失败的替罪羊?
德国之声记者继续问:“既然追偿只会起到反作用,为什么西方还会有人提出这种想法呢?”
余凯思虽然承认“中国与欧美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中急剧恶化,这多少也能归咎于习近平推行的政策。习近平本质上也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客,比如他搞的民族主义浪潮,或者是歌颂红色文化、红色旅游等等,游客们前往中共革命纪念地,穿着当年的服装,向前挥舞拳头。中国政府在这些年变得更尚武、更民族主义、更肆无忌惮,然后就激起了外国的反感”;但他用更多篇幅谴责西方将中国作为替罪羊:“在欧美,许多人都想把自己的疏失推责到中国的头上……把中国当作这一切的替罪羊。就像十九世纪以来的多次危机一样,人们总是想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将别国当作替罪羊。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
余凯思的这段论述相当关键:“一九八九年后,西方民主国家一度认为自己的体制具备优越性,历史终结论、民主胜利论、西方自由市场优越论一时甚嚣尘上。而中国此后的发展走势,却令这些论调受到了质疑。现在,也必须承认,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时,取得了比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好得多的成绩,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其病死人数、感染人数的比例要比绝大多数国家小得多。新冠危机演变成了一起象征性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民主社会的自身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来自中国的深刻挑战。中国体制当然也有自身的弱点,但是也有其长处。中国体制确实成为了西方体制之外的又一选项,中国正在打造与民主体制对立的模式。中国体制已经取得了成就,还为中国赢得了权力、争得了影响力。这场体制竞赛正在激化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极端化的趋势。”
余凯思的“民主失败论”和“极权高效率论”,在西方不是第一次出现。当纳粹德国崛起时,当苏联在太空领域超过美国时,很多民主国家的人士都对民主的前景抱悲观态度。但我又相信,余凯思对中国抗疫方式的肯定和对西方的批判,其实是言不由衷的——他绝对不愿放弃德国国籍、归化成中国人,成为一名被政府肆意凌虐、出门必须扫手机中的健康码的中国公民,那是一个宛如《一九八四》的、“老大哥”无所不在世界。如果他再读一读中国作家方方的抗疫日记(德文版已经出版),他就知道中国人被“牲畜蓄养”的境遇有多么悲惨。西方不需要替罪羊,西方需要的是真相。中国不是西方的替罪羊,中国就是疫情泛滥的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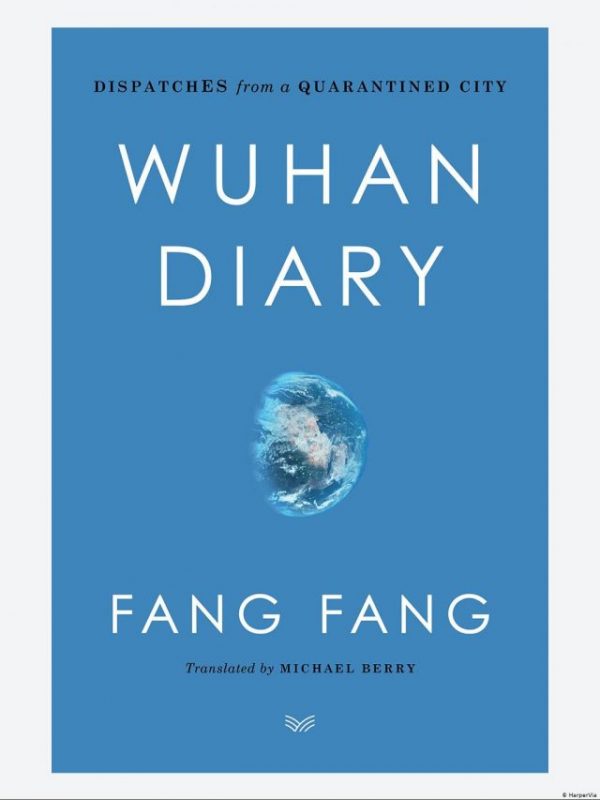
任教于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的华裔学者张伦,对中西抗疫模式做了一番精彩对比,比余凯思似是而非的“中国成功论”高明得多。张伦认为,不能只看到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也要看它的成本和次生后果有时候更严重。传统上中国是个“量”的帝国,可以靠集中力量办很多巨大的工程,但一旦出现危机,因为缺乏地方自主和有效的平衡机制,灾难的传递效果、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在现代世界,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过分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其王牌,其实是很危险的。反之,大疫来袭,西方国家很难强迫把国民关在家里,而是依靠每个人的自律。张伦更认为,疫情带来了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将因此而改变。中国与其洋洋自得于“中国经验”,不如好好思考:当代的中国人要以怎样的文明形象展示给世界?在制度转型之外,国人需要在价值方面做出更深层的调整,加快文明转型。
在抗疫之战中,西方表面上落后了,但西方没有输;中国表面上闪电般地控制了疫情,但中国并没有真正获胜。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在《D-DAY:诺曼底的巅峰时刻》一书中揭示的民主的英美必然击败独裁的纳粹德国的真理,依然适用于今天:当初,希特勒的闪电战席卷整个欧洲,让希特勒相信,自由散漫、享乐软弱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培养出跟纳粹的最优秀的士兵抗衡的军队,极权主义的狂热和忠诚永远会征服民主主义的开明和温和。然而,那些阅读反战和愤世嫉俗主题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长大的美国年轻人,“当考验来临,是为自由而战还是屈服,他们选择了战斗。他们是民主的斗士,他们是D日的勇士,因为有他们,我们才有今日的自由。”在诺曼第登陆的那一天,因为在德国的指挥系统中,精锐的装甲部队必须希特勒才能调动,前线指挥官只能坐等灾难降临,而希特勒相信真正的登陆地点是加来,所以按兵不动。反之,盟军统帅艾森豪那一天没有做出任何指令,将权力下放给前线将领,因为前线将领能够根据现场瞬息万变的态势对作战计划做出调整。这是两种战争机器和两种观念秩序的对决,历史已经决定了它们的成败。历史还将决定今天独裁的中国与民主的西方的成功。然而,在余凯思这样儒家化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已然丧失了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自信与战斗精神。
来源:台湾公义报


你怕不是被下了降头,还中国病毒,你应该给你和你全家换个肤色换个发色,换个基因,和你一个肤色真是悲哀。枉我买过你那么多书,塞村头厕所当手纸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