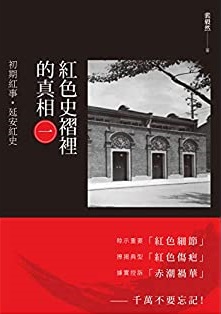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6)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6)
中共初期经费来源
任何军政活动都需要庞大财力支撑,政治角力的实质是经济能量的调动,经济决定军政成败。缺了钱袋子,难举枪杆子。曾国藩剿灭洪杨发逆,首在筹饷,清军江南大营每丁饷银三两八钱/月,湘军每丁饷银四两二钱,亲兵四两五钱,什长四两八钱,[1] 当然疆场用命。孙中山搞共和,必须「粮草先行」。1907年5月~1908年5月,同盟会在两广、云南六次举事,筹用港币20万。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同盟会支付187636元,每位贫家义士发「安家费」5000元。同盟会前后八举事,经费共约47.9万。捐款者以越泰华侨为主,时称「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2] 辛亥研家认为:「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3]
没了「阿堵物」,职业革命者无法生存,大场面的革命无从形成。没有经济基础,最初的革命队伍无法聚集,革命活动无从开展,这是基本常识。中国共产党(下文简称「中共」)早期经费的主要来源为苏联,但中共对「用卢布」一向讳莫如深。1960年代前苏联要避「输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佣」;此后中苏闹翻,中共又得避讳「依靠卢布喂大」——缺乏独立自主,现在开骂「苏修」,岂非「忘恩负义」?亦有损「万水千山」的艰难度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必然性。1980年代后有所弛禁,1990年代苏联档案解密,不断飘出尘封资料。但大陆学人勒痕犹在,余悸存心,很少敢沾碰这一专题。近年,党史界有人开始整理这方面史料,研究论文开始发表于较冷僻的学术刊物。绝大多数当今大陆学人(遑论老干部)对中共依赖卢布起家尚不知详,会发出「原来如此」的惊叫。
一、 最初的窘迫
1920年7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每月自捐80银圆为小组活动经费。[4] 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政治系教授,月薪300银圆。[5] 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离沪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长,日本帝大毕业生李汉俊(1890~1927)代理中共上海支部书记。[6]他向武汉来沪准备留苏的包惠僧抱怨:「人都走了,经费没有,没办法干了。」李汉俊要包惠僧赴穗请回陈独秀,要么将党的机构迁往广州。包说:「我同意去,但是没有路费。」最后,与包一起来沪的某青年团员资助15元,包惠僧才有赴穗旅费。[7] 《共产党》也因缺乏经费,只出了六期。[8]
1921年,由于资助中国学生旅法勤工俭学「华法学会」破产,许多留法学生顿陷困境,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没有地方学习或聚会。1921年2~3月间,周恩来在巴黎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共,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
从南开中学毕业,一直漂泊不定饱受生存之困、前途渺茫的周恩来终于安定下来,有信仰、有组织、有让他感到充实的活动,还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共产国际向他们提供了衣食无忧的支援。
1924年6月下旬,经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向党代表廖仲恺推荐15名共产党员,周恩来为第一名。廖同意后,向周恩来寄出归国路费。周恩来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9月1日抵香港,数日后入穗。 [9]
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Hendricus J.F.M.Sneevliet,1883~1942)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1921年6月初至12月10日期间中国共运: 「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维经斯基(Gregori Voitinsky,即吴廷康)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10]
1921年11月,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维经斯基已回俄。李达记述:
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任党的经费。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覆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就与陈独秀闹起意见来。……我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极力弥缝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李汉俊余怒未息,不肯代理书记,就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我,要我做代理书记,我只好接受下来。当时党的工作,因为缺乏经费,都暂时停顿,只有《新青年》月刊仍旧继续出版,我们就在《新青年》写稿子。[11]
经费问题差点阻挡「革命车轮」哩!
1921年陈公博起草的〈广东共产党的报告〉:
我们感到最遗憾的是缺少钱。《劳动界》停刊了,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我们的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继续下去。[12]
经费问题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难题,撮选几则史料。1929-9-19鄂西特委负责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经费:
我们最低限度的预算每月300元(交通费公办费150元,生活费房租在内150元),宜昌机关四个、沙市两个、郝穴一个,共七个机关,如少了则万万办不到,而省委只允许200元,假如是做生意,我要300元,他还200元,早已成功。无奈我们不是生意,200元实在办不到,也是无法啊。[13]
1934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连遭严重破坏,经济一时陷于绝境,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主动拿出四万美金,帮助中共度过难关。[14]1935年秋,河北省委因与中央失去联系,经费无着,只得一边紧缩机关,一边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五十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五十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15]
1935年底的「价廉物美「(张申府语)的「一二·九」学运,散发传单仍需阿堵垫衬,北平学联的成本为100大洋。[16]
二、 资助中共成立
为避免孤立无援,赤俄政权稍一稳定,便急着「输出革命」。1919年3月2日,列宁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规划世界革命。1920年4月中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外事处代表维经斯基赴沪。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为其筹措经费,派遣特使携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变卖,不止一次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某次带去的款额为2000美元。[17] 俄共最感兴趣的当然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运,给维经斯基的任务是克服中国革命的分散状况,将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成立。[18]
1920年秋,《新青年》杂志开始接受共产国际资助,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引发著名的「胡陈分流」。[19] 1921年1~2月,广州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领到俄国人给的生活津贴(每月20港元)[20]
维经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国组建赤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出正式使节马林来华助建中共,最实质的支持当然是金钱。6月6日,马林抵沪,[21]立即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六个外地支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东京)寄送通知,邀请每一支部派两名代表赴沪与会,每位代表汇来路费100元。[22] 据说回程时再领50元川资,毛泽东就是靠这笔钱于会后游历杭州南京。毛此时在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年薪仅百余银圆,他不断给报社投稿以赚稿费,很辛苦。[23] 直到获得中共中央每月寄来湘省活动经费(从60银圆一路增至170银圆),毛泽东的经济状态才彻底改善。[24]
有关赤俄资助中共成立及国共合作,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1894~1979)记述清晰:
1920年维经斯基来中国,与陈独秀、李大钊及其它有关人员联系,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当然马林是执行第三国际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宁命令办事的。
……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的酝酿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25]
1921年8月,陈独秀夫妇、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五人被捕,马林使尽力气,聘请法国律师应诉,花了许多钱打通会审公堂各关节,最后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罚款五千元结案,所有款项皆由马林向共产国际领取支付。此前,陈独秀与马林政见分歧很大,这次被捕促成两人和解,陈独秀承认中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接受领导,并通过赤色职工国际(又称「红色工人国际」)接受共产国际经援。[26]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27]
中共三大一结束,马林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
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
党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党早产并过多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28]
1925~26年,随着国民革命热浪,中共党员从不足千人增至上万。1926年5月20日,俄共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29]
俄共不仅仅向中国输出革命,还向日本、蒙古、朝鲜等东方各国共产党提供经费。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1895-?,原姓赫尔扎诺夫斯基,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华代表)的工作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给国外工作的拨款……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30]
三、 苏联经援概况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刚结束,张国焘(1897~1979)草拟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与工作计划,以上海为总部,京汉穗及长沙设立分部,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各地出版地方性工人刊物,约30人领取津贴2035元/月,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为每月一千零数十元。马林表示均由共产国际补助。[31]
1923年4月30日,陈独秀打收条认领共产国际寄交中共的四、五月经费一千墨西哥元。5月19日,再认领2940港币(折合三千国币)。7月10日,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专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32] 马林档案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援。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3000元;1925年预算月领2250元,4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三万元以上;1928~32年,每月预算五万元左右。1927年以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如1927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三万元,开办党校得五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得款近五万元,9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一万元,12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十万元。1928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万特别费。[33] 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章士钊也为他筹了两万元,这即毛后来厚待章的「出处」之一。[34]
1926~1927年春,仅李大钊经手的经费就达数万,款子均由穗汉国民政府处汇来。[35] 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6000元/月;1927年再增经费预算1.2万元/月。1927年7月5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1927年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须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捕一带二。共产国际代表为此拨款千元。1927年8月国共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拨给中共的经费增加到2万/月。[36] 1927年9月6日,莫斯科电令上海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请在年底前给中共拨款17128美元」。[37]
据中共历史档案财务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中共各项款额接近100万银圆,这一数额相对于苏联这一时期援助国民党与西北军冯玉祥累计5000万银圆虽微不足道,但对尚处婴幼期的中共来说,年助百万已是天文数字了。[38]
国共合作期间,赤俄还大力资助广州国民政府。1926~27年,为支持国民党北伐,赤俄援助国民革命军五架飞机、五万余支枪及其它军火。[39] 苏联顾问对广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背后可是站立着强大的经援,包括资助赴俄学生的各种费用。如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每月十个卢布津贴、精美伙食、郊外疗养等,以及1927年秋入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学生,每月津贴30卢布,都出自赤俄财政。[40]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苏联提供约十万卢布经费。联共(布)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1928年6月11日再拨九万卢布给中共应急。[41] 共产国际1928年上半年拨款12.5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增至34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1928年月均超过六万元。[42]
1928年尾,共产国际决定从1929年起每月削减中共经费3.3万中国货币单位(即每月从六万降至约3.7万)。[43]192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此专函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共经费每月六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中央并决定今后严格按照新预算开支,各省1.9万元不变,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压缩为3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交通费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二元,原有的娘姨费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44]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880~1931)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45] 直至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入江西苏区,来自苏联的固定经援才中止。但被停发的相当一部分经费,共产国际建立「中共基金」,仍谋求以某种方式支持中共,只因苦求人员往来中断无法交递。[46]
1933年10月下旬,团中央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均被捕,此前被捕并叛变的党中央局书记盛忠亮(1907~ )入狱劝降:「……现在党中央局、团中央局都几乎全部破坏了,连最微薄的活动经费因同国际方面的联系断了,也难以维持了……」[47] 中共总书记、党中央局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成为国民党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资助的确凿证据。
红军长征抵陕后,1936年6月16日终于架起大功率电台,中共中央向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一封电报,就直述财政情况,「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并要求给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12月5日,张闻天再驰电:「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48]
1936年12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向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向中共)「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1938年2月,共产国际经援中共50万美元。[49] 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了30万美元。[50]1941年7月7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100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51]
俄援直到抗战结束后仍在继续,苏联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批军械转拨中共,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迅速膘壮,成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资本。1948年东北战事结束,全境陷赤,林彪四野准备进关,中共少将李逸民记述:「东北全境都解放了,接着准备120万部队进关。苏联的援助物资也来了,有轻武器,有汽油。」[52]
四、 陈独秀报账
向共产国际报账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主要工作之一。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它约二千余元。」[53] 十分明确,经费主要来源「国际协款」,自募党费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6%。
1925年3月2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结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54]
1925年4月9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十分详尽的年度收支报告,撮要精述:
1924年1~6月预算:
一、收入:800美元和10174.93元。(均来自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
二、支出:300美元和9341.366元。尚余520美元和833.064余元。
1924年7~10月预算:
一、收入:14510.0164元。二、支出:12053.234元。尚余2456.93多元。
1924年11~12月预算:
收入: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产国际给中共四大援款870元;C、向鲍罗廷借款1000元;D、过去结余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支出:A、中央委员会2554.17元,内含机关及各种开支432.82元、工作人员生活费1903元;邮件电报128.65元、(交通运输202元、专项开支162元、印刷598.7元。B、地方组织2548元,其中北京550元、铁路总工会200元、山东233元、湖南100元、唐山:90元、武汉275元、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运动1850元。D、偿还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学生联合会借款20元。
收支相抵尚余552.055多元。[55]
五、 为经费闹矛盾
经费问题一直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摩擦点。中共「一大」前后围绕是否接受经援,争论激烈;此后则为款额多少与拨款拖滞不断「摩擦」。
「一大」之前,李汉俊(1890~1927)就向马林表示:中国共运当由中共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从旁协助;中共只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希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展开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时接受共产国际的补助;共产国际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顾问,决不应居领导地位。马林碰钉子后,急盼能与更有影响力的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见面。[56]
1921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晤马林,基调仍是「闹独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国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援助,以免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党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语,会对产生中共无中生有的攻击。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十分紧张。此时,张太雷到沪,奔走陈独秀、马林之间。一次,张太雷在陈宅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发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一拍桌子:「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挟起皮包气愤走人。[57] 李汉俊、陈独秀这一最初的「闹独立」,成了中俄赤党关系的一大基调。
一次,陈独秀在党内会议上怒拒共产国际经援:「何必国际支持才能革命!」马林大惶,逊谢不已。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争执,致使会议无法继续。[58] 陈独秀对李达等人说:每月只拿他们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于人,十分难堪,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陈独秀连接几周不出来与马林会面,不愿每周向马林汇报工作。[59] 陈独秀认为:中共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国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接受人家的钱就得跟随人家走,而且一时也没什么工作可干,要钱也没用处。陈独秀还认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需要100年,要革命青年重视学习,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现实。[60]
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也取得重大进展,鲍罗廷等抵穗,国民党即将改组,俄共对华工作重心发生转移。马林认为「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61]为此,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援助发生问题。1923年11月,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莫斯科:
首先应该强调一下它的财政困难情况……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个事,并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由于没有钱,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停止。[62]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哪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63]
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成为苏联在华的唯一援助对象,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握拨款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1928年2月,他致信共产国际联络局长:
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二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共)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要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64]
但他也为中共增拨预算呼吁:
促使我到莫斯科来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给中国共产党拨款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二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建议拨给党总的预算为3.5万墨西哥元……责成它按时拨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责成它拨其它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2/3用于报刊。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3.5万元。[65]
六、 中共干部的生活
1928年,中共中央委员领到的生活费为27元/月。1928年5月7日,苏兆征、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
……深信正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近半年来党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最近有几个同志被逮捕,法国人拒绝把他们移交中国当局。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资金的话,党组织就可以把他们解救出来。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物质援助。党希望共产国际能像它过去在物质方面援助国民党那样来援助它。期待你们尽快就此问题作出答复。[66]
1929年秋~1930年初,后为托派骨干的王凡西(1907~2002)任中共组织部干事,中组部长周恩来助手之一。他在回忆录中说:「党费收入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25元,区委会的同志为19元。这个数目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类,或有家属而『住机关』者,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但足够维持。」[67]
1934年任团中央局宣传部长的黄药眠(1903~1987),每月领伙食费12元,零用交通费三元,添置衣服鞋袜要向组织再提申请。一次黄药眠买东西多用五毛钱,受到组织批评,说他经济观念不正确,做了半天检讨。[68]
其时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谢觉哉(1884~1971):「每月生活多的给30元,少的给10元,即是说除房租外,每天至多花一元。那时黄金每两值洋112元。」[69]
中共职业革命家众多,超过非职业化党员,根本无法用党员缴纳的党费维持职业革命家的生活。1927年6月1日,中共政治局用党章规定党费缴纳:月收入不满20元减免;30元以内月缴2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别征收;失业工人或在狱者免缴。[70] 事实上,党员所缴党费甚微。
1927年10月,中共在上海收容南昌暴动被打散的归队者,一时没有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二角生活费,首次发放最多只给二元。[71]1931年4月,广西红七军东调部队负伤干部王震,因地位不高,尽管携妻带子,给他的生活费也只有每天二元,住旅馆及伙食都包括在内,度日艰难。红七军第十九师长龚楚,因是高干,左腿重伤,每天给生活费三元,另加电疗费二元。龚妻前来照料,还要帮助红七军其他在沪疗伤干部,「在极其节省的情形下,尚可维持。」但也仅仅维持,无力添衣购物。贴光个人存款后,龚楚打报告要求增补生活费,始终未得增额。这位后来成为「红军第一叛将」的龚楚,晚年仍抱怨:「迫不得已将电疗的次数减少,以维持日常必需开支。有时我想起我在广西工作时,为党筹措了五万元港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活动经费,另外支持香港日报亦用过一万多元。我抛弃家庭温暖,为革命流血,现在必需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无法维持,未免太刻薄。」[72]
周扬(1908~1989)抗战前在上海:「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73] 周扬据称周瑜后裔,然家道衰落,倒是其妻吴淑媛(1908~1942)乃当地大户。周扬最初在沪搞革命,全靠岳家经援。1934年暑假,周扬爱上光华大学女生苏灵扬,与之同居,将发妻送回湖南益阳,断了岳家接济,经常上胡风处告贷,求借三五元菜金,「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74] 1936年苏灵扬临盆,阵痛难忍,周扬身无分文,没法送医院,急得团团转。其女周密:「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75]翻译《安娜·卡列尼娜》得酬约800元,周扬经济状态才有所好转。[76]
不少革命青年因为经济原因,无法坚持「职业革命」,只得离开中共队伍。1938年秋,重庆党员周健因家庭经济拮据,只得到歌乐山某儿童保育院任教,离开了职业革命岗位。[77] 「一二·九」后参加中共的李锐、范元甄,由于没有经济来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残等,都需要家庭或亲友资助,尽管这些「职业革命家」看不起供养自己的「不革命者」。[78]
穷则思变,贫穷固然是革命的天然元素,但穷人一般很难参与革命。1925年秋,湖北送11名青年团员留苏,规定自行解决从汉口到上海的路费及自备服装。贫家子弟伍修权拿不出这笔钱,靠武昌高师附小级任老师张朗轩慷慨解囊40元,才得以成行。而熬度西伯利亚寒冷的那件短大衣,由同学相赠。[79]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各地知青纷纷赴延,但仅凭革命热情与青春决心是到不了延安的。陕西临潼知青何方(1922~ ),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一箭之遥,但仍需筹集路费。「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参加革命各需60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介绍信,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卡车赴延,每位车资14块大洋。[80] 因此,赴延知青绝大多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有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家庭本身很少出读书郎,更不可能送赴延安。
七、 初期红军经济一瞥
1928年1~4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因驻地富庶,粮饷易筹,官兵一律月饷12元,远高于国军,部队几无逃兵。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地瘠民贫,每月只能发大洋三块。「当时三个大洋可买一百斤糙米,因此农民都喜欢参军。」随着人马壮大,存款很快告罄,前敌委员会「决定全部粮食由没收富户存粮补给,每日每人发给五分菜钱(每月一元五角),另每月每人发给零用钱二元。」1928年初毛泽东能抽美丽牌香烟。就是月饷二元,由于物价低廉,一角钱可买猪肉半斤或12个鸡蛋,「与一般农民比较,生活还好得多,待遇虽薄,他们亦感满意。官兵开小差(逃兵)的现象几乎没有。」[81]
红军退入贫瘠山区后,经济压力是除了国民党军事进剿以外的最大压力。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向湖南省委报告:「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82] 阶级觉悟、革命意志之类,都是后来的文艺宣传,史实真相当然是靠饷聚兵,红军亦非「特殊材料制成」。穷人参加革命的前提是必须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因此,只有当革命闹腾起来,有了地盘与财力,穷人才有可能成批跟进。
1929年加入红军的邱会作说:红军没有固定财源,发的物品多为打土豪没收来的,搞到什么发什么,也不管合有不合用,只要能解决困难就行。打下吉安后,商家诉红军有抢掠行为,一些士兵进钟表店抢的闹钟,勤务兵系在胸前让长官看时间,贵重的手表一声没动,因为不知道手表更好用;进百货商店抢的也是马灯、手电筒,其它值钱的东西也没拿。因为这些来自山区农民的红军士兵并不识货。邱会作承认:不会花钱、商品意识淡漠,乃这一代中共高干之通病。[83]
长征抵陕,红军仍靠「打土豪经济」。1937年底还在吃大户,薄一波在山西沁县城招待彭德怀:「今天我们就放开肚子吃一顿,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豪劣绅那里弄来的,一个钱不花,算是‘借花献佛’了。」[84]
八、 飘出史褶的证据
最后坐实接受赤俄经援,当然只能是中共自己。1982年,中共出了内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8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再出公开本,内有陈独秀1922年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中共三大的政治报告,敲实赤俄为早期中共经费的惟一来源。
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有荷兰学者托尼·塞奇(Tony Saich)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俄援的具体史料。如1922年12月9日,张国焘、蔡和森打收条从一俄人处预支12月工作用款400美元。[85]
苏联解体后,赤俄档案浮出数据。1994年、1996年俄文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25)、(1926~27),1997年、1998年中国出版中译本,具体披露赤俄经援的细节。[86] 1997年、1998年,英文版《中国法律与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杂志也在1997年第一、二期上,发表一组从1930年代中后期直至19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直接涉及共产国际的财援。[87] 2001年,俄国学者石克强(Konstantin Schevelyoff)整理了九份来自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发表于北京的《百年潮》,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1920~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援助的线索。[88] 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奎松研究员发表了《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本文多处引用),对这一专题做了较为详尽的史料梳理。[89]寰内国人这才明白「远方」(共产国际)对中共之所以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脚。
近年史料表明:苏联1945、1947年两次将日本关东军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中共。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德造武器、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可能通过北朝鲜转运)。据载,北朝鲜曾将2 000车皮「日军遗留」战略物资交给中共。1942~49年,美国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45个步兵师, 1945~48年,中共依靠苏械组建了210 个步兵师。[90]
初稿:2008-5; 修改:2011-3-25~30
[1] 袁首乐:〈湘军经济清单的发现及其意义〉,《安徽史学》(合肥)1987年第三期,页27。
[2] 范泓:〈同盟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同舟共进》(广州)2011年第三期,页45~47。
[3] 郑宪:〈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吕芳上译,《近代中国》(台湾)1979年6月第11期。转引自范泓〈同盟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页43。
[4]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2004年,页90。
[5] 陈明远:《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00。
[6] 朱文华:《陈独秀传》,红旗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17。
[7]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66。
[8] 〈李达自传(节录)〉,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
[9] 蔡咏梅:《周恩来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页27~31。
[10]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7-11),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2。
[11] 〈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年9月第一年,页3~4。
[12] 陈公博:〈广东共产党的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内部刊物)1981年5月第一年,页2。
[13] 周逸群:〈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19日于上海),《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11月第一年,页57。
[14] 朱正明:〈延安杂忆〉,原《传记文学》(北京)1993年第一期,页107。
[15] 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页174~175。
[16] 姚锦编着:《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98年12月第一年,页28。
[17]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北京)2004年第一期,页6。
[18] (俄)K·B·石克强整理:〈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李玉贞译,《百年潮》2001年第12期,页55。
[19] K·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苏)《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年,页159。
[20] 〈谭祖荫的回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年,页121。
[21] 马林抵沪时间一向模糊,此处根据(荷)弗·梯歇尔曼:〈马林政治传记〉(1974),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五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参见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年,页238。
[22]《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年,页368、427~428。再参见包惠增:〈回忆马林〉(1979年6月),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年,页95~96。
[23] 毛泽东:〈致罗学瓒信〉(1920年11月26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泽东早年文稿》编辑组合编《毛泽东早年文稿》,湖南出版社(长沙)1990年7月第一年,页562、565。
[24] 张戎、乔·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9月初年,第21页。
[25] 包惠增:〈回忆马林〉(1979-6),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95、106。
[26]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72、431。载包惠增:〈回忆马林〉(1979-6),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01~102。
[27]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档选集(1921~1925)》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168。
[28]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6-20),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243、245。
[2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5-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页267。
[30] 〈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5-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85。
[31]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52~153。
[32]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6-20),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150~151、168。
[33]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5年5月第3版,页209。
[34]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上海)2002年,页6。
[35] 李大钊:〈狱中自述〉,《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11页。
[36]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北京)2004年第1期,页13~15。
[37] 〈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35。
[38] 徐焰:〈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页30。
[39] 林伯渠:〈从同盟会员到共产党员〉,王来棣采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第一年,第23页。
[40]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页128~129、155。
[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9号(特字第28号)记录〉(1928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492~493。再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北京)2004年第二期,页16。
[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35号(特字第34号)记录〉(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521。再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续)》2004年第二期,页16。
[43] 〈向忠发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电报〉(192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77。
[44]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二期,页17~18。
[45]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75年出版,页163。
[46]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二期,页24。
[47]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年,页260~261。
[48] 〈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二期,页25~27。
[49]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年,页48、64。
[50]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第一年,页190。
[5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年,页147。
[52]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年,页164。
[53]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1989年8月第一年,页47。
[54]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二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页593。
帝俄金卢布于1914年退出流通,1921年赤俄政府恢复使用帝俄金卢布为结算单位,可兑换4083卢布;1921年上半年一金卢布兑换11300卢布。1923年,赤俄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首批苏联金币,一新金卢布含金量相当于旧俄十金卢布,兑换率为一新金卢布折1923年发行的175卢布,或1922年发行的17500卢布。
[55]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一期,页10~11。
[5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32~133。
[57] 包惠增:〈回忆马林〉(1979-6),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00~101。
[58] 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1979),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07~108。
[59] 〈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7~8。
[60]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67。
[61]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6-22),载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89~90。
[62]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页316。
[63]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页529。
[64]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360。
[65]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360~363。
[66] 〈苏兆征和向忠发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8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页445~446。
[67]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3月第一年,页125~126。
[68] 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年,页246。
[69]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年,下册,页934。
[70]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年,页154~155。
[71] 李逸民:《李逸民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6年11月第1年,页58。
[72]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社(香港)1978年5月初年,下卷,页335、337。
[73]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号。参见朱鸿如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年,页236。
[74]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年,页117。
[75] 周密:〈怀念爸爸〉。参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年,页578。
[76]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年,页123。
[77] 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1980年代前后中国思想理论风云及其他》,时代国际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12月第一年,页362。
[78] 李南央编:《父母昨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1960年通信、日记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一年,上册,第169页。
[79]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七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页120。
[80]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邢小群录音整理,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7年9月初年,上册,页41、45。
[81]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出版社(香港)1978年5月,上卷,页147、165、148、165~166。
[82]〈中共湘西南特委军委关于红四军仍应留湘赣边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7-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册三,页27。
[83] 程光:《心灵的对话》,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下册,页724。
[84] 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 《人民日报》(北京)1988-10-23,年4。
[8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张、蔡的收条〉(1922-12-9),参见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毛研室、近代史所现代室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98。
[8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8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88] (俄)K·B·石克强整理:〈俄罗斯新发现的有关中共建党的文件〉,李玉贞译,《百年潮》(北京)2001年第12期,页55~60。
[89]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期,页1~18;《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续),《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2期,页14~31。
[90]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美)2000年夏季号,注释4。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1年6月号(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