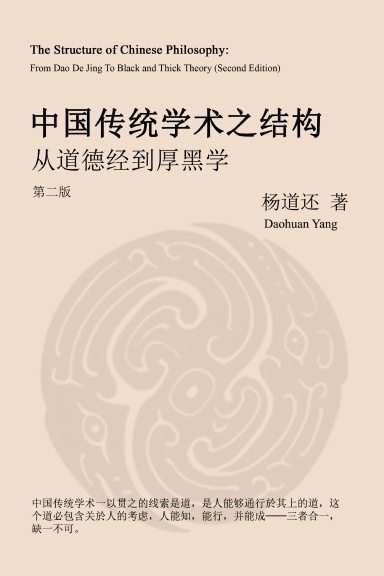 当今世界,以动力横扫一切的西方理性工具主义已经推演到极致,其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日益加剧。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主张宽容哲学,企图消除这种理性扩张;后来的哈伯玛斯(Juergen Habermas 1929-)提出沟通哲学。用沟通来融合世界各类文明的冲突。这些大智大勇的哲学家,都看到理性工具主义的危害,也提出了一些解救的办法。可是我们看到,这种用理性来疗伤理性的办法是微乎其微的。欧盟主张“沟通对话”解决世界外交的手段收效甚微:伊朗、朝鲜的核武危机依然存在;独裁国家的人权迫害更加猖狂;而中东的恐怖主义更是益无忌惮。原因是这个理性的肿瘤已根植人类的头脑中。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理性的局限性就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想不到今天的怀疑和独断更加猖獗。一个人,他从小就接受那种知性教育: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早就渗透其中,其理性观念牢不可破,你的宽容、沟通能起作用吗?我们清楚地看到,与恐怖分子讲宽容,讲沟通,无异于与虎谋皮;与独裁者讲人权,他只有把你当傻子——所有种种,就是其观念已根植于脑袋之中,把它当作一切行动的准则。理性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法自救。
当今世界,以动力横扫一切的西方理性工具主义已经推演到极致,其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日益加剧。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 1864-1920)主张宽容哲学,企图消除这种理性扩张;后来的哈伯玛斯(Juergen Habermas 1929-)提出沟通哲学。用沟通来融合世界各类文明的冲突。这些大智大勇的哲学家,都看到理性工具主义的危害,也提出了一些解救的办法。可是我们看到,这种用理性来疗伤理性的办法是微乎其微的。欧盟主张“沟通对话”解决世界外交的手段收效甚微:伊朗、朝鲜的核武危机依然存在;独裁国家的人权迫害更加猖狂;而中东的恐怖主义更是益无忌惮。原因是这个理性的肿瘤已根植人类的头脑中。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理性的局限性就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想不到今天的怀疑和独断更加猖獗。一个人,他从小就接受那种知性教育: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早就渗透其中,其理性观念牢不可破,你的宽容、沟通能起作用吗?我们清楚地看到,与恐怖分子讲宽容,讲沟通,无异于与虎谋皮;与独裁者讲人权,他只有把你当傻子——所有种种,就是其观念已根植于脑袋之中,把它当作一切行动的准则。理性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法自救。
多年来,我对人文哲学的很多新理论,新突破,新真理,新思想感到特别的沮丧与无奈:在新潮流狂热的鼓动下,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基本上都是一种理性反思之作,看不到更进一步的形而上学思考。他们自称已掌握宇宙真理,已破解了人类命运的锁链,实则只是一些标新立异,信口雌黄,自欺欺人,哗众取宠的浮躁之作。有多少人能真正坐下来认真地做反转又反转的悟觉,得出真正的学问来?人文哲学的学术,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理性分析论的结果。人文学术领域受科学技术研究方法论的影响,如今的人做学问,先定一个关键词,然后对这个关键词进行分析,抽丝剥茧,旁徵博引,资料堆积,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分析研究方法,已蔚然成风,作为是做学问的固定格式。他们已忘记了更大的综合,已没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综合统一。这种分析论的学问,在科学技术领域来说,是非常有效和进步的。但在人文领域来说,则是一种大灾难和毁灭性的打击。人文科学不断分析,最后必然是分析出灵魂基因,把人的本性、人与鬼神的关系都摧毁了。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道本,生存的价值意义何在?正如庄子所说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
人类的堕落,文明的缺失,很多的不幸,是他自身造成的。
人类要自救,不是在创造什么新理论,也不是什么新思想,新学说就能将人类拔起扶正的。太阳必定要落山,黑夜是要到来的,我们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个历史规律,回归道本。华夏古老的先民老庄、孔孟,早就悟觉出道来,已有足够的智慧,应对今天的人类生存困境。“反诸求己”,无须再创造什么新的东西。
当我对中国人文学术界抱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几近心灰意冷的时候,一年前,一个朋友转来一则信息。一个叫杨道还的先生,想要我写的《中国古人“吾”之哲学观》一文的资料。因此我就与杨先生书信交往起来。这一来往,令我大感兴奋。我们对老庄道的悟觉,都有一种“志同道合”的见解。他在与我讨论“吾”与“我”不同意涵时说,“我几年前研究‘吾我’问题,想有所验证,找到了您的上述文章,真是喜出望外——比我所想还要彻底。……我以为,庄子《齐物论》中‘吾丧我’,是庄子天人合一的关键。吾是那个与天合的,而我则是天地之‘委形’、‘委蜕’(《知北游》)而已。这个吾,与《老子》中的吾是同一个意思,这是老庄学术互通最关键的一个联系。老庄的道和德,所有出入,都可据此理顺。由此《老子》不再是玄学,而是与任何人都有一个联系,这个联系即是,任何人都可凭籍《庄子》去得到吾,然后窥道。人无时无处不在道中,不可逃,却不能识得道,问题不在于‘道可道,非常道’的困难,而在于‘我’不能‘识’,这种不能辨识是由于‘吾’的缺位:有的人,虽然知有余,却不能识,对道视而不见,这与王阳明深山识花的典故正成对比。由此出发,我从庄子到老子,又转回来通往墨子和孔孟,将他们的学术整理成一图,花了十余年写成了《中国哲学之结构》一书。”
我终於遇到一个得道之人了。有了一个既可以言,又可以训的道人。我们几次书信来往,虽然不多,但很有哲学意义。有次我在信里说,世界是不可以认识完毕的,每一个认识都是一个意向性,不可能有绝对的认识。就像我们计算圆周率,它总是留下一个小数点,不可能计算完毕。道还来信说,他前几天正在思考这个圆周率的问题,不想就收到我说的圆周率。我与道还先生未曾谋面,但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一致认为,老庄的道,靠理性认识来开启,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吾”的悟觉,才能得道。有时我们谈论读古书的心得,他说读古书,一定要达到与古人神游的地步,才能领略古人说话的真正意义,我刚好也有此体会。很多人先入为主,觉得古人不如我们现代人聪明,自以为了不起,读出古人的学问不是垃圾就是不如自己。这种人做出来的学问,不是糟蹋古人,就是与古人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不可能看到古文明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了。
道还先生大作《中国哲学之结构》之意义,在於他能进行综合判断,“先立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孟子语)他把中国先秦文化哲学:老子、孔子的道立起来。他从李宗吾的哲学思想受到启发,找到一个“匡廓图”,然后在“匡廓图”架构下进行阐述论证。洋洋大观,古人之大哲学,就这样被道还先生立起来了。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哲学早熟”(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早在几千年前它就达到鼎盛时期。梁先生并指出西方哲学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唯物论与唯心论),而中国哲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我称之为思维与思维的关系,是讲人类和谐的学问。),它很少指涉到自然方面。就“格物致知”来说,它也不是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这个致知,最终还是为悟道目的服务的。中国的哲学,特别是先秦哲学,已发展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特别是老子的道,已到了不用思、不可言说的地步,已抵达人类哲学的最高境界,但由於华夏文化哲学的久远,长期的破坏和失传,再加上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人再也看不到自己哲学的博大精深,看不到那“大化流行”、在人类历史洪流中屹立前行不倒的哲学。很多现代公知,认为华夏文化就是一堆垃圾,没有逻辑性,不科学。有的甚至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
我在研究先秦哲学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奈:我华夏哲学文明,明明摆在那里,有史记载,有文载道,博大精深,“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语),何以到了我们现代人的手里,特别是到了懂得一点西方哲学,懂得一点逻辑学的学者手里,则变成中国没有哲学了呢?
我在这中国哲学黄昏的途径漫步也很长久了,总不见有来者,心有戚戚焉。这个“道可道非常道”,能被我们挖掘出来吗?我们用思,用辩证法,是不可以证成的。人只有在“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易•系辞传》)《中庸》也说,“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者,其孰能知之?”(《中庸》)老庄、孔孟的道,其哲学的精髓被埋没也久远了,有几人能聪明圣知达天者?而达天者又有几个“吾”能出来述说清楚?
我终於等来道还先生的出现。我们书信交往不久,他寄来他的大作。《中国哲学之结构——从道德经到厚黑学》,让我为之一振。此书终於把中国的哲学结构阐发出来了,打破了中国没有哲学的谎言。他的“匡廓图”构思,不是冯友兰先生的形而上学说不能说的哲学论述,也不是某些哲学家用辩证法上下折腾的论证,更不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将道归为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简单化约。他揭宇宙之太极,示人生之宿命,解往圣之绝学,开智慧之境界。他的思路明确,内道与外道化经纬分明,很好地将我华夏哲学的精髓阐述出来。道还先生的大作,为中国哲学立於世界哲学之林,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工作。此书得到出版,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文哲学的一件盛事,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幸事。作为同道者,愿为其书做个吹鼓手。是为序。
黄鹤升
戊戍年七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