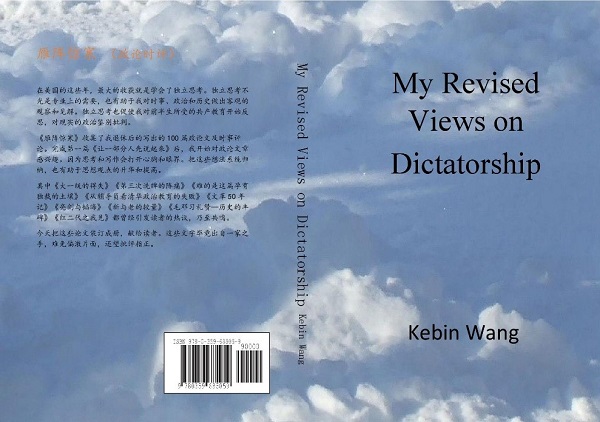铃铃铃……一阵急促而响亮的铃声,把一群素不相识的男孩子,从楼道里赶到一八班的教室。 他们在各自的位子上静静地坐下, 一双双大眼睛好奇地往前探视,等待初中第一堂课的来临。
不一会儿,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人,手里拿着课本,从容地走到讲台前。只见他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服,头发灰白,向后背着。双目略微突出,炯炯有神。他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林万选。然后,诙谐地说:“我叫林万选,是一万个人里选出来的。” 引起大家轻松的一笑, 使得原本有些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多。林老师接着又用英文字母写了“林”字,其中,L是花写的,在起笔时打了个反阿尔法的绳结。让我觉得漂亮新奇。
接着,他自我介绍说,他毕业于辅仁大学,主攻英语,选修数学。他将是我们的班主任,除了英语,还要教代数。然后,他教我们用英语说早安,要求我们每天在老师走进课堂时,全部起立,大声对老师说,“Morning Sir,!”他再回我们说 :“Morning Boys.!“面对着这样一位满腹经纶的老先生,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敬意,为遇到这样一位老师而感到庆幸。暗自思念着我得把英语学好。
第一堂课相当简单,只是重复地念彼德和安娜(Pete and Ann)。老师又教了我们几个字母,还有相关的国际音标。在教音标的时候,他非常认真。让我们严格地按他的口型发音。在这堂课上,他还引进了清辅音和浊辅音的概念。老师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带着我们大声地朗读。我都觉得有些口干舌燥了,可从老师身上,看不出一点倦意。老师这麽高的工作热情也令我十分感动。
那时候,我还不大知道中苏关系这种深奥的大道理, 只知道在58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学都只教俄语。自打我们这一届起,突然增设了英语班。当俄语的余温尚存的时候,我不知为什麽偏偏选择了英语,难道是机缘巧合?当时,初一的八个班中只有两个是英语班。现在回想起来,林老师作为英语专家,刀枪入库已有了七八年之久,好钢一旦被征用到刃上,他那蓄势已久的积极性一下子在我们这个小天地充分迸发出来。
放学回家,我一改往常先玩耍后作业的习惯,第一件事就是把小饭桌搬到院子里,拿个小板凳,静静地坐在桌旁。我把老师教过的单词一遍又一遍地写着读着,最后,把它们一个一个地记在一个小本上。每一行的左边,写着英文,右边写着汉文意思,并且把它们编了号。从此以后,每学到新单词,我都把它们按顺序记录下来,一直到初中毕业。把英语作业完成后,又继续做好其他的作业。初中第一天,我好像搭上一趟直快列车。前面有一个依稀的目标在吸引着我。为它,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听写和拼音测验我都得到满分。为了肯定我的进步,林老师常常买些小奖品, 当着大家的面给我。比如说,有毛主席的像章、铅笔、本儿等。奖品虽小,但对我确是很大的鼓励。有一次,我在英语作业中,写了一篇关于水库和鱼的短文。 虽然只有五六行字,老师却拿到另一个班上去读,说是一八班五号写的。从那时起,学英语的同学都知道我这个五号了。老师的这种勤于褒奖的教学方法,确实行之有效。每次都象一根鞭子,抽在一匹小马的身上,不痛却痒,让它别松劲,持续地往前跑去。
当我刚进这个班时,什麽职务都没有。皆因我在小学的纪录实在平庸。几个星期以后,我由于英语课总是满分,被选为英语课代表。对英语课的高度兴趣,使我端正了对其他课程的态度。代数、语文、历史、地理, 无一落后。于是,过了一两个月,大家又推荐我做学习委员。从此,我不但坚持努力学习,还逐渐树立了责任感。到了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成了一八班的班长。一个在小学不起眼的孩子,如今当了班长了。这是个多大的跃迁呀。其中又融合了多少老师的心血和汗水。
在庆祝1959新年的全校大会上,老师用英文写了一篇讲稿。让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去念。那时,我才学了四个月的英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感到这是一种莫大的激励。林老师在引导学生上进,真可谓用心良苦了。如果说我是一棵小树,林老师就是第一个把我扶正并且精心浇水施肥的园丁。遗憾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忙碌的学业与工作中,没有腾出时间去回忆园丁的苦心,也从未专程去看过林老师一次。
如今,林老师已经永别人世,我只好把眼泪化作墨汁,写出那一幕幕的往事,作为对林老师的感谢和悼念。一个人长大以后,大多数都会孝敬自己的父母,不仅因为血统,还有那千金难买的养育之恩。可是,有多少人会惦记他们的老师,以寸草之心去回报那三春之辉呢?就连我这饱受厚爱的弟子,也未能尽晚辈之心,行尊师之道。作为老师,他们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却从未想过回报。这大概就是老师这个职业的高尚与伟大之处吧。
林老师对教育的热忱不仅表现在认真负责的教学工作中。他努力跨越年龄的代沟,经常在课下同我们在一起。 班上有几个同学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吹口琴,他也从家里拿来几个两边都有孔的口琴来,大概是西洋货,同我们一起吹奏。他还教我们唱英语歌。开始时,教唱早晨好,用的是现今流行的祝你生日快乐的曲调。后来,又叫我们唱那首“我们的红旗就是战旗”。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努力地跟上社会形势。他一句一句地教唱着,还不时地校正着发音。
在社会上提倡勤工俭学的时候,他不甘落后。为我们构思出做黑板擦这个课题。在学校木工老师的协助下,我们班做出了几十个板擦。后来还到师大附中去展出。这些活动培养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初二年纪的辅导员沈国英还为我们编写了一个班歌。歌词大意是,“我们是一八班,真是不简单,大同学小同学,团结意志坚,嗨嗨,要做红旗班。”老师常常亲自指挥我们唱班歌,增进我们对集体的热爱。这班歌把40多个同学的心拧到一起。在一次班级比赛中,一八班如愿以偿,真的成了全校的红旗班。
林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他对我们做的每件错事都会严肃地批评和指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们有七八个同学到东单体育场去打篮球。球场明文规定不许在里面骑自行车。可我们几个在打球之余竟然饶着球场赛起车来。当我们骑得正欢实的时候,管理人员制止了我们,并且通知了学校。第二天一早,林老师就把我叫到教师预备室,他的严肃神情令我惴惴不安。他狠狠地批评了我。他说我是班长,应该带个好头儿,以后不许再犯。
有一次在英语课上,老师叫起一位叫郭启东的同学,让他用“you are” 造句,他不假思索地说:“You are banana。” 然后用“ I am” 再造一句,他说:“I am father.” 课堂上浑然一片笑声。老师非常生气,把郭同学罚到了门外。老师在他的课桌上,拿起他的笔记本,念着郭的汉语注音。“你死贼死不可死。” (这是不是书),让老师哭笑不得。还有一次,一位叫林海的同学课上看《林海雪原》。 老师把他叫起来,问他为什麽看小说?他说:“我没看,就是瞧瞧。”老师把他的书给没收了。
提起林老师的往事,不得不说说坐在他面前的40几个学生。北京市第90中学是个创建才有一年之久的只设初中部的新学校,它位于崇文区的金鱼池西侧,离昔日的龙须沟不远。是北京穷区里的穷角落,亦即穷的平方。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劳动家庭,家长们以卖苦力者为多。有的竟连个正经活儿都没有,属于地地道道的城市贫民,拿不出两块钱的学杂费。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这些穷孩子从未有过歧视和讥笑。相反,从他的言行,经常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每当看到同学不认真学习的时候,他都会语重心长,不无感慨地说:“你们的父母为了养家糊口,披星而去,带月而归。你怎麽向他们交待呀?”老师多麽希望他能把这些个孩子培养成材,改变家里的贫寒处境,间接地帮他们的父母一把。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调教过的这个班上,居然有好几个人上了高中,接着又有四个进了大学。这四个人里,有两个进了外贸学院,一个是外语学院,我侥幸进了清华。其中,有三个都是和英语有关的专业。林老师的英语教学算得上硕果累累了。同内城的重点学校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的升学率未免过于寒酸,难于启齿。可是 在一个辍学率高出百分之十的这所年轻中学,能够涌现出这几棵秧苗,已经是个可喜的收获了。
就我个人而言,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父亲十四岁到北京学徒,母亲不识字。他们忙于工作和家务,没时间也没能力启发孩子的智慧,更不用说让孩子出生前就能享受到美妙奢侈的胎乐了。以致于我这个棒槌连续两年都考不进市立的一中心小学。到了八岁的9月1号早晨,才让私立的普济小学的刘立曾老师来不及面试,稀里糊涂地把我收作门徒。从此我开始启蒙,渐开茅塞。证明了我原来不是傻子,也有跟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能力。
然而直到小学毕业,我还只是个顽童。学习一般,品行中常。我未来的目标也就是象我父亲那样守在家门口,当个工人,奔波劳碌。林老师的出现成了我心中熠熠发光的亮点。 他高擎着一根蜡烛,一步一步地引导我去接近一个从未听说过的稀奇烂漫的境界,一点一点拨发着我求知的心弦和欲望,使一个不懂事的顽童变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中学生。是他传给我的知识,是他对我的每一份关心与鼓励,才使得我们这个世代工农的家庭,出了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直至第一个留美博士。
当我步入花甲,有空回首反顾的时候,朝着当初起步的原点望去,我看到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站在90中学的门口,默默地向我微笑。他就是当初那位第一个把我推上求知列车的林老师。
敬爱的林老师,您的音容与笑貌,您的奉献和热忱,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间。
安息吧,林老。
2006年1月于弗吉尼亚
2021年8月修改于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