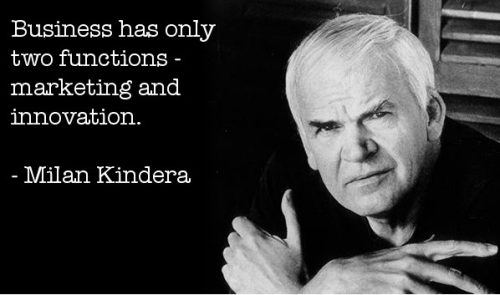雅罗米尔继续在跑,而世界继续在变:他的姨父,那个认为福尔特尔是伏特发明者的人,被诬告犯了诈骗罪(和成百的商人一道)。他们不但把他的商店收归国有,而且还判了他几年刑。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被驱逐出布拉格。他们带着冷冷的沉默离开了这幢房子,由于雅罗米尔投靠了这个家庭的敌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玛曼。
政府把这幢别墅空出来的底层楼分配给另一家人,这家人很快就采取了粗暴、挑衅的态度,新来的房客是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搬来的,因此认为任何人拥有这样宽敞、舒适的别墅都是极大的不公平。他们觉得他们不只是到这幢别墅来住的,而是来清算一个过去的历史错误。没有请求任何人的许可,他们在花园里为所欲为,并要玛曼把房子的墙壁修理一下,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时,剥落的墙灰可能会危及到孩子。
外婆愈来愈老了,她已经丧失了记忆,于是有一天(几乎没有感觉到)她化成了火葬场的青烟。
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玛曼对儿子的逐渐疏远感到特别难以忍受。他正在学习的学科她很反感,他不再把他的诗歌给她看。当她想打开他的抽屉时,她发现它己上了锁。就象脸上挨了一耳光。想到雅罗米尔在怀疑她窥探他的私事!她求助于一把雅罗米尔不知道的多余的钥匙,但当她检查他的日记时,她没有发现任何新的记载或新的诗歌。然后她注意到墙上已故丈夫的照片,她回想起她曾经怎样恳求阿波罗的塑像从正在她子宫里生长的婴儿身上抹去象他丈夫的一切痕迹。哎,莫非她丈夫在坟墓里都要与她争夺对雅罗米尔的所有权吗?
在前一章结尾时,我们把雅罗米尔留在了红头发姑娘的床上。大约一周后,玛曼再次打开他书桌的抽屉。在他的日记里,她读到几句她不理解的简洁的话,但是她也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新的诗歌。她觉得阿波罗的七弦琴再一次战胜了她丈夫的军服,她暗暗地高兴起来。
读完这些诗后,这个好的印象得到了增强,因为她真心喜欢它们(实际上,这是她第一次真诚地欣赏雅罗米尔的诗!)。它们是押韵的(在内心深处,玛曼始终觉得不押韵的诗决不是真正的诗),完全明白易懂,充满美丽的诗句,没有衰弱的老人,没有土里腐烂的尸体,没有松垂的腹部,没有眵垢的眼睛。相反,这些诗提到鲜花,天空,云彩,有几处,(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甚至还出现了”母亲”这个词。
雅罗米尔回家了;当她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所有这些年的辛酸苦辣忽然都涌上眼睛,她禁不住热泪纵横。
“什么事,母亲?怎么啦?”他轻轻地问,他的声音里很久都没有这种温柔了,玛曼尽情地把它吸收了进去。
“没什么,雅罗米尔,没什么。”她回答,看见儿子对她关心,好哭得更加厉害。再一次,她流下了多种眼泪:为她的孤独的悲伤的眼泪,为儿子抛弃她的指责的眼泪;为他有可能回到她身边的希望的眼泪(受到他那新的旋律诗行的刺激);为他站在她面前那笨拙样子的气愤的眼泪(难道他就不能至少抚摸一下她的头发吗?);还有企图软化和俘虏他的虚假的眼泪。
终于,尴尬的犹豫之后,他拉住了她的手。太好了,玛曼停止了哭泣,她的话就象刚才的眼泪一样滔滔地涌出来。她谈到她一生中的所有委屈:她的守寡,她的孤独,企图把她赶出她自己房间的住户,不再理悉她的姐姐(”都是因为你,雅罗米尔!”),最后,最重要的是——她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密朋友正在摒弃她。
“可那不是事实。我没有在摒弃你!”
她不会为这样轻易的回答平静下来。她苦笑了;他怎么能这样说?他总是很晚才回家,有时连续几天他俩都不交换一句话,甚至当他俩偶尔谈点话时,她也非常清楚,他根本没有在听,他的心在别的地方。是的,他正在变成一个陌生人。
“可是,母亲,那不是事实。”
她又苦笑了。噢,不是?难道她必得向他证明这点吗?难道他想知道真正最伤害她的是什么吗?他有兴趣吗?那么好吧。她一直尊重他的秘密,甚至当他还是一个小孩时。为了让他有自己的房间,她曾与家庭中其他成员进行了多么艰难的斗争!而现在——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侮辱!一天打扫他房间时,完全出于偶然,她发现他因为她而锁上了书桌抽屉,他怎么想她当时的感觉!为什么要锁它?谁可能会愿意干涉他的私事?难道他认为,她除了打探他的事就没有别的更要紧的事可干了吗?
“哎,母亲,这是一个误会!我几乎没有使用那个抽屉!如果它被锁上,那只是出于偶然!”
玛曼知道儿子在撒谎,但这无关紧要。比他的话更重要的是他话音里的顺从,它象是一个和好的礼物。
“我愿意相信你,雅罗米尔。”她说,紧紧握住他的手。
当他瞅着她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淌满眼泪的脸。她冲到浴室里去照镜子,她感到恐怖;她那泪湿的脸看上去很丑,身上穿的那件过时的灰衣服只是使情况更糟。她轻快地用冷水洗了脸,换上一件粉红色的睡衣,从橱柜里取出一瓶红酒。她开始再次对雅罗米尔讲,他们俩应该更加相互理解,因为在这个世上,他们除了对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这个话题她谈了很久,她觉得雅罗米尔的眼里好象流露出激动和赞同。因此她鼓起勇气说,她毫不怀疑他——一位正在成人的大学生——有他个人的秘密,她尊重他的秘密,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雅罗米尔生活中的这个女人不会损害他俩之间的良好关系。
雅罗米尔耐心、理解地听着。过去一年他之所以回避他的母亲,是因为他的不幸需要孤独和黑暗。但自从他在阳光灿烂的海岸——红头发姑娘身上幸福地登陆以后,他就一直渴望和平与灯光;他对母亲的疏远破坏了生活的和谐。除了感情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与玛曼保持良好关系的更实际的需要:红头发姑娘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而他——一个成年男人——却仍然同母亲住在一起,只有通过女主人的独立才能实现一个独立的生存。这种不同使他痛苦不堪,因此他很高兴玛曼此刻同他坐在一起,穿着一件粉红色睡衣,啜着酒,象一位悦人的年轻女人,他可以跟她友好地讨论他的权力和特权。
他声称他没有什么可隐藏的(玛曼由于焦急的期待,喉头都绷紧了),他开始对她讲起红头发姑娘。当然,他没有提玛曼在她买东西的那个商店里已经见过这位姑娘,不过他说明了这个年轻姑娘是十八岁,她不是大学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姑娘(他几乎好斗地说出这句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玛曼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觉得事情似乎在朝好的方面转变。雅罗米尔描述的这位姑娘的形象消除了她的忧虑。姑娘很年轻(以为是一个久经情场、堕落的女人的恐惧想法愉快地消失了),她几乎没受什么教育(因此玛曼不必担心她的影响力量),雅罗米尔这样热烈地强调她的朴实和善良,她不仅猜想这姑娘不是太漂亮(因此可以设想,儿子的迷恋不会持续很长)。
雅罗米尔感觉到,母亲并没有不赞成他对红头发姑娘的描绘,他很高兴,懒懒地幻想着他很快就可以同他的母亲和他的红头发姑娘坐在同一张桌旁;同他童年的守护神和他成年的守护神。这一切似乎象和平一样的美好;在他自己的家与外面世界之间的和平,在他两个守护神翅膀下的和平。
于是,在长时间的疏远之后,母亲和儿子,正在品尝他们的亲密。他们愉快地聊天,但雅罗米尔仍然一直在想着他那不过分的,实际的目的:给自己的房间争得权利,在那里他愿意什么时候带姑娘来就可以带她来,在那里他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因为他正确地领悟到,一个人只有当他是一块明确规定的场地的主人,一个完全的个人小天地的主人时,他才是真正的成年人。他用一种拐弯抹角、小心翼翼的方式对母亲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说,如果他能认为自己在这里是自己的主人,他会更加乐意待在家里。
玛曼从微醺的飘飘然中醒过来。警觉得象一只雌老虎。她顿时意识到儿子想说什么。”你是什么意思?雅罗米尔,难道你在家里感到不自在吗?”
他回答说他非常喜欢他的家,但是他希望有权邀请他愿意邀请的人,象他的女友一样不受约束地生活。
玛曼开始意识到,雅罗米尔无意间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毕竟,她也有几位爱慕者,由于害怕雅罗米尔的遣责,她不能邀请他们到她的家来。用雅罗米尔的自由来换取她自己的一点自由,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吗?
但是,当她想象一个陌生女人在雅罗米尔童年时代的房间里,一阵难以克制的厌恶就涌上心头。”你得承认,在一个母亲和一个女房东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她激烈地说,她知道,她将毁掉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过充实生活的机会。她对儿子肉欲的厌恶强于她自己身躯对肉体满足的渴求,这一发现使她感到恐惧。
还在固执追求目标的雅罗米尔,不了解母亲内心的骚乱,他继续强调他那失去的理由,进一步提出无用的论据。过了一会儿,他才注意到母亲在啜泣。一想到他伤害了童年时代的守护神他就非常惊恐,于是他陷入了沉默。从母亲的眼泪里,他突然看到他对独立的要求是无礼的,傲慢的,甚至是下流无耻的。
玛曼绝望了:她看见他俩之间的鸿沟再一次张开。她一无所获。却失去了一切!她随即试图想办法保持住儿子与她之间那根珍贵的理解之线。她拉住他的手,透过泪水说:
“请别生气,雅罗米尔!我只是因为你的变化而感到不安。最近你变得非常厉害!”
“变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母亲。”
“是的,你变了,你和过去不同了,最使我伤心的是你不再写诗。你过去常写一些多美的诗!现在你把它完全放弃了。这使我伤心。”
雅罗米尔想要说点什么,但她不让他说。”相信你的母亲,”她继续说,”我对这些事有一种感觉;你有非凡的才能!这是你的天赋。低估它就太可惜了。你是一个诗人,雅罗米尔,一个天生的诗人。我很难过,你并不重视它。”
雅罗米尔沉醉在母亲的话里,高兴极了。千真万确。他孩提时代的守护神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他!由于他不再写诗,他曾经是多么沮丧!
“但是,我现在又在写诗了,母亲!真的!我拿给你看!”
“没有用,雅罗米尔,”玛曼悲哀地摇摇头。”不要哄骗我。我知道你已经不再写诗了。”
“你错了!请等一下!”他叫道。他跑到他的房间,打开拍屉锁,带着一札诗走回来。
玛曼瞧着几小时前在雅罗米尔房间看过的那些诗。
“噢,雅罗米尔,这些诗真是太美了!你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很大的进步!你是一个诗人,我为你感到非常高兴……”
仿佛一切都在表明,雅罗米尔对新事物的强烈渴求(对新事物的信仰)不过是掩饰一个童贞青年对不能想象的性经验的渴求。当他第一次到达红头发姑娘身躯的极乐海岸时,他产生了一个奇特的念头:现在他终于知道绝对现代的含义是什么了;它就是躺在红头发姑娘身躯的岸上。
在这样的时刻,他活跃之极,充满热情,真想给她朗诵诗歌。他在脑子里迅速回忆了一下所有熟记的诗(他自己的和其他诗人的),但他断定(大为惊异地)红头发姑娘也许对这些诗根本不会关心。这使他头脑一阵混乱。接着他明白了,唯一的绝对现代的诗是红头发姑娘,一个普通姑娘,能够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诗。
这是一个突然的启迪;他为什么那样愚蠢,竟想要踩在自己的歌喉上?为了革命而放弃诗歌有什么道理?毕竟,他终于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雅罗米尔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一个游行人群,肉体之爱,革命口号的旋转的边界),现在他只需完全投入到这个新生活中,成为它的小提琴弦。
他感到充满了诗情,极想写出一首红头发姑娘会喜欢的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在此之前,他只写过自由诗,没有那种更有结构的诗歌形式的技巧。他确信,姑娘会认为无韵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诗。甚至获胜的革命也持同样的观点。让我们回忆一下,在那些日子,无韵诗甚至被认为不值得发表。所有现代派诗都被宣布为腐朽资产阶级的作品,自由诗是文学颓废最确信无疑的特征。
革命对韵律的喜好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偏爱吗?大概不是。在韵律和节奏中,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一旦挤进有规律的音步,混乱的世界随即变得井然有序,清楚明了,美丽迷人。如果一个女人厌倦人生走向死神,死亡便与宇宙的秩序和谐地融为一体了。即使这首诗是为了对人的必死进行强烈的抗议,死亡作为美好抗议的诱因也是正当的,骸骨,送葬,花圈,墓碑,棺材——这一切在一首诗里都变成了一出芭蕾,读者和诗人都在其中表演着他们的舞蹈。跳舞者当然不可能不赞成舞蹈。通过诗歌,人类达到了它与存在的一致,而韵律和节奏便是获得一致的最天然的方式。难道革命可以无需对新秩序反复证实吗?难道革命可以无需韵律吗?
同我一道狂吼!内兹瓦尔激励他的读者,波德莱尔写道,人生须常醉……酒中,诗中,道德中,各循其志……诗歌即酣醉,人们饮酒是为了更加容易与世界融合在一起。革命不希望被审视或被分析,革命只渴望同群众融合在一起。因此,革命是抒情的,需要抒情风格。
当然,革命所追求的抒情风格与雅罗米尔早期创作的那种诗截然不同。一段时期,他曾急欲追求内在自我的平静冒险和迷人暗示。然而,现在他清除了他的灵魂,把它变成了一个表演真正世界喧闹马戏的宽阔场地。他用只有他才理解的独特的美去交换人人所理解的一般的美。
他迫不及待地想起旧式的奇迹,艺术(怀着背叛者的骄傲)已经嗤之以鼻的奇迹大众化;落日,玫瑰,晨露,星辰,对故土的怀旧之情,母爱。多么美好,熟悉,清晰的世界!雅罗米尔惊喜交加地回到它那里,象一个浪子多年漫游后又回到家中。
啊,要简单,绝对简单,简单得象一首民歌,一个孩子的游戏,一道潺潺的溪水,一位红头发的姑娘!
啊,要回到永恒之美的源泉,热爱简单的词语,例如星星,歌曲和云雀——甚至”啊”这个词,这个被蔑视被嘲笑的单词!
雅罗米尔也受到某些动词的诱惑,尤其是那些描写简单动作的词;走,跑,特别是漂和飞,在一首庆祝列宁周年纪念的诗中,他写道,一根苹果树枝被投到小溪里,树枝一直漂流到列宁的家乡。没有一条捷克的河流到俄国,但诗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河水可以改道。在另一首诗中他写道,世界很快就会自由得象松树的芳香漂浮在山顶上。在另一首诗中他唤起茉莉的芳香,这香味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变成了一艘看不见的帆船,在空中航行。他想象自己在这艘芳香四溢的船上,向远方飘去,一直漂到马赛,根据一篇报纸上的文章,马赛的码头工人正在罢工,雅罗米尔希望作为一个同志和兄弟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他的诗歌也充满了所有运动方式中最有诗意的东西,翅膀,夜晚随着翅膀,轻轻地拍打而搏动。渴求,悲伤,甚至仇恨都有翅膀。当然,时间在不变地沿着它那带翅膀的路行进。
所有这些诗句都暗示了一个对广大无边的拥抱的希望,使人联想到席勒的著名诗句:Seid,umschlungen,Mi-llionen!Diesenkussderganzenwelt!(德语:大家拥抱吧,千万生民!把这亲吻送给全世界!——译注)这种对宇宙的拥抱不仅包括空间,而且还包括时间,不仅包括马赛的码头,而且还包括那个神奇、遥远的岛屿——未来。
雅罗米尔一直把未来看成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神秘事物。它包含着一切未知的东西,因此,它既诱人又令人恐惧。它是确定的反义词,是家的反义词,(这就是为什么在焦虑不安期间,他要梦想着老人的爱情,他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再有未来)。然而,革命赋予了未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不再是一个神秘事物;革命者熟悉未来。他从小册子,书籍,报告,宣传演说中知道了它的一切。它不令人恐惧;相反,在一个不确定的现在,它提供了一个确定的安息所,革命者朝它伸出手臂,就象一个孩子朝母亲伸出手臂一样。
雅罗米尔写了一首描写一个共产党工作者的诗。一个深夜,当喧哗的会议被晨露代替(在那些日子,一名战斗的共产党人总是被表现为一名喜欢争论的共产党人),他在书记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窗下的电车铃声在这位党的工作者的梦里,变成了世界上所有钟摆的欢乐洪亮的声音,宣告将不再有战争,全球属于工人阶级。这位党的工作者意识到,靠神奇的一跃,他不知怎么已来到了遥远的未来。他站在一块田地之间,一位女人驾驶着拖拉机朝他驶来(未来的妇女通常被描写成拖拉机手),她惊讶地认出这位工作者就是从前的社会主义英雄——往昔的劳动者,为了她现在能自由而幸福地耕地,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从机器上跳下来迎接他。”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世界。”她说,并想要报答他。(看在上帝面上,这位漂亮的年轻女人怎么能报答一个疲倦不堪的老工作者?)这时,窗上的电车发出特别有力的鸣声,这位睡在党的办公室角落的狭窄沙发上的男人醒了过来……
雅罗米尔写了好几首类似的新诗,但他还是不满意。除了雅罗米尔和他的母亲,没有人读过这些诗。他把它们全都寄给日报的文学编辑,每天早晨都要细心地翻阅报纸。一天,他终于发现三版上方有一首五节四行诗,他的名字用粗体字印在诗题下面。这一天,他骄傲地把这期报纸递给红头发姑娘,要她仔细地看一遍。姑娘未能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她通常忽略诗歌,因此根本不注意作者的名字),雅罗米尔最后不得不用手指着这首诗。
“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一个诗人!”她钦佩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雅罗米尔告诉她,他写诗写了很久了,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札手抄的诗。
红头发姑娘开始读这些诗,雅罗米尔告诉她,有一段时期他曾放弃了诗歌,是她鼓舞了他回到它身边。遇见她就象遇见了诗歌本身。
“真的吗?”她问,雅罗米尔点了点头,她拥抱他,吻他。
“奇妙的是,”雅罗米尔继续说,”你不仅是我最近写的诗歌的女王,甚至也是我认识你之前写的诗歌的女王。当我第一看见你时,我就觉得我过去的诗变得栩栩如生,成了一个象你这样女人的化身。”
受到她脸上显露的好奇、不理解的神情鼓励,他继续对她说,他曾经写了一首长长的散文诗,一个幻想故事,描写了一个名叫泽维尔的男孩。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写这首诗,只是梦到过它,希望有一天把它写出来。
泽维尔的生活与别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睡着了,又做了一个梦,从这个梦中醒来,他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就这样,他从一个梦渡到另一个梦,同时过着几种不同的生活。他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这不是一种很美妙的生存吗?没有拴在一个单一的生活上,虽然是一个人却又过着多种的生活。
“是的,我想这会是很好的……。”红头发姑娘说。
雅罗米尔继续说:当他第一次在商店里看见她时,他就大吃了一惊,因为她长得与他想象中泽维尔最亲爱的人一模一样:虚弱,红发,淡淡的雀斑……
“可是我很丑。”红头发姑娘声明。
“不!我爱你的雀斑和火红的头发!我爱这一切,因为它是我的家,是我从前的梦!”
姑娘又吻他,他继续说下去。”请想象一下,整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泽维尔喜欢穿过煤烟熏黑的市郊街道漫步。他常常打一个底楼窗户经过。他总是停留在窗前,幻想着那里也许住着一个漂亮的姑娘。一天,窗户里的灯亮了,他看见了一个温柔娇弱的红头发姑娘。他情不自禁了。他推开窗户,跳进了房间。”
“可你却从我的窗户边跑掉了!”姑娘笑起来。
“是的,不错,”雅罗米尔回答,”我跑掉了,因为我害怕我在从现实跨进幻想。你知道吗,当你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曾在梦中见过的情境时,会是什么感觉?你会惊恐得想拔腿就跑!”
“可不。”红头发姑娘愉快地赞同。
“就这样,在故事里,泽维尔从窗户跳进去追求姑娘,但这时她丈夫回来了,泽维尔把他锁在了一个沉重的橡木衣柜里。那位丈夫直到今天还在那里,成了一具骷髅。泽维尔把他的恋人带走去了远方,就象我将把你带走一样!”
“你就是我的泽维尔。”红头发姑娘感激地在雅罗米尔耳边悄声说。她顽皮地用泽维和泽维克的呢称称呼他。然后紧紧地拥抱他,吻了他很久,直到深夜。
雅罗米尔到红头发姑娘的住处去过许多次,我们想回忆其中的一次,那次姑娘穿着一件前面有一排白色大钮扣的衣服。雅罗米尔试图把这些钮扣解开;姑娘大笑起来,因为它们不过是用来作装饰的。
“等一等,我自己来脱,”她说,然后伸手去拉脖子后面的拉链。
雅罗米尔为自己的笨拙而感到窘迫,当他终于弄清楚衣服的原理时,他急欲想弥补自己的失态。
“不,不,我自己来脱。别管我:”她一边笑着,一边从他身边往后退。
他如果再要坚持就显得可笑了,但他却被姑娘的行动搞得心烦意乱。他相信,一个男人应该为他的情妇宽衣解带——否则这整个动作就与普通的、日常的穿衣脱衣毫无区别了。这个观点不是基于经验,而是基于文学,以及文学中引起联想的句子:他是一个给女人脱衣服的行家;或者,他用熟练的手指解开她罩衫的钮扣。他不能想象性交之前会没有一阵迫不及待的、兴奋慌张的解钮扣,解拉链和解钩子。
“干嘛要自己脱衣服?你又不是在看病!”姑娘已经匆匆脱掉了衣服,只穿着内衣裤。
“看病?你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觉得整桩事就是这样的。象一个医生在检查病人。”
“我明白了!”姑娘笑起来。”也许你是对的。”
她解下胸罩,站在雅罗米尔面前,挺着她的小Rx房。”我有点疼,医生,就在我的心脏下面。”
雅罗米尔似乎没有懂这个玩笑。”请原谅,”她抱歉地说,”你也许习惯让你的病人躺下检查。”然后她伸直身子躺在沙发上。”请仔细瞧瞧我的心脏。”
雅罗米尔别无选择,只好照办。他俯在姑娘的胸脯上面,把耳朵放在她的心脏上。他的耳垂贴着她胸部的柔软垫子,从她躯体的深处,他听见了有节奏的怦怦声。他突然想到,当一个医生在神秘、紧闭的诊室门后检查红头发姑娘的身子时,他感到的也正是这个声音。他抬起头,瞥了一眼赤裸的姑娘,感觉到一阵强烈、痛苦的忌妒。他在用一个陌生男人的眼光,一个医生的眼光看她。他匆匆把双手放在她的Rx房上(这决不是医生的方式),以便结束这场令人痛苦的游戏。
“医生,你真调皮!你在干什么?那可不是检查的部位!”姑娘抗议道。
雅罗米尔怒火填膺。他看到女友脸上的神情,就和一个陌生人的手抚摸她时会出现的那样。看见她轻浮的抗议,他真想打她。但同时他意识到他已变很多么兴奋,于是扯掉姑娘的衬裤,进入了她的身体里。
他是那样兴奋,妒火很快地熄灭了,尤其,是当他听到姑娘的呻吟和叹息(这个绝妙的效忠),以及”泽维!泽维克!”的爱抚之词,这些词已经成为他俩亲密仪式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然后,他平静地躺在她旁边,轻轻地吻着她的肩膀,感到非常愉快。但是,从不满足于一个美好的片刻乃是雅罗米尔的不聪明之处。对他来说,美好片刻只有作为美好永恒的象征才是有意义的。从一个玷污了的永恒中掉下来的美好片刻是骗人的谎言。因此他想确信他俩的永恒是完全纯洁无理的。他用恳求多于寻衅的口气问,”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愚蠢的玩笑,那桩与医生的事。”
“是的,当然,”姑娘回答。对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能说什么呢?然而这并没有使雅罗米尔满意,他继续说:
“如果别人抚摸你,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实在不能忍受!”他把手拳成杯状放在姑娘发育不全的、可怜的Rx房上,仿佛他未来的幸福就全在它们的不受侵犯了。
姑娘笑起来(十分天真地)。”但是,如果我生病了该怎么办呢?”
雅罗米尔意识到他不可能排除一切医疗检查,他的阵地是守不住的。但他也知道,如果一个陌生人的手打算触摸姑娘的Rx房,他的整个世界就将坍成碎片。他重复说。
“我不能忍受!你明白吗?我实在不能忍受!”
“那么当我需要医生时,你要我怎么办呢?”
他用平静而带责备的口气说,”你可以找一个女医生。”
“我有什么选择?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她忿忿地叫起来。”我们全都被指定给某一个医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你知道社会主义的医疗是怎么回事。他们命令你,你就得照办。比如,妇科检查……”
雅罗米尔心头一沉,但他镇静地说,”喔,你有什么毛病?”
“噢,没有,只是为了预防。为了防治癌症。这是法律。”
“闭嘴,我不想听这个!”雅罗米尔说,把手搁在她的嘴上。这个动作是那样猛烈粗鲁,他担心姑娘会误以为是一个耳光,生起气来;但她的眼睛非常谦卑地望着他,以致他觉得没有必要为他无意的粗鲁动作道歉。事实上,他开始欣赏这个动作,于是继续把手搁在姑娘的嘴上。
“我告诉你,”他说,”如果别人用手指摸你一下,我将永远不再摸你。”
他仍然把手掌按在姑娘的嘴唇上。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女人的肉体使用暴力,他觉得这令人陶醉;他用双手箍住她的脖子,仿佛要把她掐死。他感觉到她的喉咙在他的手指下已变得虚弱,他突然想到,只要把两个拇指往下压,他就可以轻易地扼死她。
“要是别人触摸你,我就要把你扼死。”他说,继续扼她的喉咙;一想到姑娘的生死掌握在他手中,他就感到高兴。他觉得到至少在此刻,姑娘是完全属于她的,这使他充满了一种令人愉快的权力感,这种感觉是那样销魂,他又一次进入了她的身子。
在作爱过程中,他几次狂暴地压她,把手搁在她的喉头上(在性交中扼死情人,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并咬了她几次。
然后,他们紧挨着躺下休息,但这次性交持续得并不太长,也于是因为它没能平息雅罗米尔的愤怒;姑娘躺在他身旁,没有被扼死,仍然活着,她的裸体使雅罗米尔想到了医生的手和妇科检查。
“别生气,”她说,抚摸着他的手。
“我没有法子。一个被许多陌生人摸过的身子使我恶心。”
姑娘终于明白了他是当真的。她哀求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只是在开玩笑!”
“这决不是玩笑。这是事实。”
“不,不是事实。”
“别说了!这是事实,我知道我对这也无能为力。妇科检查是强迫性的,你不得不去。我不责备你。但是,被别人摸过的身子使我恶心。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
“我发誓,这全是我编造的!我从小就没生过病。我从不看病。我的确收到过一张妇科检查的通知,但我把它扔掉了。我从没去过那里。”
“我不相信你的话。”
她极力向他保证。
“那好吧。但假如他们又叫你去呢?”
“别担心,他们太缺乏组织,不会注意到我没去。”
他相信了她的话,但他的痛苦不会被理智所平息。毕竟,他的痛苦并不是真正由医疗检查引起的。她在迷惑他,她并不完全属于他,这个感觉使他非常痛苦。
“我爱你,”她反复说。但这个短暂的片刻不能使他满足。他想要占有永恒,至少占有这姑娘生活中的永恒。而他没有占有它。甚至她从处女跨入妇人的那一小段生活都是属于别人的。
“我无法忍受别人将会抚摸你。而且有人已经抚摸过你。”
“没有人将会抚摸我。”
“但有人已经进入过你的身子。真叫人恶心。”
她搂抱他。
他把她推开。
“多少个?”
“一个”
“你在说谎!”
“我发誓!”
“你爱他吗?”
她摇了摇头。
“你怎么能同一个你不爱的人睡觉?”
“别再折磨我!”她说。
“回答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别再折磨我!我不爱他,那真可怕。”
“可怕什么?”
“别问。”
“有什么可隐瞒的?”
她突然流出眼泪,向他坦白,那人是她村里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他令人厌恶,他曾摆布她(”不要问我,你不会想了解这件事!”),现在她已竭力忘掉了他的一切(”如果你爱我,永远不要使我再想起那个男人”)。
([捷克]米兰·昆德拉著,景凯旋译)
(未完待续)
(努努书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