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作者: 以赛亚·柏林
译林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2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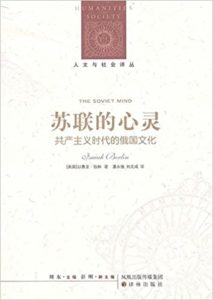
对苏联事务,伯林既是冷静的思想者,又是保持距离的观察者
作为曾经的俄罗斯人,后来的英国驻俄外交官和热爱自由的学者,无论从哪方面看,伯林对俄罗斯的持续兴趣都顺理成章。这册文集,除了最后一篇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的《不死的俄罗斯知识阶层》是较宽泛的时评类文章,其余部分都集中关注俄罗斯历史的黑暗时期。这段时期里,俄罗斯遭受了纳粹德国的入侵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俄罗斯有过无数伟大的心灵,最坏的年月愈发能衬托出这些心灵的可贵。第五纵队式的内部绞杀,不仅直接损害这些心灵,更破坏了他们栖居的土壤。
伯林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不尽相同,亨利*哈代在《编者序言》里介绍得很清楚,有向政府提交的备忘录(《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有受编辑所托而写的评论文章(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另一篇鉴赏文章《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为专业杂志(或机构)撰写的文字(《人为的辩证法》等)和自己的私人回忆(《访问列宁格勒》等)。不同的动机、题材、文体,保证了行文视角的多元,加之伯林又是整个苏联时代的见证者,所以这本书有特殊的价值。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顺理成章的期望,却往往滑向不切实际的狂热,影响了到对周围世界的清醒认识。伯林既是坚持自由主义的冷静思想者,又与苏俄社会保持了恰到好处的距离,所以他的证言有摆脱”当事者迷”的可能。
伯林借助外交官的身份,流连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观察普罗大众的精神面貌。尽管文字平实,没有晦涩或华丽的惊人之语,但是他的印象记要比一般旅游者、记者和许多职业学者都深刻和周全许多。他亲身接触的俄罗斯,令人颇有似曾相识之感。1956年,后斯大林时期初段,和他交谈的学生”期望的是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找个好工作,外出旅游,谈恋爱,挣更高的薪水,好好地享受生活,而丝毫没有远大的抱负、意识形态的热情、民族主义情绪,或对任何公共问题的敏感”(P118)。常规的意识形态教育仍然继续,却对个人主义的盛行束手无策。普通人”认为原则上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专制,政府就不可能进行高效的运转,他们并不相信国外有真正的民主,尽管他们承认国外在物质文化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外国公民的生活也更加的舒适”(P120),但是在他们身上又不乏淳朴和友善的光辉。后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尚未曝光,统治者/被统治者二分的社会中弥散着劫难过后惊魂未定的病状。
分享类似的文化,让伯林更容易与俄罗斯的作家、诗人成为真诚的朋友,像老乡重逢一样回忆思古抚今。在全部国民当中,这只是极微小的一群人,却更为直接地传承所谓”大传统”的使命。自身的声望、对民族的爱以及前诗人斯大林对的看重,合力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中。那时候,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定也需要斯大林本人亲自定夺,连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要插嘴说上几句。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虽然斗胆据理力争,但是他的意见根本算不了什么数。(参见西蒙诺夫,《斯大林文学奖评选内幕》,《狂飙突进,悲歌未绝》,P166-191)伯林讲述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们的悲剧,大浪淘沙,最后剩下的是不是金子见仁见智,但是他们内心的坚强自不待言。
记录自己亲身感受的俄罗斯社会、文化时,伯林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古怪行止描画得一清二楚。纳粹德国的侵略让俄国变得更团结,并不足以带来荒诞不堪的副作用。这是”大清洗”之后的岁月,官方作家、技术官僚、钻营者们与伟大领袖一道,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封闭、迟滞、逢迎和恐怖,把民族文化中恶的因子,如历史主义和唯一真理论发挥到极致。在黑暗时期坚守可贵心灵的作家们,是个松散而开放的群体,与自己身处的时代几乎格格不入。广为人知的故事之外,伯林提供的种种碎片佐证了这些心灵的特别。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流亡海外的机会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耀,他本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这些,来反证制度的错误,但是近乎固执的忠诚又不允许他做出这个无所谓对错的决定。伯林列举出来许多帕氏精神力量的来源,比如他的家庭与托尔斯泰的友谊,比如斯克里亚宾、别雷和马雅可夫斯基。他坚守了”白银时代”的荣光,也维护了俄罗斯思想家的荣光,由此”赢得了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一致尊敬”(P87)。简略看来,阿赫玛托娃是另外一种类型,她批判托尔斯泰的说教,甚至”把他看作自负的魔鬼,自由的敌人”,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但是同样乐于欣赏外面的美好。所有一切都可可以略过不谈,最重要的是她说到卡夫卡—-“他写书给我并写关于我的故事”(P75),又是一个美好的传奇。
不同的坚守让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有了不同的伟大,还有许多人,在在晦暗时代有一颗能发出光亮的心。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为了后人的榜样。可悲的是,他们本该为自己而活,为诗歌和文学而活,根本没有义务成为道德偶像,忍受摧残。但愿他们从来没有机会,成为令人扼腕的道德楷模。
伯林指出斯大林时代的病根是一种”人为的辩证法”,伟大领袖通过摇摆不定的”路线”让他的小集团保持一定限度的恐慌,并进而将这种统治术的效用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身上。其后果便是伯林看到的麻木和史书上记载的恐怖。回望故国,他不敢有丝毫的乐观。他不无悲哀地写道,”统治者也许残酷无情、玩世不恭,甚至被绝对的权力严重地腐化:但只有出于强烈的义愤和坚定的信念而非从实际的实际的观察和历史的经验中得出的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才会使某些苏联的研究者预言这些恶行本身必将很快腐蚀那些作恶的人,让他们无法继续掌权,从而自取灭亡。被统治者,一群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羔羊,也许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得极其玩世不恭,渐渐变得冷酷无情,但只要实行的是一种迂回的’路线’,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能有些短暂的喘息,他们尽管经历了种种苦难,但仍然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还能—-仅仅是还能—-忍受并继续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乐的理由。”(P112)
及至苏联解体,伯林看到了俄国特有的”知识阶层”的薪火相传,期望俄罗斯人因自由而为世界带来”惊喜”。但是他的乐观相当谨慎,他说”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自豪”(P160)。时过境迁,斯人已逝,环视现在的俄罗斯和全世界,很难确定老先生的期望究竟有多少变成了现实。
(四季书评2017-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