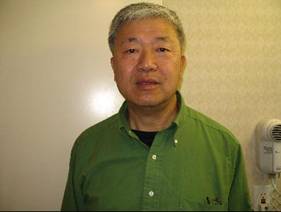【苏晓康按:老康停了他的脸书,偶有得意之作,会来央我帮他贴出,这不,他忽然从旧友处得着几张照片,勾出他的一段回忆,落到文字上乃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故事,却充满了关于饥饿、存活、动物等等的张力,中国人在瘟疫、病毒、囚禁之前的记忆,大概只有饥饿吧?】
有位友人传来马栏农场柳树坪站近照,原来这处关押劳动教养犯的监狱已废弃了。我曾在该站服刑三年,这场景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柳树坪是盛产土豆的地方,那是一种紫皮土豆,个儿大,淀粉含量多,吃起来很面,若吃一大口而下咽太急,很容易把你噎住。但自我们到达此地,从没有放开肚皮吃过土豆。我们劳教大院建在低处的山坳上,围一圈高墙,墙内又一圈号舍,中间空出的一大片院子是我们平日活动的场地。从院子里抬头可以望见修筑在半山腰平旷处的站部,那里有房屋和窑洞,房屋里住着干部和武警,窑洞里贮存着各种东西,而一排排土豆窖则在山腰的更高处,在荒草间露出狭小的洞口。土豆窖里贮存的土豆主要供播种之用。冬闲时常派个别人到窖内翻检所存的土豆,把部分变坏的土豆挑出来送入伙房,伙房的人剜去霉烂处,留下那可食的部分给我们做菜。每天送入伙房的烂土豆十分有限,能用来做菜的当然不多,整个冬天,分到碗里的煮土豆总是汤多土豆少,发出了泔水一样肮脏的灰色。随着天气变暖,土豆窖内清除出来的土豆量加大,汤里的土豆也日渐增多,等到播种开始,土豆的供应便达到高峰,每个人吃饭时都能分到一大碗煮土豆块。这时候大量的劳力拿镰片切下土豆上有芽眼的部分,拌上灰,运到地里栽种。剩下的多余部分全部送入伙房,在伙房里稍经洗刷,切成块大锅给我们煮食,各组的饭桶里,饭后常出现剩余。我终于目睹了六号在五处曾向我描绘的情景,不论你饭量小或饭量大,这期间确实都可以放开肚皮往饱吃了。
春播期间,从西安看守所正好送来一批新劳教,一个个苍白的面孔风吹日晒后都起了皮,脱皮之处,都是深一块浅一块的褐斑。我已在劳改队混过几个月,新来乍到的陌生感正在淡薄下去,突然站在局外观察新来的劳教犯,从他们脸上正好看出了自己当初的饿鬼模样。新劳教中有个小伙子,他大约就像王建中那样饿坏了肚子,碰上这一年一度放开肚皮大吃土豆的日子,吃得他忘掉了节制。那天,他吃完自己的一份土豆,又贪吃了别人分给他的,结果吃的太多,饭后不久,就肚子痛得在地上乱打滚,医生还没来得及急救,便因肠胃堵塞而撑死了。
原来人不只能饿死,还会撑死,这可是我从未经过的世事。但“撑死”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我想起了小时候西安的小孩子都会背诵的童谣,那时候每到黄昏,成群的乌鸦从城外飞到住家户的大树上栖息,哇哇地叫着,此刻,我们小孩子就在树下齐声高喊﹕
“老鸹老鸹一溜溜,
回去给你妈炒豆豆。
你一碗,我一碗,
把你妈撑死了我不管。”
撑死,就是没有限度地进食的结果,它基本上是动物的行为。比如,开春后我们的煮土豆内偶尔会有一点点羊肉,据伙房的人说,都是因羊号不断有死羊送来,才使我们的菜碗里增添了肉味。原来春暖草长,窝了一冬的羊群突然面对鲜嫩的新草,便没命地饱吃起来,其中有些小羊没有控制能力,往往一直吃到撑死为止。我曾目睹过羊号送来的死羊,肚子都是鼓胀鼓胀,像吹足了气的羊皮筏子一样。我们的祖先经过了漫长年月的制礼作乐,才使先民脱离了动物状态的饮食恶习,从而建立起文明的饮食礼俗。而监狱,特别是共产党的监狱,现在却滥用其饥饿惩罚的手段,把一个犯人饿得像春天的羊那样没命地暴食,最终撑死了自己。
小伙子撑死的次日,干部叫我上去帮忙装殓死人。尸首停在土豆窖附近的窑洞内,一具临时钉起来的薄棺材放在一边,死人的肚皮鼓胀,身上散发出食物发酵的酸臭味。他吃下去的土豆已经在尸体内膨胀开来,撑得他的肚子和腰部碌碡一样滚圆。我和另一个人用尽了力气,都无法把一条给他换上的干净裤子提上胯部。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半穿着裤子的尸体装进了棺材。
自从装殓了那个可怜的撑死鬼,我一看见饭桶内堆积的煮土豆,就想起他鼓胀的肚皮,还有他那土豆芽一般苍白发青的脸色。整个春播期间,每逢端起碗吃我那丰盛的一份,我嘴里都有一股子怪味。那几句童谣从遥远的童年隐隐传来,在我的耳边回旋不已﹕
你一碗,我一碗,
把你妈撑死了我不管。
(苏晓康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