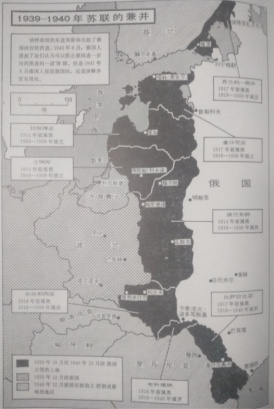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0)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3)
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从成立伊始就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问题。然而,过去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长期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存在着错误的认识,盲目地宣布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而导致对苏联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矛盾和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提出,由于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民族关系问题的法律,各个非俄罗斯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实体,因而已经彻底解决了少数民族受压迫、歧视和地位不平等问题。从后来苏联的社会现实来看,列宁的观点很不符合实际,纯属一厢情愿的想当然。
1924年1月列宁去世,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十三大政治报告中谈到民族关系发展状况时就提出,关于各民族权利平等、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当时苏联民族关系的实际状况,因为仅仅过了两年,联共(布)中央在一个决议中批评某地党组织中存在“氏族斗争和民族集团”,应加强少数民族工作,改善民族关系。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决议宣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在民族关系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而且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灭”;“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的问题。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政治报告进而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从后来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历史问题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这样评论民族关系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而是人为地掩盖了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问题。
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扬言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对于民族关系发展状况,赫鲁晓夫提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完全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已转入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因此“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为,“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苏共纲领认为,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统一大家庭中,各民族共和国边界已失去原有的意义,今后苏共的民族政策主要是促进各民族全面接进和统一。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对苏联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也作了错误的估计,否认存在民族矛盾和问题。
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成立50周年决议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已形成了各民族共同和一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各民族利益已经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各民族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正在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同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苏共今后的民族政策是实现各民族关系的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民族关系的现状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基于对社会发展的错误认识和对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长期以来,苏联当局在民族关系方面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从而轻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是苏联高层在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出现许多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多民族国家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一书中对列宁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从1917年到1964年这段时期,苏联所遵循的民族政策前后变化不定。由于形势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更替,民族政策出现过转折和中断。这些转折和中断使人无法理解苏维埃政权看待这个问题的观点和它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如果对这一复杂的历史进行细致和周详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1917年以来的所有政策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忽视民族问题和对这一问题的有关情况不甚了解。列宁生前虽然经历过各种事件,而且非常重视各民族给他提供的斗争武器,然而,他却很乐观地认为他能够控制住他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些“制造混乱的力量”。他最终还是严重地低估了民族意志的自治力量,也低估了俄罗斯的民族意志的力量,而俄罗斯民族是不愿让自己等同于以往受自己统治的民族的。
这种低估首先是由于列宁对民族问题缺乏兴趣。列宁是把民族问题看作革命的一种武器而予以关心的,他根本不关心民族本身,也不关心民族的愿望。他不了解俄罗斯周围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不同民族共处所必须的真正条件,正是这种无知常常导致布尔什维克犯估计性错误和策略性错误。
虽然斯大林与列宁以及自己的继承人都不同,他曾敏锐地意识到民族问题的顽固性,但他并没有因此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清楚准确的认识。他认为,从力量对比——中央的力量对民族力量占压倒优势——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虽不是已彻底解决,至少不会再影响苏联的政治生活。事实再次不容置疑地否定了这一看法。在战争时期,边远民族地区成了苏维埃制度中的“最薄弱的环节”。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自1917年以来所有苏联领导人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把民族问题看作是与别的问题同等性质的问题,看作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或者是错误政策留下来的问题。他们都认为采取适当的办法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长期的、威胁整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
所有苏联领导人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 他们都认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消灭民族差异。只是他们消灭差异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宁靠的是教育,斯大林靠暴力,而赫鲁晓夫则是靠否定斯大林式的方法,寻求政治和经济的合理性。但在这个问题上,前后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列宁和斯大林最终都懂得了他们一点也没有改变民族关系的紧张局面,这种局面仍然存在着并且在威胁着整个制度。相反,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却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一种从表面看来要比列宁和斯大林当时所理解的要简单一些的局面。从1917年起,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差不多等于两代人的时间,而这两代人都只知道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和体制。所以,赫鲁晓夫曾宣称,过去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联盟终于成了名符其实的联盟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消除被布尔什维克砸开的“各民族的监狱”所固有的不平等的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努力使这个新的人类共同体、社会主义共同体(而不是原来的四处分散、彼此隔阂的许多民族)兴旺发达,则是今后继承人的任务。今后就是“苏联人民”的时代。
那么,赫鲁晓夫的继承人能实现赫鲁晓夫的愿景吗?
苏联的民族问题在列宁时期初露苗头,在斯大林时期形成隐患,在赫鲁晓夫时期危机初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痼疾发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的少数民族逐渐“不安分”起来,自主甚至分离的要求日益显现,使苏联当局面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
虽然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沙俄帝国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民族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地发生。对于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活动,勃氏并没有运用民主和法制方式去解决,仍旧采用思想压制和武力镇压方式。例如,1965年至1967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院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严厉批判,逮捕和关押了几百名组织者和参与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
1968年4月21日,乌兹别克奇尔奇克市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借举行纪念列宁诞辰游园会之机,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实体,当即遭到警方的干预。大批鞑靼人不顾警察的阻挠涌向市内公园举行示威。军队和警察包围了公园,喷射有毒液体驱散人群,并逮捕了三百多人。但是,鞑靼人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968年5月,几百名鞑靼人在乌兹别克检察院和党中央大厦前举行示威,抗议对一些鞑靼人的迫害。1969年5月,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在“俄罗斯人滚出乌兹别克”的口号下又举行了群众集会。苏联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大约150人。
1972年3月6日,苏共中央通过批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为“民族主义者”,结果二百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
1972年5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而遭到批判和撤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有50多人。
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多人。
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受牵连。同年11月6一7日,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导弹驱逐舰250名拉脱维亚、立陶宛族士兵,因反对苏军中的民族歧视,组织哗变,把军舰驶往瑞典,遭到苏联海、空军的拦截镇压。
苏联当局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大力扩充专政机构,以维护统治地位。1969年5月15日《消息报》报道: “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拉脱维亚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都在为民警建设行政楼、汽车库、消防车库和训练所,并给他们拨出住房。民警住所有现代化的家具。值勤部队有专用的汽车,配备有中央通讯台和无线电装置。” “民警工作者被授予很大的权力”。苏联当局还抽调大批军人充实内务部。在各加盟共和国,苏联当局加紧扩建“人民志愿纠察队”、“同志审判会”等机构。据《苏维埃立陶宛报》1974年10月1日报道,该共和国共有6.7万多名纠察队员,4500名同志审判员。苏联报纸还报道说,亚美尼亚党中央通过决议,责成各地把“人民志愿纠察队的活动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吉尔吉斯党中央不仅制定了一整套法律教育计划,而且在一切居民点成立了所谓“预防违法的公众委员会”,等等。凡是反抗苏联民族压迫的人会受到审判,关进监狱。在苏联的集中营里,有一半是所谓的“民族分裂主义者”。青年学生反对民族歧视要被开除学籍。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各高等院校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学生,一年竟达七千人。至于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更要遭到苏联当局的镇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多年来,苏联各族人民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此伏彼起,持续不断,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据外电报道,1962年,在乌克兰、乌兹别克、西伯利亚南部等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发生过多次武装抗暴斗争,群众袭击军火库,武装自己,遭到军警镇压,许多人被枪杀。1963年,乌克兰人民为反对民族压迫政策,要求民族平等,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苏联当局派军队进行镇压,但是,乌克兰军区的官兵拒绝执行命令,当局调了另外两个军区的部队实行镇压。1965年,阿塞拜疆人民爆发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1966年,乌克兰掀起了更大的反抗苏联当局的斗争浪潮,在首都基辅,在敖德萨和伊凡一弗兰科夫等城市爆发了群众示威,抗议苏联当局推行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1967年,乌克兰人民要求尊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歪曲乌克兰民族的历史,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苏联当局在利沃夫、基辅、敖德萨等地进行了大逮捕。
1972年,从乌克兰到中亚,从波罗的海沿岸到高加索山区,各族人民的斗争互相呼应,持续不断。诸如,5月,立陶宛考纳斯市有一个青年为抗议民族压迫政策而自焚,几千人走上大街,高呼着“给立陶宛自由”的口号游行示威,冲击市党委和警察局,同前来镇压的警察和伞兵部队进行搏斗。6月,爱沙尼亚塔林市的大学生举行示威,反对苏联当局限制使用爱沙尼亚语言,掠夺爱沙尼亚资源的民族压迫政策。9月,乌克兰第聂伯罗杰尔任斯克市一万多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高喊着“法西斯分子”冲击了警察局,砸了州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克格勃大厦,撕毁了勃列日涅夫等人的画像。苏联当局调来军队进行镇压,当场打死了许多人。
1973年4月,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在乌兹别克三大城市塔什干、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可以在建筑物的墙上看到要求乌兹别克独立的标语。同年,立陶宛一些地方的大学生在公共场所贴传单,传单上有“打倒苏联统治!俄罗斯人滚出立陶宛!自由属于立陶宛!”的口号。1973一1974年,因为利沃夫大学在举行纪念乌克兰诗人舍甫琴柯的会议时散发了地下出版物,克格勃便在师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清洗。
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还不断出现反抗苏联统治的地下组织,他们出版地下刊物、散发传单、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如乌克兰一地下组织1972年底散发的一份传单指出,勃列日涅夫一伙已经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苏联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俄罗斯帝国的行政区,并作为殖民地而受到莫斯科当政者的统治”。传单强烈谴责勃列日涅夫一伙“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采取的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1974年,立陶宛一地下刊物揭露克格勃对立陶宛人的迫害,使他们丧失了起码的人权。
这些实例既戳穿了苏联当局散布的什么苏联国内“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已经消灭”的谎言,又说明了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反抗苏联统治的斗争不仅经常发生,而且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形成了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威胁着布尔什维克的统治。
几十年来,由于苏联当局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结果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加深了民族离心倾向。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的第六章《处于危机的一体化》中,用大量事实揭示了苏联少数民族是如何反抗苏联当局的专制统治的。这里摘录部分内容:
1967年是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72年是建立苏维埃联盟50周年;1977年颁布了新社会的新宪法。苏联政权有这么多的机会来宣传苏联民族的团结和一体化的成就。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年里,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公开的不一致,表明了一体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彻底。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危机。一体化政策从一开始就遇到危机,并深刻地分裂了中央政权和它的非俄罗斯居民。斯大林十分严密地监视着所有民族的优秀人物和集团,并一批又一批地屠杀他们,因为他们不屈不挠地想要保持本民族的统一性,并把被伤害的同胞们团结在自己周围。
赫鲁晓夫的安抚和让步政策使得各民族又出现了能代表它们意愿的优秀人物,但这些优秀人物在革命后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也证明了一体化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首先是培养出了优秀人物,他们是苏联政权引以为豪的“苏联人民”的化身;其次是出现了知识最发达的社会。然而,在最近几年所爆发的民族危机中,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些优秀人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所以,这些危机首先发生在那些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往往是最高的民族集团。如果说在1967年还可以认为不满情绪只是零星地偶然爆发出来,那么,经过这些年,某些民族集团表现出的不满情绪的增加和扩大就不能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转瞬即逝的事件”了。在一些共和国或自治州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事件,这些事件非常严重,以致苏联政权进行了严惩。这显然暴露了一体化的弱点。看一看这些事实和当地的争端,就会使人考虑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民族危机是不是由于某些特殊的形势和情况造成的,因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以控制呢?抑或是这些危机证明了一体化远远没有实现?
接着,唐科斯以三个少数民族的遭遇说明了所谓一体化是什么货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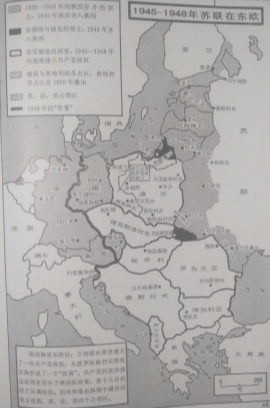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