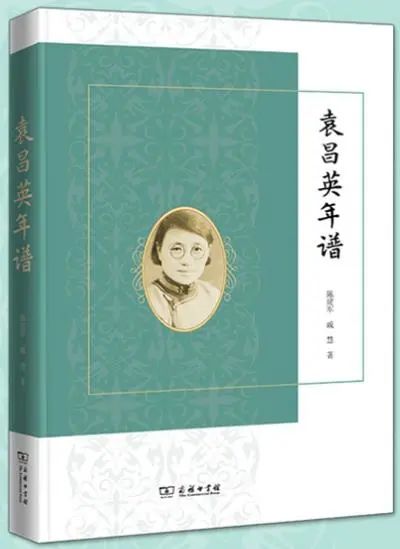(转者注:今天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珞珈三女杰”大姐袁昌英教授祭日五十周年,特荐年初出的此书以资纪念。)
我系统搜集袁昌英资料,大概始于2000年。当资料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萌发了编一部《袁昌英年谱》的念头,但人事栗碌,一直无暇动笔。我的硕士研究生戚慧,自从在课堂上听了我讲袁昌英的故事之后,也注意搜罗袁昌英的资料。2015年,她把近10万字的《袁昌英年谱》初稿交给了我。我在其基础上,补充了一些内容。2017年,戚慧考上了博士,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查找到许多有关袁昌英的资料,终使年谱增加到近40万字。2019年9月,我申请了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并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出版合约。
《袁昌英年谱》即将印行,遗憾的是,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先生和儿子杨弘远先生永远不能看到了。
2005年5月,我给静远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并寄了一份《袁昌英著译目录》。7月23日,她在来信中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你多年关注和搜集我母亲的遗作,而且极为认真,不遗余力,是我从未想到的。可惜早没有和你联系上,否则前几年我去武大时一定会去拜访并从你获得我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你的《目录》,比我在《飞回的孔雀》上列出的更详尽,例如独幕剧《笑》,我从未听说过,建国后的文章我也从未查到过……”在2015年静远先生以93岁高龄驾鹤西去之前,她一共给我写过七封信,同时随信寄了几篇她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如《徐志摩和袁昌英》《砖塔胡同梦寻》《又见“小脚”》《莎士比亚在中国迟来的春天》等。静远先生曾给我寄过一本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2月出版的《写给恋人(1945—1948)》,忘了签名,后特地签在一张纸条上,叫我粘贴在扉页上。静远先生视力不好,写的字如芝麻般大小,字迹也不算工整,可是非常干净,几乎没有涂改的痕迹。每当收到她的信后,我在感动之余,总会在心里警告自己:再也不要打扰她老人家了。
静远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译有《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传》《勃朗特姐妹全集》等。同时,她还致力于袁昌英研究,撰写了《回忆我的母亲袁昌英教授》《忆母亲袁昌英的二三事》《袁昌英和莎士比亚》等一系列文章。她的《让庐日记》《咸宁干校一千天》等,虽然不是袁昌英研究专著,却是研究袁昌英所无法绕开的重要参考文献。《袁昌英年谱》中,就大量引用了其中的材料。
也是在2005年,我拜访了杨弘远先生。记得是7月初,我头天跟弘远先生通电话,他约我第二天上午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他的办公室里见面。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弘远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言谈举止之间,尽显儒雅之风。我与他聊了大约两个小时,但他讲的少,而我说的多。印象至深的是,他说正中书局1947年1月出版的五幕剧《饮马长城窟》,最后一句不是他母亲写的,是编辑加上去的。临别时,弘远先生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7月出版的《勤思集》,签名后,送给了我。前几年,我想再访弘远先生。可是,上网一查,他已于2010年不幸病逝了。
杨家姐弟若是健在,我当第一时间将《袁昌英年谱》出版消息告诉他们。他们知道后,也许都很高兴吧。
老实讲,在与戚慧合作编写《袁昌英年谱》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并非总是愉快的,特别是在翻看了袁昌英的交代材料和揭发、批判袁昌英的文章之后,反而有些沉重。袁昌英的后半生极其悲惨:被划为“右派”、被定为“极右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在监督下清扫街道、被遣送原籍湖南醴陵、死时身边无一亲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袁昌英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仅从这一方面来看,编撰、出版一部《袁昌英年谱》是相当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警示我们:以史为鉴,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
为某一作家编撰一部内容翔实、可靠的年谱,需要尽可能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而这些资料的获得,则需要仰仗各有关单位、各方友朋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感谢武汉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让我们查阅了苏雪林遗留下来的日记手稿和稀见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学习简报》《思想改造快报》《新武大》及其他档案材料。感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周荣教授和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线索或获取材料的路径。感谢湖南省醴陵市袁昌英纪念园杨大秋先生,为我们拍摄了袁昌英生平业绩陈列馆的展品图片。感谢刘弋嵩、吴乐为两位同学。他俩都是武汉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弋嵩现在伦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乐为现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乐为从爱丁堡大学档案馆为我们复制了袁昌英的入学考试成绩单、主修课程记录表、当年的校历和《苏格兰人报》《晚间电讯报》《中国学生杂志》上面有关袁昌英的报道等。
感谢我的博士生沈瑞欣!瑞欣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是畅销书《红星照耀中国》的责任编辑,有比较丰富的编辑经验。她受商务印书馆邀请,审校了《袁昌英年谱》的后半部分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性建议。
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陈国恩先生!之所以请先生赐序,主要是想为我们三代之间的学术情谊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感谢责任编辑林烟霞女史!此前,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和《说不尽的废名》都是由她责编的。女史功底厚实,认真负责,《袁昌英年谱》能再次由她担纲责编,我是万分放心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为某一作家编写一部尽如人意的年谱,单靠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同行、专家、学者、读者的帮助、补正和指谬。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其臻于完善。”《袁昌英年谱》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同行、专家、学者、读者不吝赐教。
陈建军
2022年仲夏于珞珈山麓
来源:商务印书馆《袁昌英年谱》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