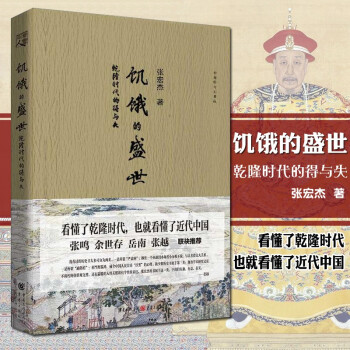二 大规模动荡的前奏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决定天下一切人的生死,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1743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遗传基因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也就是45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1775年),65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生命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之后,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年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调出全部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错误接二连三,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越来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倾转于内向,主动转于被动。壮岁之时,心雄万夫,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批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态变化。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的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清仁宗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他壮年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毀。”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皇帝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以来的六千多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二千七百余万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普免八省钱粮;乾隆六十年(1795年),免各省当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清高宗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
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但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托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23次,其中13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11次,迟延占4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9次中,迟延占5次。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4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5任地方官,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清高宗实录》)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啯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啯噜”的活动进入縞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1795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