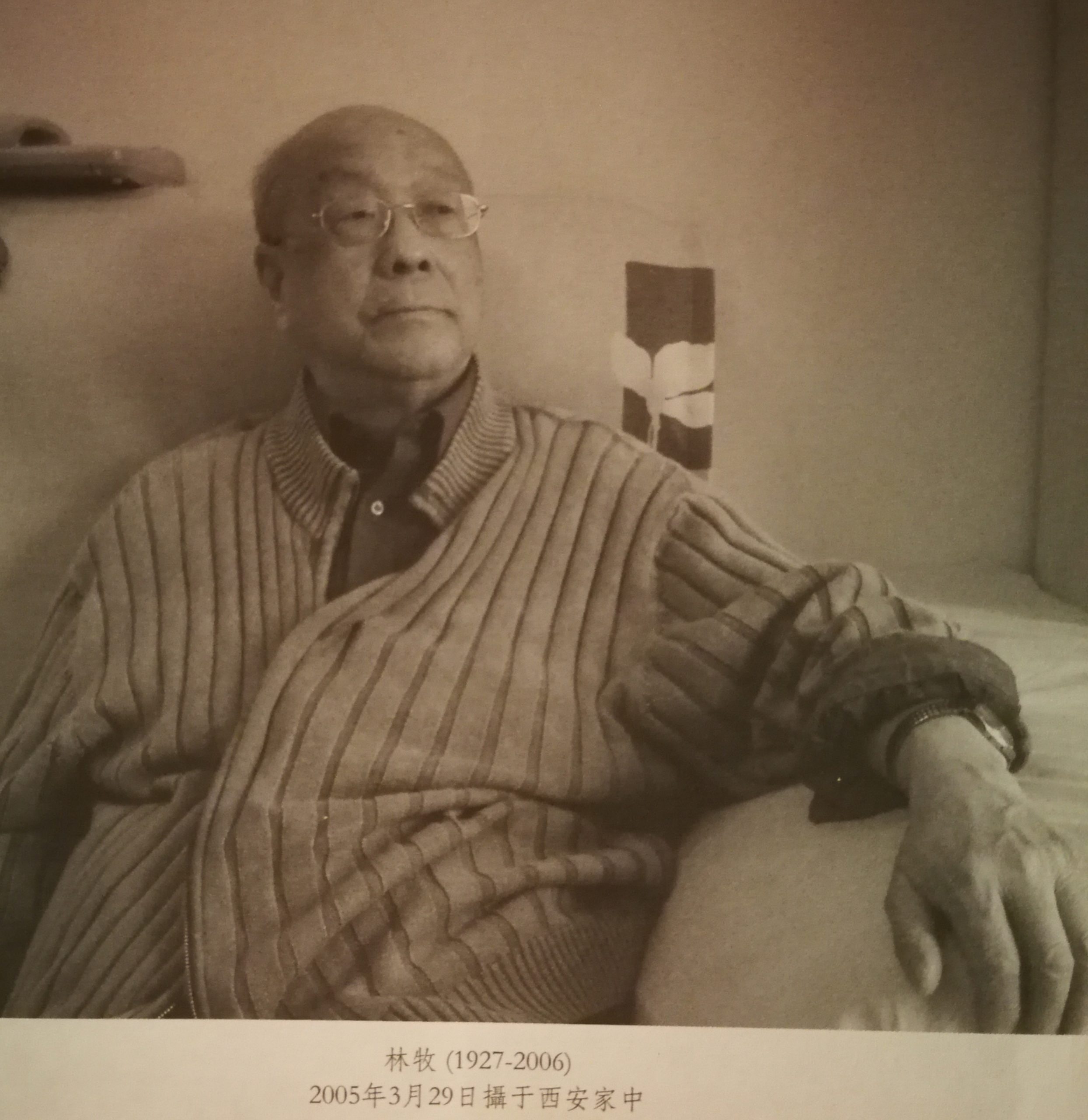六、我的几次自杀
第一次自杀时39岁,李自成等很多名人也是这岁数自杀的
耀邦问我:林牧你怕不怕挨斗?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的必死药方都是假的
吃安眠药、吞铁钉……
胡耀邦的自我评价:不是自己既是自己
七九年我也搞过西安的“民主墙”
就因为胡耀邦这件事,因为我是三次上书嘛。起先我是在第二条战线,就是列在训练班,有批人先都倒戈了,胡耀邦不在,集中揭发的是第二书记赵守一,最亲密的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我们私下所谈的一切都揭发了,我就是在6月16号晚上自杀了。
后来被一个省委宿舍的管理科科长发现了,把我送到医院去。自杀准备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要从耀邦临走的前一天晚上,1965年6月19号晚上,和耀邦最后一次谈话,耀邦就问我,林牧你怕不怕挨斗?这次省委预备会人家已经要斗你了,没有人响应,以后还免不了要斗你。我说:我这个人只经过小批,没经过大斗,因为反右派,反右倾,我都有问题,那时候省委保护我,我恐怕经不起打击。你们走后,我的前途不是新疆劳改,就是自杀。他的秘书戴云说,你怎么那么悲观,我说我乐观不起来,我做梦都盼望你们这次回去打官司能打赢,但是我很没把握。彭老总当年不过是提了几条缺点,并没有提出一条纲领的东西和方针,耀邦提了一套跟党中央不一致的非常开放的一条路线,这在党内没有过的。毛主席不允许,耀邦自以为他跟毛关系很近,他的重大职务都是毛主席提拔的,比如说二十八岁当中央军委组织部副部长,第二年当正部长,二十七岁当抗大的政治部主任,他大概也以为他跟毛主席关系非常亲密,但是就是跟毛主席关系密切,恐怕毛也不饶他。我开始准备自杀的东西,是在中央的通知下达以后,刘澜涛发表讲话,要抓西北的三家村,他没有点名,但是点出的问题都是胡耀邦,我看出这回大劫难逃,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阵势,群众都入了迷了,我觉得必死无疑了。到了1966年的春节,虽然刘澜涛已经知道我两次给中央上书,但还在争取我,他还是叫常黎夫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西北局去。我说我不想去,我在西北工作时间太长,想留一下,预先又给杨明轩讲过,他要调我到《光明日报》,《光明日报》通过中宣部调了两次,省委没放我。常黎夫说那不行,你只能在西北这个范围,当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或者研究室副主任由你选,我说那不行,我干不了,西北局的部长没有我这么年轻的。
谈话的时候我三十八岁,我自杀的时候是三十九岁,李自成、郑成功都是三十九岁死的。我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的人,怎么能到西北局去当副部长呢。他说不行,马上找省委书记,西北局要调我,我不是不愿意去,哪怕把我分配到越南去,去支援越南都可以。耀邦已经在北京给我找到工作,西北局不放。省委书记说西北局调令已经来了,你不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没有好处,到研究室当副主任,这是提拔。到66年3月,第七次批我的时候,我又给邓小平写了信了,我在省委的职务已经没了,必须到西北局去,我没有任何职务到长安搞社教去。一直到6月,省委集训班开始把我往回调,前一天晚上,在蓝田县大寨大队,离县城不远,做梦我正在那儿爬山,爬了几步出溜下来,再爬几步出溜下来,老是爬不上去,抬头一看,天上出现四个大字“珠穆朗玛”。这次这个大山我说绝对爬不上去。随后胡耀邦出事了,他们马上起来就抄材料,中午打电话来让我去省委,第二天就上了批斗会了。我已经积攒了一百多片安眠药,还有刀,可以切腕,还根据李时珍本草纲日上讲的合吃必死的东西,一种是蜂蜜加大葱合吃必死,另一种是西瓜加羊肉,咸菜加甲鱼,其他的弄不来呀,我的自杀首先吃的是蜂蜜大葱,一点反应没有,我亲身试验了一下,李时珍说的那些是无稽之谈,西瓜加羊肉也不行啊,也不起作用,最后吃的安眠药,要切腕觉得太疼,大概一百多片安眠药。具体日子是1966年6月16号。
自杀的动机主要是不愿意受苦,无穷无尽的,假如说没有大会斗争,没有私仇,这个私仇没办法,非致你死地不可。后来他们跟我讲,要把你们这些反党分子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看以后还有人敢反党不敢。他们把我救到医院去,整整二十四小时,才恢复了一会儿知觉,我看到我怎么在医院呢,还是很昏沉,好像自己认为还是要死的,旁边已经有人监护了,公安厅副厅长,我比较熟悉的人,让我讲话,我就讲了几件事情,刘澜涛有些什么问题,还有就是1962年,在西北搞包产到户,我说是他刘澜涛提倡起来的,后来他又推给省委书记,他几月几号讲话怎么讲的,我打了一个星期的报告,当然他不会报告中央。
6月18号中午,来了三个人向我宣布: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其实当时已经开除了我的党籍了,只是还没有宣布,因为审批手续还没有审批。于是就叫我搬家,专案组的这三个人是西北局政法组组长g,第二个成员是新调来的陕西省公安厅厅长n,第三个是陕西省警校校长h,这三个我都不认识,而且都是河北人,是华北帮(刘澜涛的班底主要在华北)。
他们宣布: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专门抓你这个案子,你写给中央的材料我们都看过了。其实那是诈乎人,但是我当时都相信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陆定一的老婆,给毛主席写信告林彪,已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就是这样的政策嘛,何况我三次告刘澜涛。
“你的信是谁给你转中央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田家英转的,有什么问题?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还不知道你们的同伙,现在已经畏罪自杀了?他不是毛主席的秘书,是破坏分子安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个钉子。当时我还不知道田家英已经自杀了。
马上他们就叫我搬家,很匆忙的,连鞋都没穿,急急忙忙把我塞上车,前面一辆车,后面一辆车,我坐在中间。第一次搬到军医大学神经病科,这一科的医生护士全都腾光了,其他都是看守人员,“病人”只有我一个,就在那儿审查。
后来又转移,文化大革命可能群众闹起来了,他们又从神经病科把我转移到西安市西大街夏家什字的一个公安厅招待所,那个房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院,有各种花木。第三次转移就降低标准了,搬到莲湖公园附近一个很普通的院子,再一次转移就更降格了,转到了公安厅八处那个看守所。这次看起来很神气,是在半夜里,前面一个打头的车,后面跟着一个车,我中间坐一个没有窗子的车,半夜转移。
审查问题主要是支持胡耀邦,为胡耀邦三次上书辩护,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后来又升成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说什么我当年到延安带了三十几个学生,是去做潜伏特务的。有个组织叫反共青年社,我是副社长,社长在当时已在台湾。社长原来是陕南人,后来是国民党两湖监察使,那人都六、七十岁了,我这个二十几岁的人当副团长,胡说八道呢。
第一次住监狱住在夏家什字,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资本家院子,还有花木,我还在相信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夹竹桃的枝叶有剧毒,我那个院子有几株夹竹桃,我大量的吃,没有任何作用。还有就是吃铁钉子,墙上拔的铁钉子,也没事儿,因为钉子在肚子里是直插下去的,如果斜插下去,肠穿孔了,马上就会死。反正不想活了,中国没有希望,前途是一片漆黑,越活下去就要继续受污辱。
后来怎么出来的?1966年12月25号,突然来了一个军人,说是红卫兵要把你拉出去批斗游街,批斗完了就接你回来,你在外面不许乱讲,给你自己加重罪过。
来人把我送到西军电(西安军事工程电子大学),交到那些红卫兵手里,头一天晚上看守着睡,第二天是12月26号,不能游街,毛的生日,红卫兵要找事干,叫我交待问题写材料,他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大人物的生活呀。
“这么冷的天气,你连棉衣都没有,毛衣都没有,你家在什么地方?“红卫兵问我。我说:“我已经扫地出门了,我也不知道妻子儿女在什么地方。”“你想办法说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去。”我说:“我妻子的娘家在什么路几号住,你试试看。”
结果他们派人去打听,第二天我的夫人就把棉衣棉裤棉鞋毛衣什么的都送来了,家里来人他们也不管,“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那伙人都关在那儿,黑帮都关在那儿,那些人吃饭时候都是黑牌子,不给你戴牌子,以后永远不给你戴牌子,27,28号要组织游街,不给你游街,这次游街是西北局抛出来的人,不是我们要的人,我们是向西北局要过你,听人说你搞过刘澜涛,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借批斗的名义把你要出来,以后再要游街,就是刘澜涛带头了。回到西军电的院子里,你是好人,你怎么还游街了?”红卫兵告诉我。
这样受“保护”的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学生的宿舍,还有外面借我去写材料,西军电说不行,这是我们的人。
吃饭都吃得很好,以后再不游街也不批斗了,在那儿混了大概一个月,后来领导干部都要放回去。平时也不参加什么劳动,也很自由,家属也可以来,我也可以出去,群众组织一次批斗都没有,他们给我翻案的时候,我说我不翻,我不是特务、反革命人员,我们就是修正主义分子。特务反革命是陷害,他说特务反革命给你否定了,就没材料嘛。
后来江青反翻案风,到了67年5月,新的革委会成立了,我们一个队里面叫小阳春,成为监护对象了,对我们还要进行军事监护。就在西安的73号院,门牌73号,里面关了73个人,大院套小院,一个房子住一个人,谁跟谁不能联系,在那儿一直关到1969年9月10号,忽然省革委会来了两个人,向我宣布两条,一条是林牧在历史上没有叛徒特务问题,而且还加了一句,对错误有认识。第二条是结束军事监护,送回原单位,接受群众批判,争取群众监督。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怎么突然给放出来,后来回到省委办公厅,有些干部告诉我,为什么现在把你放出来,但是又是半解放,不是全解放,毛主席点名叫胡耀邦等两个红小鬼参加了九大,而且都提名为中央委员。但是江青他们不同意,故意把这两个人都没选上,胡耀邦已经解放了,他们只好把你解放,没有全解放,就是胡耀邦没有当权,如果当权了,你就是全解放。
然后就是群众讨论,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后来反胡急先锋,省委领导里唯一一个被结合的继续担任书记的s发话了:“连林牧这样的人都要解放,那么胡耀邦就成了光杆司令了,陕西就抓不住黑线了。”然后又说我翻案,又开始限制我自由,送到五七干校四年半,商洛又去了四年,一直到77年六、七月份,我到北京去申诉,胡耀邦的秘书来了解,这些人怎么老都不解放?现在你们这一批没解放,是非没弄清。胡耀邦不能插手这个事情,他介绍王震,王震又转给叶剑英,邓小平刚刚出来,由汪东兴写了个批示,写得很有力,叫复查平反。陕西省委还核实,不给做结论。王任重来了,当时李瑞山在陕西这儿是一把手,他很顽固,不给我做复审结论,有些地方就为我打抱不平,第一就是安徽省委,第二就是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三就是国家民委。这几个打抱不平:把林牧调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做结论。正在这个时候,王任重到了陕西,接任了第一书记。王任重说哪里都不要去了,就在这儿,先工作,后做结论,管审查的人老是给你转弯子,先到省委宣传部当副部长。
11月初到省委宣传部,干部处那些同志说:“你怎么没有组织关系呢?”我说:“我开除两次党籍,哪有组织关系。”“你不是党员怎么当宣传部长了?”“这个事情就是滑稽,你们去问王任重,我也不清楚。”“你的待遇也不对呀,你十八年前就是省委的副秘书长,怎么现在是十七级呀?”我说:“开除党籍都要降级,连降了四级。”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平反结论下来了,补发工资。
到了北京当然是先找胡耀邦,胡耀邦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说呀,这是我的问题嘛。他的秘书戴云说:不说你的问题又说什么,他有什么问题,要不是你的问题,他哪有什么问题。我说那怎么办呢,胡耀邦又介绍说,有个人,你的老上级,是提拔过华国锋的,原来在西北局,你去找找他吧。
那个人很有骨气,他说:华国锋是和我有点历史关系,他来看过我,正因为这样,你以后不要来了,我现在自己还没解放呢,我头上还有黑线呢,我跟他不通信,也不打电话,你叫我转信,我不好转。你就去找胡耀邦嘛,他闯的祸,他不管谁管。
戴云建议请王震转,耀邦说:“王震星期天要到我家,你那天来吧。”王震来了后,耀邦给我介绍,王震说:“你是不是来开会的?”耀邦说:他有什么会可开呀,他还是黑帮呢,他是来告状的。王震说:“你告什么状?”胡说:“他告的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状嘛。”王震说:“怎么阎王都解放了,小鬼还没解放?”耀邦说:“历来是阎王好解放,小鬼难解放。”王震把我的材料拿回去,交给邓小平和叶剑英,王震对解放干部还是办了些好事的。
外电采访我讲过一次,胡耀邦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不是自己既是自己,是比较准确。他的夫人对他的评价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这也比较确切。我说大概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胸怀坦荡,透明度过高,基本上是在公开场所讲的和私下讲的是一样的,讲的和做的是一样的,他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水晶体,和他谈几句话,如见其肺肝,很容易看透。他的缺陷是无防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术。我们说的不可没有防人之心,他说不能防人,不做坏事,光明磊落,可以说通体透明。第二条好学深思,他的文化不高,他就是初中一年多,不到二年级,跟他的表兄杨勇一起参加革命,14岁嘛,在工作中博览群书,中国的、外国的、理论的、文学的、西方的古典小说、中国的古典小说几乎都读了,甚至连马列都看了,新旧约都看了,马列通读二遍,马恩列全集,通读第二遍的我还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中还有第二人。不但好学,而且脑子不闲,在陕西省委有人给他概括了五个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工作不断,抽烟不断——一天三包中华烟,不断的动脑筋。缺点是他的生活情趣不行,是工作狂,比如有个什么好戏好电影,让他去看看,放松一下,他不去看,说把剧本拿来看看。第三条是宽容,过分了,比如说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邓立群,都是他解放出来的。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是反胡的积极分子,陕西省委文革以后给他做出结论是开除党籍,到了北京不同意,还叫他回到吉林,降了半级,任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别人讲你胡耀邦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此人?他整你整得那么严重,耀邦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是不好,但是几个市委书记都这样,胡就这样为他找了个借口。对刘澜涛安排得也不低,刘澜涛人缘很不好,在北京找不到房子,耀邦当时还没当总书记,他是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秘书长可以管房子,胡耀邦说我来给你批,把大连高岗过去的公馆叫刘澜涛住。别人都不同意,说高岗公馆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规格,你怎么给刘澜涛呢?他说住了算了,宽容有点过头。他的思想超前,他是贫下中农出身,14岁在红军里面摸爬滚打,阶级斗争里面搞了几十年,为什么这个人思想那么开放,恐怕与读西方的著作有关系。在陕西搞的那一套,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想都不敢想,他的思想超前,1979年就提出在经济领域里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
1986年书记处有一次会上,讲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经过我们党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再加上一条法治,这三条是我们的最终觉悟和最高价值。1986年他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要继承欧洲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优良传统。还有也是1986年的事情,就是跟法国总理谈话,多党制可以是什么,共产党可以参加竞选,这对党的改善和提高有好处,如果落选了,就说明人民不再拥护你,你下来嘛。再就是对精神污染的看法与邓小平很不同,邓的看法是反对现代文明,企图把中国人拉回到几千年前去。
从被解放出来以后,我又回到省委宣传部,他们为了让我熟悉情况,给我看文件,办公室主任拿了一堆文件,一般的文件我也不看,我在里面翻出来一个敌情动态,是七十年代末吧,我和陈元方在西安了个民主墙,主要是我们两人写,还有其他人写的,都是在我们领导下,一翻那个册子,你们把我和陈元方的大字报都当作敌情了。负责专案的人说那是省委交待的,凡是西安钟楼民主墙上有份量的大字报,都叫我们拍下来,然后整理出来,作为敌情动态嘛。
我们提点不同意见,就成了敌情了。现在我又成了掌握敌情的人,宣传部是掌握敌情嘛,掌握思想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说是哨兵,是思想战线的哨兵,说不定我哪一天又提了不同意见,又成了敌情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