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鲁迅,为何老死不相往来?
在郁达夫的帮助下,来自底层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但是微薄的稿费仍旧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为此,沈从文不得不放下尊严四处写信给朋友寻求帮助,只为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于是,沈从文与当时已逝著名作家的鲁迅先生有了间接的接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造成深深的隔阂。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一生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
❶沈从文冒充女人糊弄鲁迅?
由胡也频,沈从文随后结识了丁玲,他俩由亲密到疏远的复杂关系从此开始。因为丁玲的一封信,引来一场莫名其妙的鲁迅对沈从文的误会。就像当初走投无路的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诉苦并请求援助一样,眼见在北京看不到出路的丁玲给鲁迅写信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她陈述苦闷和困境,希望能得到先生的指引和帮助,为她设法谋一份能够糊口的职业,哪怕是到书店或报馆当一个印刷工人也行。但丁玲没有沈从文那样的好运气,她的信石沉大海,她灰心绝望之下黯然返回湖南老家去了。
鲁迅不给丁玲回信倒也不是没有爱心而见死不救,如果他知道“丁玲”确有其人,她信中所说的也都是真的,他会像郁达夫那样伸出援手,但他收到信的那天偏偏遇到《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另一个编辑荆有麟,鲁迅问荆认识不认识丁玲,荆有麟不但说不认识,还在看了丁玲的那封信后确信那是“休芸芸”的笔迹。这惹恼了鲁迅,在他看来,沈从文冒充女人糊弄他。胡也频又贸然以“丁玲的弟弟”的身份登门拜访鲁迅,更加剧了鲁迅对“休芸芸”的恶感,他把“写信”“登门”看作是沈从文的一而再再而三的骚扰,加深了误会。
针对沈从文在《国文周刊》上发表的一首录自家乡的方言民歌,鲁迅写信告诉钱玄同,这个叫“沈从文”的就是“休芸芸”, “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他所说的“各种名字”肯定也包括“丁玲”。他更把沈从文与欧阳兰—北京大学的一名男学生,因以女性化笔名发表文章,一度被孙伏园认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相提并论,指责沈从文 “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手”给他写信,被他识穿后, “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他没有用“人”这个字,而是自造了一个女字旁加一个人这么一个新字,用以讥讽)。
沈从文的确很无辜,他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莫名其妙地被鲁迅奚落了一通。当他听说了鲁迅有关自己的谈话和信的内容后,本来就自卑的他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以致终生不愿与鲁迅见面和交往。而鲁迅在得知了丁玲就是丁玲,丁玲的弟弟就是胡也频后,明白“不是休芸芸的鬼”,也为当初没有回丁玲的信而感到不舒服,但他明知是他误会了沈从文,而且还将误会扩大传播,使沈从文的名声多少受了些不良影响,却没有向沈从文表示过丁点儿歉意。
❷沈从文笔下的鲁迅形象
“一个胡子,像个官!”
沈从文平白被冤枉,却连个道歉都得不到,心中之气自然一直难消,在越来越会写、越来越能写的他的笔下,鲁迅的形象便显得不可亲不可爱甚至不高尚了。这主要体现在他创作的小说中。
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沈从文涉及到鲁迅的小说粗略统计主要有五篇:1928年的《不死日记》、1929年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和《元宵》、1930年的《血》、1931年的《一日的故事》。
在《元宵》中,沈从文借一个书店小伙子之口这样描绘鲁迅的形象: “我还见过鲁迅先生!是一个胡子,像个官,他不穿洋服!”“像个官”,意味着在沈从文的眼里,鲁迅是高高在上的。
《不死日记》,沈从文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文学青年生活和精神的苦闷,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困惑和感知。这很像刚刚起步文坛的沈从文他自己。其中的“鲁迅”是一个“无用东西”。 说鲁迅“无用”,当然不是说他这个人没有存在的价值,沈从文的意思显而易见,无用的是牢骚、是讥讽—表明他不喜欢发牢骚,不满意鲁迅最擅长的冷嘲热讽。他认为鲁迅的文章再怎么深刻再怎么被翻译,却都“无用”,因为不能改变现状, “中国还仍然是中国”。而有用的是女人,是男女关系,这比深刻的文字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沈从文一方面不满鲁迅讥讽,一方面却又在讥讽鲁迅。
《一个天才的通信》,也写的是一个文学青年贫困潦倒的生活。准确地说,它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其中的“天才”影射的当然是沈从文自己。其中,“鲁迅”出现在“天才”的一个荒诞的梦境之中: “梦到鲁迅做寿,有许多人都不远千里而来,穿一色拜寿衣裳,成天磕头,膝上全绑着有护膝。他们拜完了寿就听那老头儿说笑话演讲,大家觉得比吃寿面还好。”——沈从文仍然在讥讽。
“北新书局”也随鲁迅一起出现在“天才”的梦中并非偶然。鲁迅与北新书局来往密切,他的作品很多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的,双方合作成为文人与商人取得共赢的典范。“我从肥人胳膊下望去”暗示像沈从文一样有才华而无名的文学青年对像鲁迅和北新书局那样互惠互利从而建立起良性出版机制的向往和渴望,也昭示了他对文人被商业控制使得文学不可避免地沾染商业气息的鄙视和痛恨。
沈从文对文人与商人互相利用、相互结合的嘲讽,在《一日的故事》中也可以找到。主人公晋生君被出版商相约“做生意”。所谓“生意”,也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文章)。出版商许诺先付给晋生君一笔钱,晋生君答应在一定期限内交出稿子。可是,晋生君一连几天灵感不冒火花,憋得痛苦,便心生感慨: “只要上面写的是字,说是鲁迅这老汉子作的,在上海方面,就有人竞争出钱印,出钱买。这事情,不是就说明读书人与著书人,近来全是天真烂漫的做着所谓文化事业么?”——又是一个讥讽。
沈从文在《血》里说鲁迅是“呆子”,呆就呆在他说过“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他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就他所见所闻,从血管里出来的未必都是血,或者可能是水血混合,或者可能干脆只是水。他觉得鲁迅之所以“呆”,是因为躲在安逸舒适的书斋里时间太久而见到的事情太少。如果“见到事情较多”,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呆”话来了。沈从文一直自认见多识广,他把鲁迅归于脱离现实生活只会纸上谈兵那一类。
❸落魄的底层文学青年与“无用”而“矫情”的知识分子
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固然离不开他所受的教育,更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有关。沈从文用这几篇小说讥讽了鲁迅与北新书局(文人与商人)的结合是文人的堕落、鲁迅说“呆”话是因为脱离现实生活、鲁迅写的那些所谓深刻的文字于现实毫无用处,等等,其实都反衬了沈从文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与鲁迅不同,也透露出他自傲且自卑的矛盾心理。
“自傲”在于相比鲁迅的埋首书斋而只在被称作象牙塔的大学校园穿梭的单纯,从社会底层一步步走来的沈从文生活经历多彩、社会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是他创作的资本。他自信比鲁迅对环境有更多的认识,对民众的疾苦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对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丑恶有更深刻的理解。
“自卑”在于相比鲁迅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又有外国留学背景,只上过小学更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沈从文只能以上过“社会大学”来自嘲。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固然是他擅长乡土文学,其实也不排除他以这种自贬到底的方式保护自尊。自傲与自卑,都来源于他的经历。
曾经贫困潦倒过,自然对贫困潦倒有着切身的悲切感受,沈从文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像他自己的文学青年形象:生活拮据而不得不想着卖文为生,却因为人微言轻而不被重视,四处投稿石沉大海;那边,出了名的作家不愁吃不愁穿地与出版商做着买卖,写出来的东西未必有价值有意义却被人抢着要。原本,他对新文化运动还是充满激情的,到北京后却时常看见新文化人只把“运动”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
在自认经历过并仍在经历着生活的艰难困苦、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的沈从文看来,像鲁迅那样并没有经历过真正底层生活的人,却在那里作深沉状探讨底层贫民的人生,还要悲天悯人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委实有些矫情,因此,本能地怀有一种反感与排斥,所以他才会说鲁迅深刻的文字“无用”—没有生命的文字改变不了社会;才会说鲁迅的某些言论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鲁迅其实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
如果说,沈从文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只是他练笔似的草草勾勒的话,那么,当他也日渐有了相当的名声后,对鲁迅的人与文的评述便显示出理论性的深刻和极具个性的独特。总的来说,他对鲁迅的小说、散文、诗的评价是积极的,他也承认他写乡村题材的小说是受了鲁迅《社戏》的影响;但对一般人认为是文中精粹的鲁迅杂文,他则不肯赞同,甚而颇多微词。
❹贬与褒之间转换的复杂心态
无论是沈从文对鲁迅,还是鲁迅对沈从文,他们的态度有时都会表现出矛盾的一面。鲁迅去世后,与文化人纷纷撰文纪念怀念不同,沈从文很沉默。直到一年以后(1937年),他才在《再谈差不多》一文中质疑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的鲁迅,“伟大何在”?也就是说,他特立独行地并不认为鲁迅是中国最伟大人物。他是不喜欢鲁迅这个人的,但他却又在十年以后的1947年,在《学鲁迅》中推翻了他以前对鲁迅的贬,取而代之的是一味的褒。这次,他认为鲁迅有“明确而永久”的贡献。或许这与他此时已经与“自由主义者”渐行渐远,而融入了主流,这才以主流话语的方式响应或号召“学鲁迅”。
鲁迅亦如此,他也不喜欢沈从文这个人,但当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后简为《记丁玲》)被当局粗暴删节时,他没有冷笑着斥一声活该,反而很为之鸣不平。不能把他的“鸣不平”理解成因为《记丁玲女士》记的是左翼人物,他对沈从文时有讥讽并不影响他对沈从文文字功底、小说成就的部分认同。“丁玲信”事件中,他虽然在给钱玄同的信里有对“孥孥阿文”的轻慢语言,但他也承认“阿文”“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能做做”,从“不讽刺就是褒奖”的鲁迅嘴里说出来,可以算是难得的赞赏了。1934年,“文化生活社”出版一套十二本作家作品选,鲁迅明知其中有沈从文的《八骏图》,他还是极力向萧军推荐,还说“这出版社并不坏”。
然而,1935年上海良友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八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在“小说部分”,却不见有沈从文的大名,而选编者恰恰是鲁迅。他为什么不选沈从文,看沈从文的一段话,或许可以找到解释: “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沈从文《读〈中国新文学大系〉》)“清算”二字,颇能说明问题。只是不知道鲁迅的行为是无意之中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的清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沈从文顺应形势,与主流“同期声”,再次无限拔高鲁迅。他在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一封信中,在谈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说: “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很难说这是他的违心之论。在他和鲁迅老死不相往来的时候,他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所秉持的自由主义立场恐怕是他与鲁迅难以相容的根本原因。如今,他不再“自由”。自由时,说出来的是自由的话;不自由时,说出来的未必不是自由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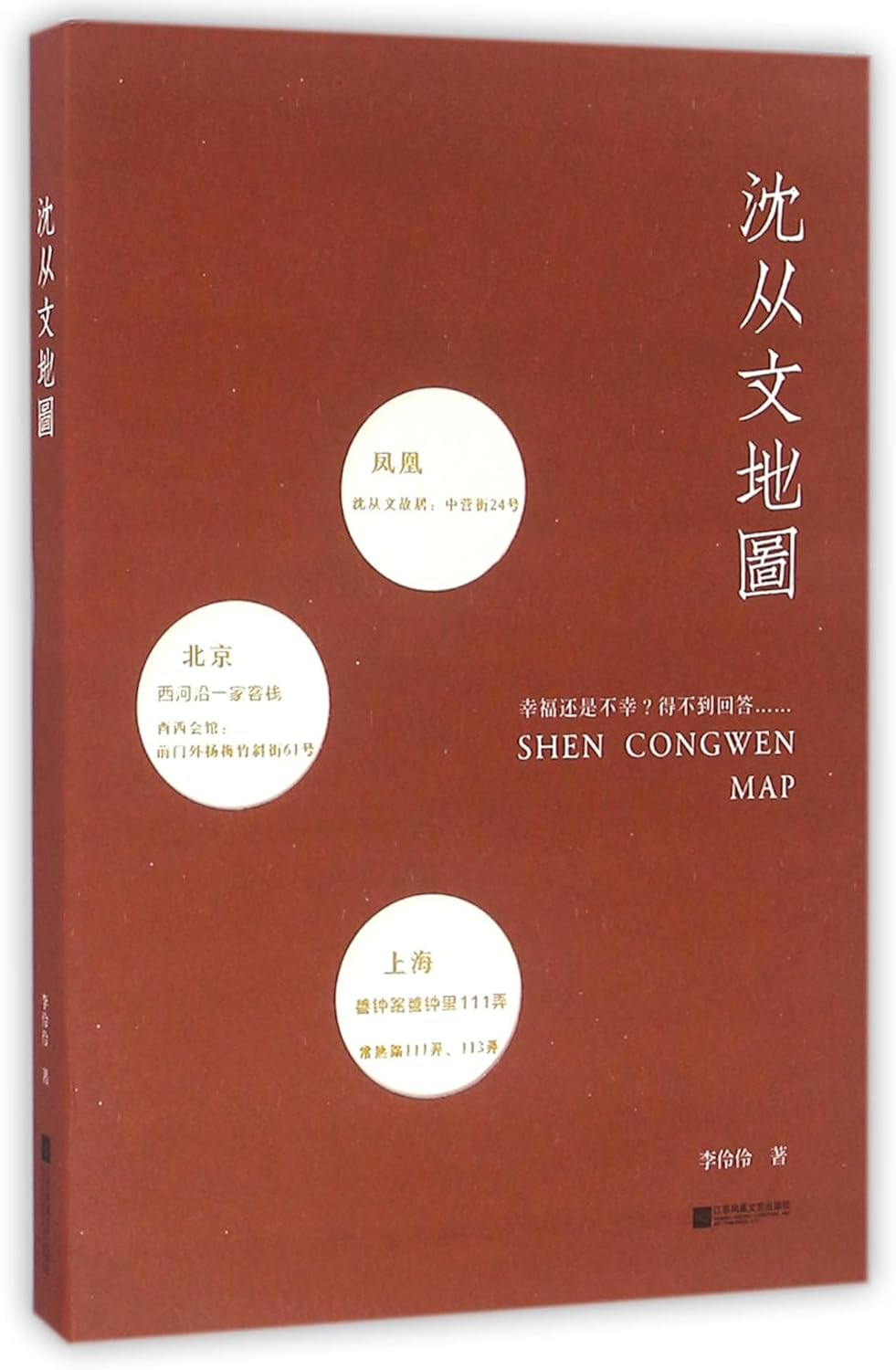 节选自《沈从文地图》
节选自《沈从文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