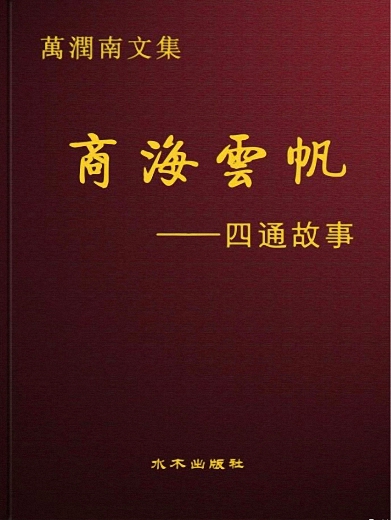第六章 泰山压顶
(43)抽银根
雪上加霜的是,“上面”还要抽银根,切断我们的资金链。
一个企业能否健康运行,关键是看它的现金流( Cash Flow )。企业现金流的循环,犹如人体的血液循环。要是把一个人的血液抽干,这个人还能活命吗?同理,如果掐断了一个企业的现金流,这个企业就只能关门。查收入、罚税款、限物价、查外汇,都没有把四通整垮,这“抽银根”,是最厉害的一刀,它砍到命根子上了。
四通的现金流,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当年,从国家银行那里,我们贷不到一分钱,我们唯一的贷款来源,是一家农村信用社:海淀信用社。崔铭山和信用社主任老祁是老交情,他们之间的合作在小崔加盟四通之前就开始了。那时候小崔在科学院发育生物所的劳动服务公司。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是月息7.2厘,比国家银行的6.6厘高出10% 。四通先后从海淀信用社贷款约2500万元。到1985年4月调查组进驻时,尚未归还的,还有1500万元的贷款余额。
政府出台了新政策:一个企业的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其注册资金的二倍。四通成立注册时只有四季青的二万元。明摆着,我们不可能再贷到新的资金了。
这1500万元,是四笔半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7月份到期200万元,8月份要还300万元,9月份和10月份各有500万元贷款到期。其中只要有一笔还不上,政府就可以派人来接管、清理四通的资产。所以,其他公司的调查组先后都撤了,在四通的调查组一直到1985年11月7日才撤,他们是在观察四通的还贷能力,或者说,他们在等待取缔四通的机会。
结果让他们失望了,这四笔贷款,我们居然每一笔都如期还上了!但这背后的艰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不胜唏嘘。
四通超强的行销能力,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逼出来的。在1985年5月6日的公司会议上,我曾提出年销售目标2500万元,日销售额不能低于9万元,就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结果我们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好。1985年我们的年销售总额,超过了3000万元。
做生意其实很简单,就两件事:一是买,二是卖。这是一位哈佛商学院的学渣说的。
在《哈佛学不到的学问》一书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两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若干年后在街头相遇了。一位是当年班上的学霸,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主管;一位是班上的学渣,现在是成功的企业家、百万富翁。学霸问学渣:当年在班上没看出你有这两下啊,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学渣嗫嚅道: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两元钱买来的东西,五元钱卖出去……
在四通,这两方面,都有超一流的人才。王安时会买,崔铭山会卖。进什么货,要两元钱买得到,需要智商和精准的市场眼光;五元钱卖得出去,需要情商,需要一般人学不了的“行为艺术”。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崔铭山立下赫赫战功。他不仅抓门市销售,还驾着“大篷车”到全国各地搞展销,不仅把货卖出去了,还为四通建立遍布全国的销售网铺了路。
但是,再怎么会卖,从进货到出货需要一个周期,资金链仍有断缺。为了渡过难关,我们到处借钱。万幸,在关键时刻,我们借到了两笔救命钱。
那时候,我到处寻找可供短期周转的资金。当时,清华校友沈如槐刚接掌康华公司。康华答应为我们银行贷款作担保,但要收百分之一的担保费。担保费好说,问题是那时候没有一家银行能给我们贷款。所谓同意担保,不过是一个空口承诺。
我和李文俊去找四季青信用社。我至今还记得信用社小林那种带嘲讽的冷冰冰的目光:“你们这样的大公司,我们小小的信用社,哪里配得上给你们贷款?”
文俊气得黑了脸,拉着我转身就走。是啊,李文俊的哥哥李文元,一乡之长,因为四通的事情,正在做检讨,至今还没有过关。
熟门熟路的找遍了,没借到一分钱。无意中偶尔遇到两位陌生朋友,居然帮了我们大忙。
清华校友叶延红,是印甫盛和刘菊芬的好朋友,逢年过节,我们三家常一起聚会。老叶家住石油大院。叶延红听说我们到处在找资金和外汇,提供了一条信息:海洋石油测井公司非常有钱,也有外汇额度,建议我们去找一下公司的段总。
我们结交的第一位陌生朋友,叫段康,海洋石油测井公司的老总。
1985年7月9日,我和李玉去他们那里谈合作,这是我和段总第一次见面。之前,李玉曾找过他一次。我介绍了四通以及近期准备开发的项目。然后我说:“我们有技术、产品和市场,你们有资金和外汇,两家组成联营公司,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段总表示非常有兴趣,希望我们进一步提出可行性分析、市场预测和经济效益概算。我一口答应。
我说:“合作是一个过程,尤其涉及到外汇,从立项、论证到批准,周期很长。我们可以先从人民币合作开始,作为将来大项目合作的准备。”
段总说:“人民币合作简单,我就可以说了算。你说吧,怎么合作?”
我果断地抓住机会:“这样,你们拿100万元人民币,合作期三个月,我们按月息1.2 分(是银行借款利率的一倍),给你们分利3.6 万元。”
段总二话不说,打开抽屉,拿出支票本就签字盖章。
当我把100 万元的支票交给万老时,老爷子很激动,这可是雪中送炭啊。四通账上差不多已经被罚空了,这个月到期的200万元还贷,还没有着落。当月销售收入估计能有100多万元,这天上掉下来的100万元,正可解燃眉之急。

很不好意思,我们从段总那里拿走100万元支票时,连个收条都没打。三个月后,段总如数收到了103.6万元。从此,段总成了我们的铁杆朋友,每年的周年庆典,他都是四通的贵宾,直到1989年。
第二位陌生朋友,叫宗祥厚。他登门来访,是推销积压在手里的一批黄卡其布休闲裤。介绍他来四通的是楼叙坡,这位姑奶奶,常常有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据说,这位总后某副主任的女婿,路子很宽。我问宗,能帮了找短期融资吗?他一口答应,还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当时北京市的电话号码还是七位数。我至今还记得,他家的电话号码是“8147926”。
不是我的记性多好,而是因为楼叙坡当时开了他一句玩笑:“老宗,你这个电话号码不好。你自己听听,多不吉利:爸已死,妻走儿溜。你也太惨了吧?”
大家哈哈一笑。他的黄卡其布休闲裤,四通人包了圆。我也和大家一样,买了好几条。后来大家都穿它上班,戏称“四通裤”。
宗祥厚果然厚道,三天以后,“8147926”回了电话,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如约前往,这是一家部队办的公司,叫新兴公司,公司的老总叫张竹桥。张总和我寒暄了几句,便点点头,说:“具体事情,你去和小宗谈吧……”
我大概天生一副见了就让人放心的面相,否则很难解释段总和我第一次见面,不打收条就签了100 万支票;和张总见面几分钟,就答应借300万!有人说,这叫“面善”,相书上说:“相由心生”。应该是“心善”所以“面善”吧?但也不尽然,后来张竹桥对我说:“其实,对你们,我已经观察很久了……”
宗祥厚和我谈的借款条件不算厚道:300万元,期限三个月,利息30万元。年息高达40%。
我回来商量,连一生谨慎的万老都认为可以接受。九、十两个月我们分别要还贷500万元,总额1000 万元,这300 万元,正可谓雪中送炭。
到年底,四通账面上已经相当宽裕,我们非常从容地还了新兴公司330万元。据说,这次合作,让宗老兄在张总那里也很有面子。后来他去了日本。我流亡巴黎之后,他还主动联系过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