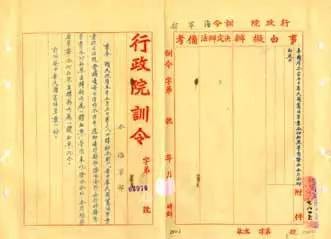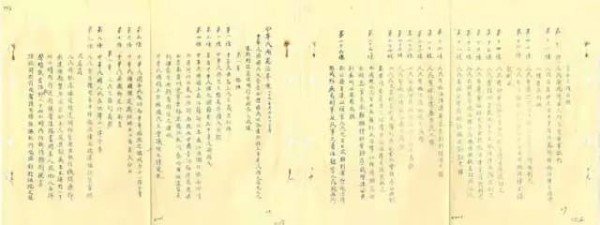上世纪30年代,思想界围绕政制与宪法问题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内容关乎国家政治走向与民族前途,其深度与尺度都极具突破性。
虽则由于抗战爆发讨论戛然而止,然其所论之议题与论证仍有长远意义。
自1933年12月起,胡适和《独立评论》的同人们讨论政制问题,参与者包括蒋廷黻、吴景超、常燕生、丁文江,以及在《东方杂志》撰文的钱端升等人,他们从1934年1月起为《大公报》写“星期论文”。讨论断续将近一年,胡适在12月9日为《东方杂志》撰写的《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小结。
 在逐一反驳了蒋廷黻、钱端升等主张专制或独裁的观点之后,胡适说:“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式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他注意到此前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57期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就公然主张领袖独裁制。同一期另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
在逐一反驳了蒋廷黻、钱端升等主张专制或独裁的观点之后,胡适说:“在这一年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党部人员公然鼓吹‘领袖独裁政治’,而一方面又是政府郑重地进行制定宪法的工作,正式开始所谓‘宪政时期’。已公布的宪法草案,是经过一年的讨论与修正的结果,这几天就要提交五中全会去议决了。然而‘领袖独裁’的喊声并不因此而降低。”他注意到此前10月20日北平出版的《人民评论》第57期有《斥胡适之自由思想》,就公然主张领袖独裁制。同一期另有《为五全大会代表进一言》一文,其中建议:“即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既不必再循训政之故辙,亦不必急于召开空洞无物、徒供军阀政客贪污土劣利用之国民大会。”
正当他为此感到不解之时,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通电全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盖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也。”同日,蒋发表答复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也明确:“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那一刻,汪、蒋握手言和、公开承诺不走独裁之路,至少给他带来一些小小的鼓舞。
1 民主与独裁的讨论
此文还未刊出,另一轮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又在《大公报》揭幕,这一天胡适发表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对于汪蒋通电里提出的这些原则他深表赞赏,认为通电中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要比宪法草案中用“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汪、蒋通电前后几天,就有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大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清华文学院长在办公室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
 老朋友丁文江读了此文和他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1934年12月18日在《大公报》发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他不同意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的说法,认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
老朋友丁文江读了此文和他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1934年12月18日在《大公报》发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文,他不同意胡适关于“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的说法,认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
丁文江直言:“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来说独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不过不是蒋廷黻、钱端升两先生理想的独裁而已。岂但我们的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经济恐慌。在没有渡过这双重国难以前,要讲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实的。”因此他主张往“新式的独裁”路上努力,第一步就是“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这当然是胡适不能同意的。
这一轮的讨论比上一轮要深入,吴景超、张奚若、丁文江等见解不同的文章在《大公报》作为“星期论文”发表,有的由《独立评论》转载。《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也刊登了张佛泉、陶希圣、陶孟和、陈之迈、吴景超等人的讨论文章。
12月30日,吴景超发表《中国的政制问题》,清晰地将这个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政治?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第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治?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第三,怎么就可以达到我们愿意要有的政治?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对这三点,他的看法是,“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袖占有很大的势力。”他认为这一点不单在野的人有许多这样看,就是在朝的人也是同意的。“关于第二点,因为包含一个价值问题,所以意见就分歧了。”他表示与胡适一样赞成民主政治,“我个人赞成民主政治的理由是很简单的:第一,民主政治是理智的政治,谁能够说服大众,谁就可以当权;第二,民主政治是自由的政治,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赞成政府,或反对政府,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第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政治,假如我们对于政府不满意,可以提出我们的主张来,以求民众的拥护,假如民众赞成我们,我们便可上台,不必流血,不必革命;第四,民主政治是大众的政治,凡是公民,都有参政的权利与义务,民众与政治,可以打成一片,没有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
据他观察,“中国的智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不过觉得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到时候就是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要努力在中国的环境中培植民主政治的条件,“这是和平的——同时却是很吃力的——工作,大部分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完成的。”如何用教育方式来完成?他没有展开。
2 “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
1935年1月20日,陈之迈在《独立评论》发表《民主与独裁的讨论》,简明扼要地提出,“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来产生及推倒统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这层便有了民主政治。”
对于汪精卫、蒋介石通电中“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他认为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我们对于民主政治,不可能陈义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对于现存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国民党全代会,能代表一部分应有选权的人民,并能产生稍为类似内阁制的政府,应认为是一种进步;⋯⋯对宪草里规定的国民大会,则应努力使它成功。我们不斤斤于普选,因为那只是程度问题;我们不斤斤于代表机关是否真能代表人民,因为哪国的议会都不是反映着社会的一面好镜子。”他强调的是“先抓住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就是“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
胡适指出,陈之迈所说正好可以补充吴景超所谓的“技术”问题。 2月17日,他在《大公报》发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尤为认同吴景超和陈之迈的见解,认为他们“清楚明锐的分析,——已可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了”。
北大教授陶希圣在1月20日的《独立评论》发表的《民主与独裁的争论》说,“胡适之先生主张的民主政治,很显然的是议会政治⋯⋯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胡适一方面表示,我们现在并不愿意“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宪草规定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省参议会、县议会等,都是议会政治的几种方式。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而在这样走上民主宪政的过程上,国民党是可以得着党外关心国事的人的好意的赞助的。”
参与这场“民主与独裁”讨论的有地质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观点也各不相同,甚至非常对立,但是讨论问题的态度是从容、理性的,不以观点不同而剑拔弩张,各人均经过认真的思考,并摆事实说道理,对话的姿态大于论战,关于民主还是独裁的这两轮讨论,大致可以代表了那个时代受过最好的学术训练、真正关怀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现实环境下最真实的声音,他们争的不是输赢,更不是权力或利益,而是以自己所属的国族为念,要说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在他们当中并不缺乏。
从1935年2月13日到24日,《大公报》连载张君劢专文《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主张折中独裁制和民主制,搞一个集中心力的国家民主政治。《大公报》2月13日的社评《中国不适宜于独裁》表明的立场,与胡适基本一致:“今后训政结束之后,国民党之地位,自仍可为中心势力,但同时宜本遗教所示,以培养民主政治之宪政为目标”。
3 对“公民宣誓”的争议
1935年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各方对国民党这次全会寄望甚切。9月7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对于五全代会之期待》,直言:“人类美德之一,为忏悔。国事至此,凡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享优厚机会之人,皆宜至诚忏悔,自咎负国。”
11月12日,五全大会在中山陵前姗姗迟开,《大公报》在刊登这则消息的同时,报道了宋哲元电呈大会,要求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与民更始,努力复兴大业。11月22日大会闭幕前一天,《大公报》报道,大会决议接受宪草,授权第五届中执委会修正宣布,国民大会期也由中执委会决定。
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接着,公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岁,经公民宣誓者,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之权。” 所谓“公民宣誓”的誓词为:“正心诚意,当众宣誓,从此去旧更新,自立为国民,尽忠竭力,拥护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采用五权宪法,务使政治修明,人民安乐,措国基于永固,维世界之和平,此誓。”
王芸生直言自己只是无党无派的国民,大体上同情于国民党,并且对于国民大会寄有很大的期望,但他发现要参加国民大会的选举,须先确定公民资格,如何才算公民,须经过一次公民宣誓。“我从各方面来审查我自己,或尚勉强够一个公民的资格。我誓愿尽忠国家,永不做违反国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举手宣誓信仰三民主义,却踌躇了。我不反对三民主义,并且在原则上是赞成的,但若一定叫我举手宣誓,承认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还得给我一个充分的时间,再把三民主义仔细的读几遍。这是一道门坎,迟留在这个门坎外边的,想来当不止我一个人吧。”(王芸生《五寄北方青年》,1937年4月26日《国闻周报》)
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担忧。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这样批评,“一方面倡导国民大会的选举及宪法之制定,一方面则用种种方法使得不赞成国民党的人丧失其国民之资格(例如不肯为国民宣誓的人们),实令现在热心中国政治的人感觉悲观。”他分析说,有政治意见的人,在国民大会选举之中便根本没有发表意见之机会,不肯宣誓的人根本便无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而事实上有政治意识而又服从三民主义者亦早已加入了国民党,所以余下来的只是一般无政治主张而希图藉此钻营者,或一般庸碌浑噩的‘老百姓’,以不敢或不便违背政府的功令而宣誓而投票,造成了官僚土劣威胁利诱的材料。”(《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前途》,1937年5月2日《独立评论》)
清华政治学系研究生宋士英表示,“此项态度实为目前绝大多数国民之心理与态度。再如国民大会组织法,虽因多方责难而修正,但修正的结果,反而加重国民党特殊之地位。”他批评“国民党向以人民之保姆自居,⋯⋯但今后既主实施宪政,而又不甘抛弃此保姆之观念,仍以特殊之政党自居,则为严重之错误。”(《中国宪政的前途》,1937年5月16日《独立评论》)
针对这种“包办”观念,王芸生也说:“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对于宪草上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他认为“在一个尊严的国家之上,还是少加些形容词的好”。
这种缺乏明晰主张的犹豫,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高层矛盾的呈现,也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蒋介石的内心缺乏路线。相隔八年,抗战胜利后来到重庆的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曾对胡乔木等人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还说过,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4 宪法不是用来点缀门面
1937年,对国民党承诺的宪政,知识分子既不乏批评也不无期待,毕竟这是代价最小的一条路。5月7日下午,北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原来准备组织的“宪法研究会”,修改为“国民大会各科法规研究会”。5月23日夜,胡适读了张佛泉的《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一文,忍不住也写了《再谈谈宪政》,认为两人见解很接近,他概述张的观点:“(1)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理想目标,只不过是一种过程,这正是我当年立论的用意。我说民主宪政是幼稚的政治,正是要打破向来学者把宪政看的太高的错误见解。(2)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开始时不妨先从小规模做起,人民有力量就容他发挥,这也是和我的‘逐渐推广政权’的说法很接近。干脆的说,我们不妨从幼儿园做起,逐渐升学上去。”他批评“现在的最大毛病就在不肯从幼儿园做起”,年满二十岁经国民宣誓即有选举国大代表资格,他认为这就等于“普选”了,“因为不识字的人也可以教会背诵公民宣誓的”。对于国大的规模,他认为初办宪政就搞一千四百四十人的国大,“这又是不肯从幼儿园做起的大错误”。这一年,胡适、王云五等发起为张元济七十岁生日贺寿,吴经熊写了一篇长文《过去立宪运动的回顾及此次制宪的意义》,表达对商务印书馆和张元济事业的推许之后,他回顾了立宪运动的历史及这次宪法草案产生的经过和意义,他也清楚地知道,“宪法虽经颁布,人民未必即可唾手而获宪政的美果。宪政之能否实行,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一方面是关于负施行宪法责任者的,一方面是关于国民的。”就前者而言,第一要有行宪的诚意,“宪法虽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他自己是不能实行的。”第二要有守法的精神,宪法不是用来点缀门面、粉饰太平的,其价值和效用全在于能见诸实行,“而能否见诸实行,则又大半系于执政者之是否能守法”。就后者而言,一是要认识宪法,二是要参加政治、督促政府,三是须有护宪的力量。“我们渴望将来的宪政能够成功。因此我们希望执政者和国民两方面均具有行宪所应具的条件。”(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
原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集的国民大会,以来不及筹备为理由延期至1937年11月12日召集,总算日期确定下来了,实施宪政的预备都在进行当中。《大公报》上不时有相关消息,比如,经各方反复讨论,此次国民大会的职权限于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施行日期。4月23日的社评为此感到高兴,认为国民大会“得以专心一志,郑重努力于根本大法之制定”。陶希圣认为各党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以至宪法问题,值得学界热烈讨论。透过《大公报》和《独立评论》等报刊,包括他和萧公权、张佛泉等学者的讨论文章不断。
陈之迈在《从国民大会的选举谈到中国政治的前途》文中尖锐指出,自1924年改组以来,“国民党便抛弃了议会政治的主张而采取了一党专政的理论。”他认为,“国民党要领中国走上民主之路,便应该切实开放政权,容许并保障反对国民党的政党之存在。”
可以说,宪政问题与对日问题、共产党问题是当时最受注目的三大问题,也都是关系着民族兴衰的要命问题,几个问题之间的消长起伏,最终决定了一个历史时段的走向。那些年中,《大公报》那班人、胡适等北大一班人和商务馆的《东方杂志》,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宪法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上,没有想到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越来越紧,这一切都要被中断。到1937年7月4日,胡适还在《大公报》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他认为宪法里不可有一句不能实行的条文,比如宪草第137条规定“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市县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而在当年的国家预算案中,教育文化费只占到预算总额的4.28%。难道宪法颁布之后就能每年增加那么多的教育经费?如果不能,则不可留在宪法里做一条具文。依此标准,他主张暂时把宪草里的第六(经济)和第七(教育)两章完全删去。又依此标准,宪草第五章(地方制度)的县长民选和市长民选两条,如果此时不能实行,也都应删去。至于国民大会职权中的“创制法律、复决法律”也决不是那每三年集会一个月的国民大会所能行使的,这一类空文也应该删去。这样删改之后,“五五宪草”大概可以成为一个字字句句可以实行的国家根本大法,可以做宪政的开始了。
这些讨论是认真、更是诚恳的,但此时离发生卢沟桥事变只有三天。当然,即便在7月7日之后,战火已烧起,7月18日出版的《独立评论》还在发表陶希圣《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和王赣愚《整军与我国宪政前途》等文章。
来源:《凤凰周刊》2015年第21期总第5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