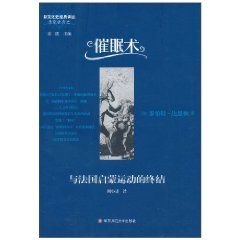
法国大革命前期的法国,虽然崇尚科学,然而在科学刚刚启蒙之时,社会充斥着大量毁三观的迷信巫术,诸如妇女坐在窗前会怀孕,因为空气中可能含有胚胎的有机分子;法国人相信自己与鬼魂和遥远的星球能够毫无障碍地沟通;大自然为人民服务,为了方便大家吃瓜,大自然把西瓜长成一瓣一瓣的;外貌协会特别有市场,因为看一个人的长相就知道对方内心到底是奸诈恶丑还是真善美爱。这些在如今看来极度愚昧的观点,却是当时法国社会极度盛行的议题。
无论是课本还是公知,在谈论法国大革命时,总是基于启蒙运动的单线叙事:大革命前期,法国人民在争相阅读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反动派的反动思想,似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进步青年。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在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的同时,在宏观大背景之下开始注重大众当时的生活方式及其态度来挖掘历史的现场,从微观社会开挖出了另一条有别于传统叙事的新文化史道路。随着新文化史的建立,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微观社会越来越被注重。这些新文化史一再表明,一场社会革命的产生与成功,必定是社会集体的复杂过程,而非单线的精英叙事。罗伯特·达恩顿在《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劈头盖脸的开篇语就是:“在卢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会契约论》最不受欢迎。”什么样的激进观点才真正合乎法国人的口味呢?罗伯特·达恩顿发现了革命的激进思潮是裹挟在风行一时的催眠术之下,让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1772年,奥利地维也纳医学博士梅斯梅尔踏上了崇尚自然的巴黎土地。他在巴黎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极为细微的液体,它在一切动物躯体上穿行环绕。这位江湖郎中大肆宣传,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这种液体在人体内的流动受到了阻碍,而通过梅斯梅尔术即催眠术对这种液体的控制、强化、按摩和疏通,便可包治百病,万事大吉。他在催眠术的描述中,既携带科学又附属神学,融合了法国科学家的科学理论和法国公知的宇宙观,使得法国社会对催眠术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骗术竟还真治好了几百人的病,催眠术也随之大行其道,连皇家贵妃都信奉了起来。如此愚昧的社会,是怎么引发大革命的呢?
在当时的巴黎,对科学的激情压倒了文艺的兴趣,连业余科学家们都充斥着各大报刊杂志,读者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参与讨论当时的“科学”。正是因为这种对科学的普遍狂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界限被抹杀了。对催眠术的狂热甚至压倒了人们对气球飞行的热情,新闻报道充斥着催眠术,法国诗人也加入了赞美的行伍,从学院到沙龙到咖啡厅,人们都在探讨催眠术:“像一场流行性疾病一样,征服了整个法兰西。”达恩顿还发现,召开三级会议之前的十年中,各种宣传手册很少见到复杂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对土地税等重要事件的分析,关于第一次显贵会议长达六个月的政治危机的内容,在撰稿人的版面上远远不及催眠术相关内容的一半。
为什么报纸杂志会出现这种状况?这得归功于政府的审查制度。政治审查阻止了人们在报纸上严肃讨论政治,新闻工作者又需要热门话题,在当时极具新闻价值的话题就是催眠术、气球飞行等伪科学或通俗科学的人间奇迹。连法国时尚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都对催眠术产生了兴趣,因为她被信奉催眠术的群臣影响了。在这种耀眼般的明星光环之下,“医学专家”梅斯梅尔被邀请到科学院讲座,但院士们对他嗤之以鼻。于是,他邀请院士们到村里现场看他如何治病,院士们继续冷眼以对。梅斯梅尔的粉丝夏尔·德隆,他是巴黎大学医学部主管医师,也是阿图瓦伯爵的首席医师,他的论文《动物磁力论》也被学院同事所鄙视,而且还被学校以宣扬异端邪说为由开除了。以德隆为代表的梅斯梅尔粉丝团在巴黎成立了普遍和谐社,开始以社团来集聚力量反击梅斯梅尔主义的反对者们。普遍和谐社逐渐地因催眠术的推广而遍地开花。
在一系列质疑与信奉的争夺中,严肃的思想家们深感必须严肃对待催眠术,因为催眠术倡导者的说服力度和催眠术的流行程度让他们不得不去检查梅斯梅尔催眠术的科学与宗教原则。梅斯梅尔主义者的治病理念在流行之后,对学院体制及宗教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一是梅斯梅尔主义者对学院不接纳催眠术感到十分愤慨,一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宗教的信奉者变成了科学时尚的粉丝。巴黎的警察在调查梅斯梅尔主义者的反击言论时发现,催眠师们在他们的伪科学话语体系中掺入了激进的政治思想。梅斯梅尔的弟子贝尔加斯对社团内部的不和谐感到不安,因为社团内部也有法国贵族在内。在贝尔加斯试图进行改革时,便开始了他的革命激进主义:“法国需要的这场革命,现在是时候了。但是,如果想要公开引发革命,那只会让革命失败。要成功,就必须把自己包裹在神秘之中,就必须以物理实验为借口团结人们,而实际上是为了颠覆专制。”贝尔加斯朋友、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在成为催眠术信徒之前就见过了日内瓦共和革命,也阅读过卢梭的作品。虽然催眠术没能给他新的激进观点,但贝尔加斯在催眠术理论中的激进理念却让他看到了卢梭的影子。布里索认为,若是将卢梭的观点裹挟在催眠术的庸俗化理念之下,那么没有心思阅读《社会契约论》的读者们就可以在对催眠术的探讨中吸收卢梭的观点:“表面上批评的是官方学术机构,实际上矛头对准的是专制独裁政府。”
正是催眠术信奉者与革命领袖的这种互相利用的媾和合作,让催眠术推进了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布里索等人重新撰写宣传手册,并将梅斯梅尔塑造成结束人间苦难的伟大奉献者,但他却处处遭遇科学院、皇家医药学会、大学医学部以及皇家委员会的羞辱与迫害。布里索的激进主义表现有:他竭尽所能地去批判学院里的那些“卑贱的寄生虫”和“祖国的压迫者”,批判沙龙里那些讨好官员、夫人和贵族的“卑鄙的谄媚者”,批判那些“似懂非懂的家伙,他们自己抛头露面,逼得真正有才能的人无处藏身”……贝尔加斯则嘲讽一切与贵族阶层相关的事情,抨击血统论出身论,反对学院特权,并煽动性地发出号召:“让所有公民变得高贵,让所有权贵变成公民。”一旦发现贵族有通奸行为,他们就将话题引向法国政府道德败坏的话题之上,并将自己的催眠术理论建立在道德与物理互为因果之上,这就让催眠术的信奉者们将矛头对准了法国政府,很多早期的催眠师们后来都成了大革命的领导人物。观战的法国人民也随之受到了思潮的影响,对社会及政府不满的下层人既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又找到了抗议的伙伴:“贝尔加斯的‘论文’,也许为革命前的激进宣传提供了最有效的弹药。在巴黎皇宫各咖啡馆里,人们租来他的手册,一页一页地相互传阅。贝尔加斯将最后也是最具爆炸性的一枚弹药直接瞄准了大臣们。”
就这样,粗俗版的卢梭主义,在江湖医术政治化过程——从医学现象到社会现象再到政治现象——逐渐地影响了法国人,借助催眠术的激进暗流,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催眠术信徒们“为加速革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因为通过对催眠术的社会争论,“1787年到1788年间几乎所有反对政府的作品才得以发布”。法国大革命之后,布里索转身抨击催眠术,因为他已经是个政治家了。而当年政府派出的“提线木偶”(马拉对法兰西皇家科学院派出调查催眠术的科学家们的称呼),在大革命时期也遭到了惊人的报复:拉瓦锡等多位法兰西院士们被送上了断头台,抨击催眠术的孔多塞被毒死在狱中。
达恩顿在叙述催眠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向我们展示了启蒙思想与科学革命对普通民众的接受方式、大众文化与精英理论在法国社会的接受程度,还展示了民众是如何对待政治及时尚的,而催眠术从江湖巫术到政治革命的过程则向我们展示了革命时期的政客是如何科学且有效地操纵民众的。虽然说催眠术利用启蒙思想的社会事件本身带有反启蒙色彩,但催眠术裹挟的激进暗流却又带有启蒙色彩。达恩顿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社会进程中,既不能忽视精英理论,也不能蔑视大众心态,无论你是政客还是公知。
刊《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4年4月12日
